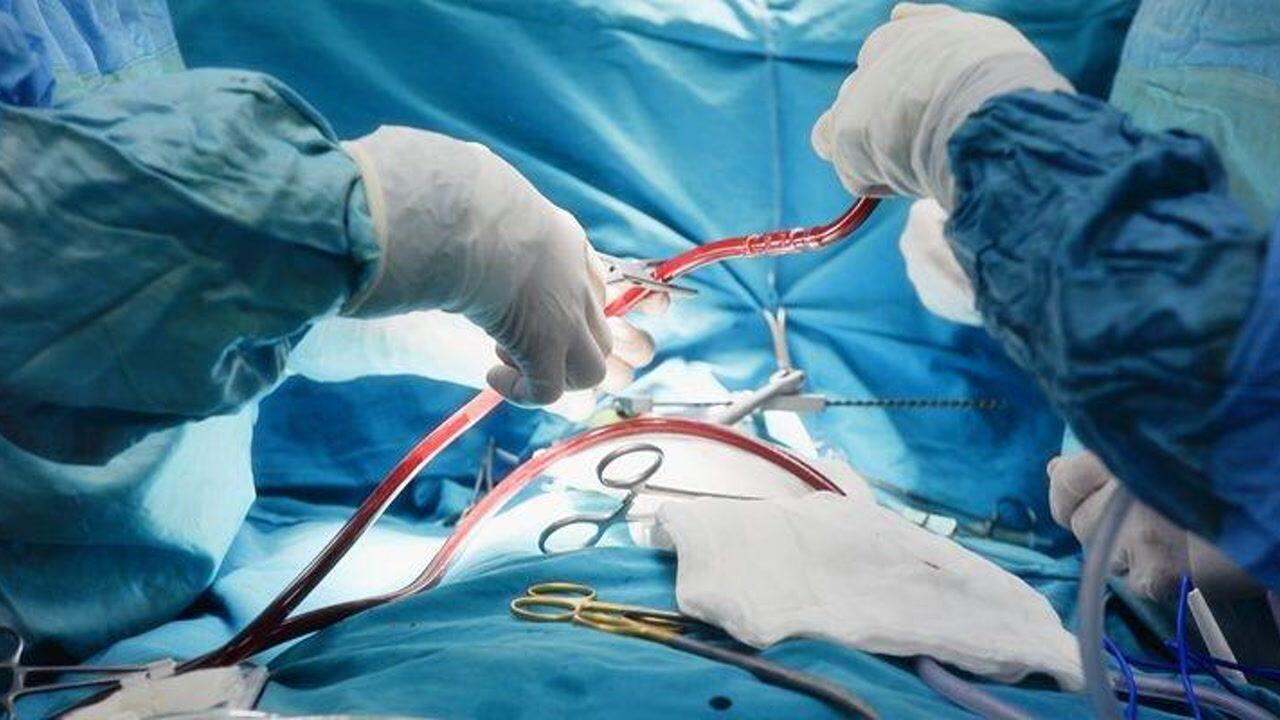半夜十二点多,老公轻轻把我拍醒,说心脏部位有点疼,刚含了两粒救心丸,让我和他去医院。到了医大x院,验血和做心电,夜里只能做这两项,排除了心梗的风险。医生拿着检查单,语气放缓了些:“暂时没大事,但心脏疼不能大意,明早空腹来做个心脏彩超,再查个冠脉CT,彻底看看情况。今晚先在急诊观察室歇着,有不舒服马上叫护士。” 十二点十七分,我是被他胳膊肘轻轻撞醒的。 “有点疼,”他声音压得很低,像怕惊到空气似的,“心口这儿,刚含了药,去医院吧。” 他的手搭在我胳膊上时,带着刚摸过床头柜抽屉的凉意——那里面常年备着的救心丸,今晚第一次少了两粒。 急诊室的灯光比想象中亮,亮得能看清他后颈渗出的细汗。 护士递来的纸杯里,温水晃出细碎的波纹,他捏着杯子的指节泛白,“怕耽误时间,直接挂了急诊。” 验血的针头扎进肘窝时,他偏头看我,“其实没那么疼,就是……想让你在旁边。” 心电图纸吐出长长一条时,我数着上面的波纹,数到第七个突然不敢数了——万一哪条歪得厉害呢? 医生进来时带着消毒水的味道,手里的报告单在灯光下泛着光。 “排除心梗,”他指尖点在“肌钙蛋白”那栏数字上,语气松了半分,“但心口疼不能掉以轻心,明早空腹来做彩超和冠脉CT,今晚在观察室待着,有事按铃。” 观察室的折叠床有点窄,他往里挪了挪,让出小半块位置。 我盯着他胸口的起伏,突然想起上个月他生日,吹蜡烛时多咳了两声,“是不是蛋糕奶油太腻?”他当时笑着摆手,现在想来,那笑声里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钝痛? 那些他加班晚归时说的“有点喘”,我当时只当是写字楼空调太闷,原来早有细碎的提醒藏在日常里? 我们总以为日子是条直线,却忘了健康是串悬着的珠子,一颗松了,整串都在晃。 他现在呼吸匀了些,睫毛在眼下投出浅影。 我摸了摸他的手腕,脉搏跳得比在急诊门口时稳,像终于找回节奏的钟摆。 只是那两粒救心丸空出的抽屉角落,像在心里剜了个小坑——原来所谓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把风险藏进抽屉,直到藏不住的那天。 明早的彩超单会是什么样? 不知道。 但此刻他的手搭在我手背上,温度比刚醒时暖了些。 或许日子就是这样,在急诊室的惨白灯光里,在观察室的折叠床上,我们学着把“以后再说”,换成“现在就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