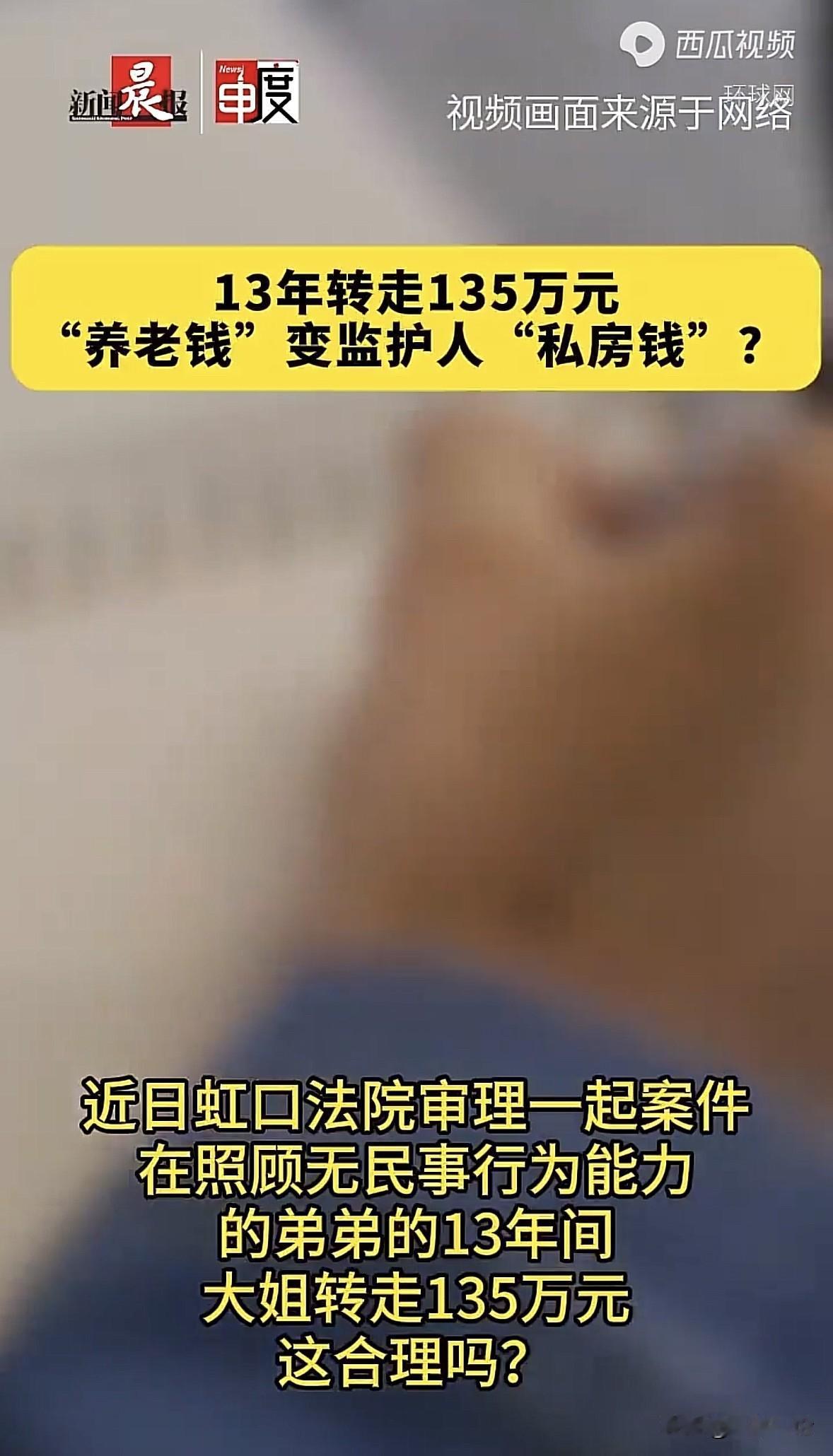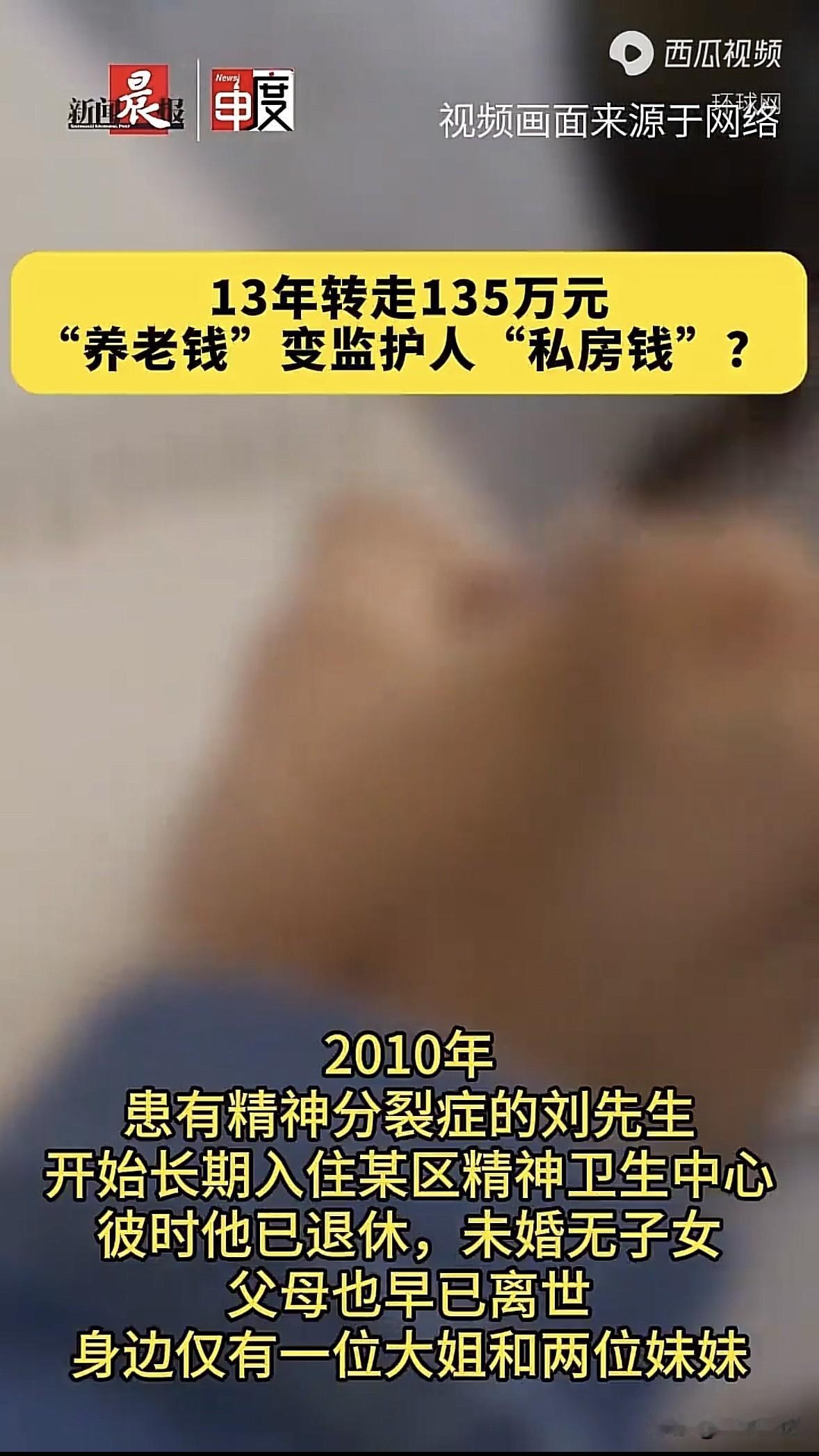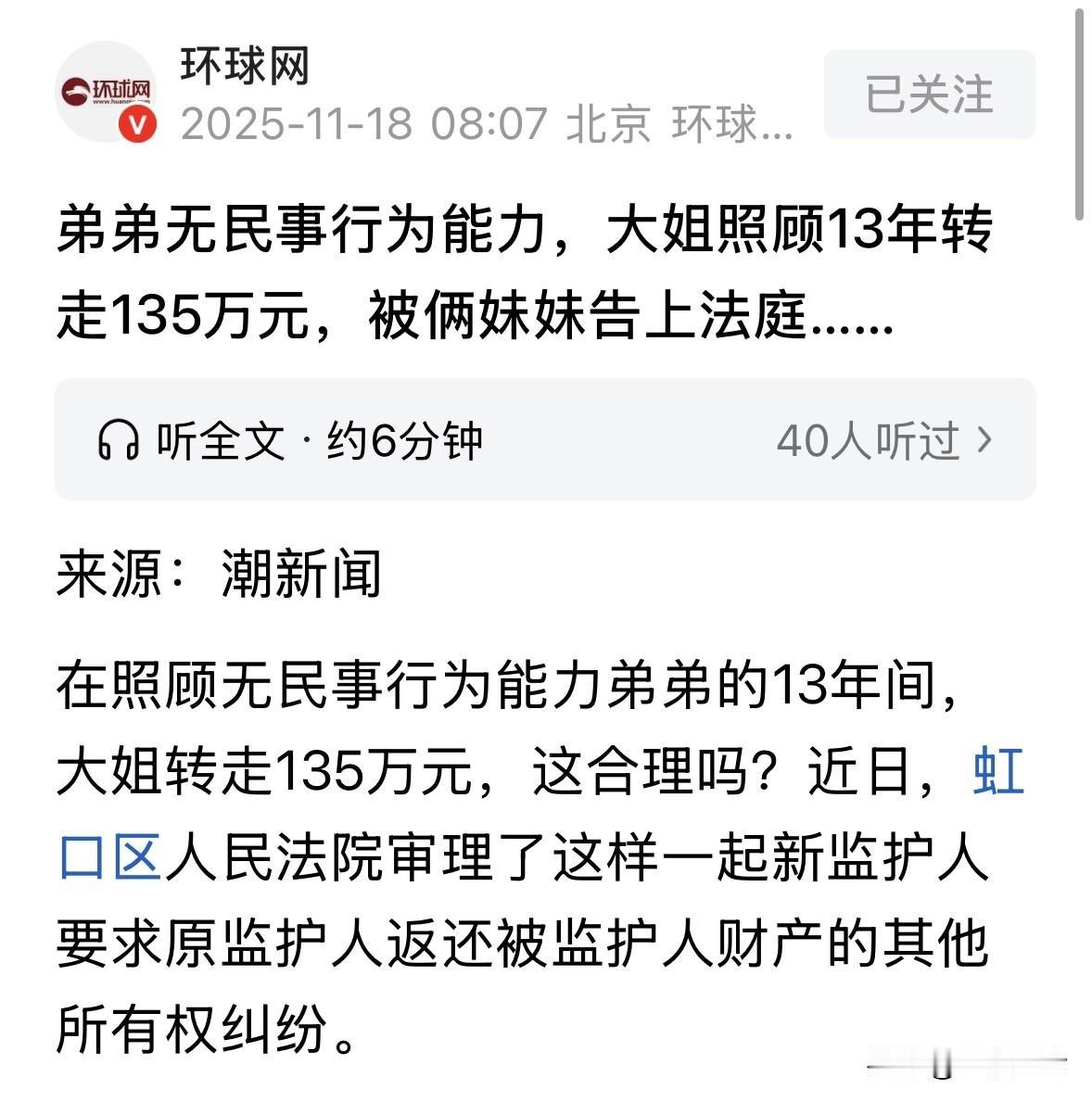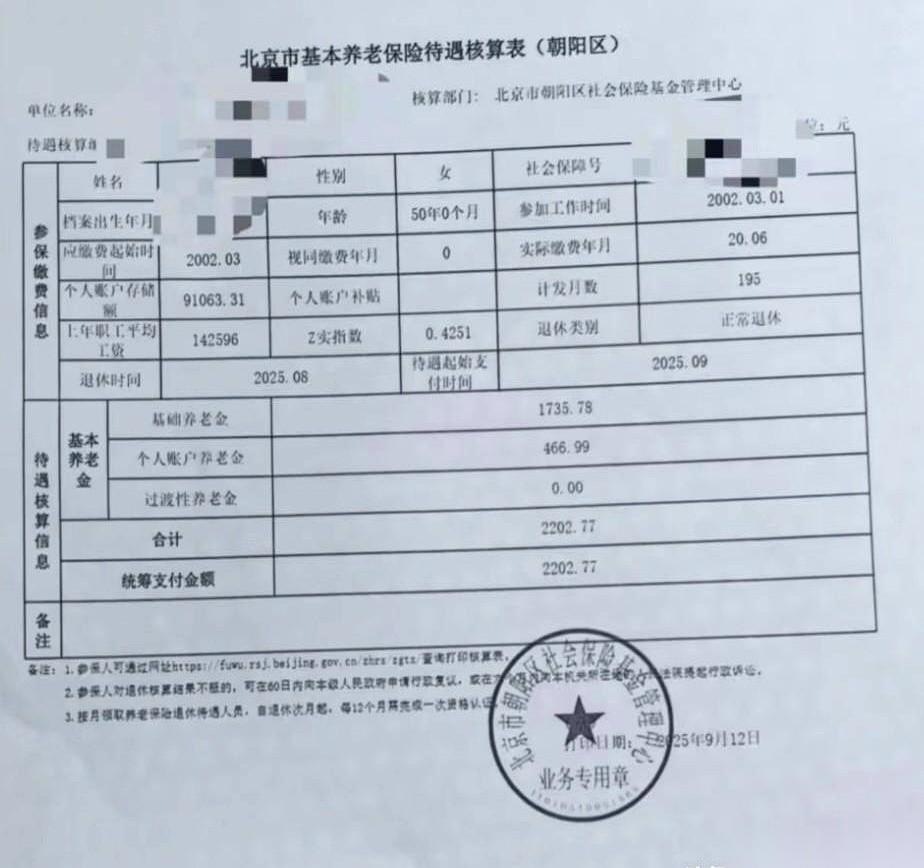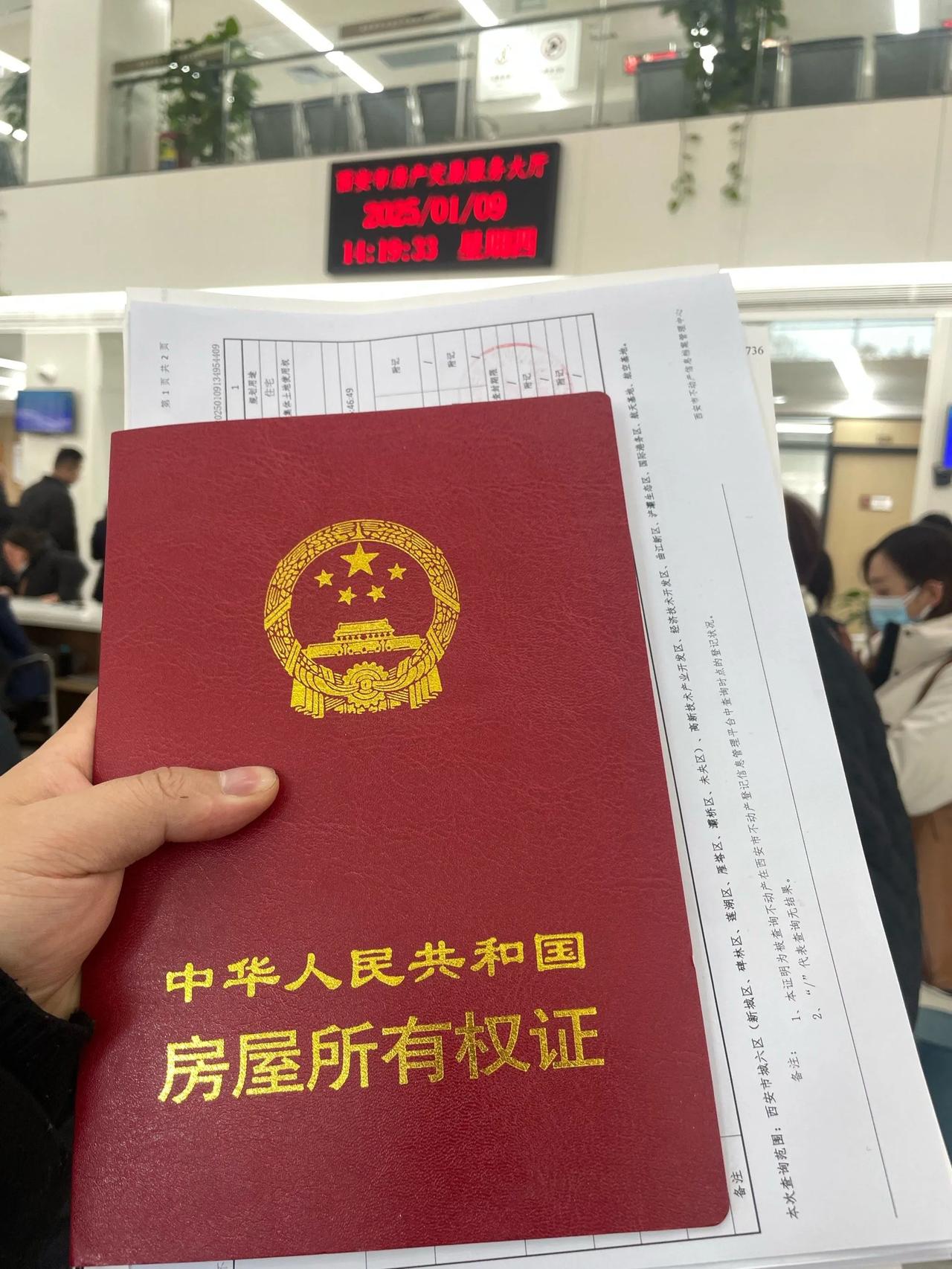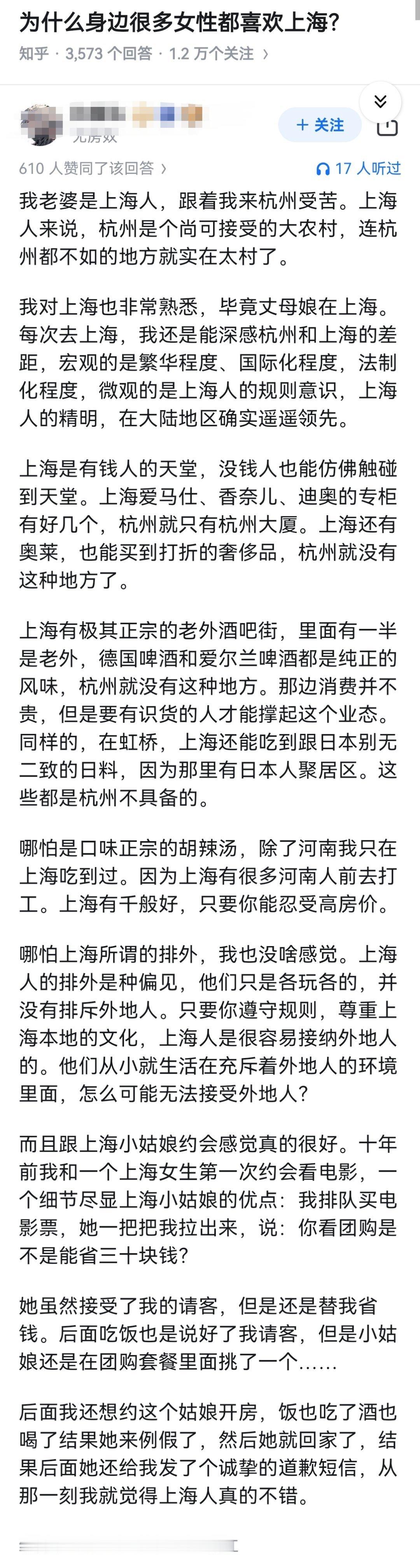上海,男子患精神分裂,常年住卫生中心,身边只有一个大姐和俩妹妹,男子每月领5000退休金,还有一笔不小的积蓄,他的财产全部由大姐掌管,后来,仨姐妹因为父母财产分配的事彻底闹掰,俩妹妹就申请变更为监护人,接管男子财产后俩妹妹惊讶发现,过去13年,大姐竟从男子账户里转走135万,她们诉至法院,对此,大姐的解释亮了。 2010年,患有精神分裂症的退休工人刘先生搬进了某区精神卫生中心。 他孑然一身,未婚无子,父母也已离去,只剩一个大姐和俩妹妹。 刘先生虽在病中,但经济上还算安稳,他每个月能领5000多的养老金,单位部分报销的护理费,再加上零零碎碎的车贴、残疾补助、敬老卡津贴,每月进账不少。 更难得的是,他患病前勤俭半生,攒下了不小的积蓄,足够让他安然度过后半生。 13年光阴,刘先生躺在病房里,在亲人的扶持中度过。 起初,姐妹仨人有商有量,决定由稳重的大姐一手接管刘先生所有银行账户、存折和各类证件,日常开支一笔一笔也由她记在账上。 俩妹妹对大姐也是信任有加,13年间从未对大姐的管家权提出半分质疑,仿佛这本就是天经地义,是大姐辛苦照料该得的体面。 然而,到了2023年,原本关系还不错的姐妹仨,在父母遗产分配的问题上爆发了矛盾。 几番对簿公堂后,姐妹仨人的关系彻底破裂了,这时,她们齐刷刷把目光聚集到了终于刘先生的财产上,这钱还谁来管理,怎么管理,成了彼此攻讦的新战场。 信任既已粉碎,2位妹妹随即向法院出手:申请宣告刘先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力主由她们接手监护职责。 法官审理发现,大姐经手刘先生账户资金流水中,取现频繁,甚至存在公私账户界限模糊的隐患。 在刘先生财产明细本身尚未厘清的情况下,相对置身事外的妹妹们,似乎成了眼下更合适的管理人选择。 最后,法院敲下法槌,宣告刘先生无民事行为能力,指定2位妹妹为监护人。 监护权移交了,银行存折和账户也交到了妹妹们手里。然而,当她们真正翻开旧账,一行行数字令她们倒抽一口冷气… 13年间,大姐从刘先生账户里提取和转走的钱款,竟累积达到135万! 2个妹妹以兄长代理人的身份,愤然起诉大姐,要求她全数吐出这笔巨款。 法庭上,俩妹妹质问道,这钱,多少是真正花在我哥身上了?绝大部分都被大姐揣进了自家口袋! 大姐的反驳称,我每月接他出来住,用的是他的积蓄租房,那房租一年比一年高,你们谁算过?还有他的日用花销、看病、其他房子的物业费……哪一样不是我默默贴钱撑着? 她更指妹妹当了监护人后才查旧账,说要告也只能告今年的账,我还得问你们要证据证明我私用了钱呢! 法官将争议聚焦于一点:大姐过去多年处分刘先生财产的行为,究竟是否越界?如果越界,又该退赔多少? 首先,刘先生的日常开销并非无底洞。他长年居住精神卫生中心,原有单位护理费报销政策加上稳定的退休金,已足以覆盖其常规生活需求,外出就医、居住或家属探望等额外开销。 大姐提出的律师费、诉讼费、装修费等大项开支,都没有可靠票据支撑其真实性与合理性,可以说记账混乱的像一团乱麻。 大姐和她的家人长期占用刘先生租金租住的房屋,甚至动用他的积蓄数十万装修,即便刘先生后期身体恶化无法外出,她们依旧占据该屋,租金照旧由病人账户支付。 同时,另一套本供刘先生偶尔外出休养之用的房屋,竟也被大姐拿去出租牟利。 凡此种种,早已逾越了监护职责所划定的“为被监护人利益”的边界。 13年间,刘先生从医院外出的次数仅有66次,每年看病也就6到8趟。就算把所有可能的聚餐花费都算上,合理开支的总量也绝对有限,更不可能全由刘先生一人承担。 在这个背景下,135万这个庞大数字早已突破了合理性的边界,大姐对刘先生财产权益的侵害,昭然若揭。 那么,从法律角度,怎么看待这件事? 《民法典》第35条规定:监护人应当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监护人除为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成年人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应当最大程度地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保障并协助被监护人实施与其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监护人有能力独立处理的事务,监护人不得干涉。 大姐在2010-2023年期间实际履行监护职责,但她的行为存在多处越界。 大姐将刘先生账户资金用于支付自己及家人长期居住的房屋租金、装修费用,甚至在刘先生无法外出期间仍占用该房屋,并将刘先生名下另一套房屋出租获利。 这些行为明显超出“为被监护人利益”的范畴,构成对监护职责的滥用。 最终,法院衡平考量各项因素,一锤定音:大姐对她处分财产行为的正当性未能充分证明,尤其大额花费严重缺乏凭证,她的行为确已构成侵害。酌情判决大姐向原告刘先生返还人民币70万元。 自此,这场纠纷尘埃落定,无人上诉。 对于这件事,你怎么看? 欢迎关注@一案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