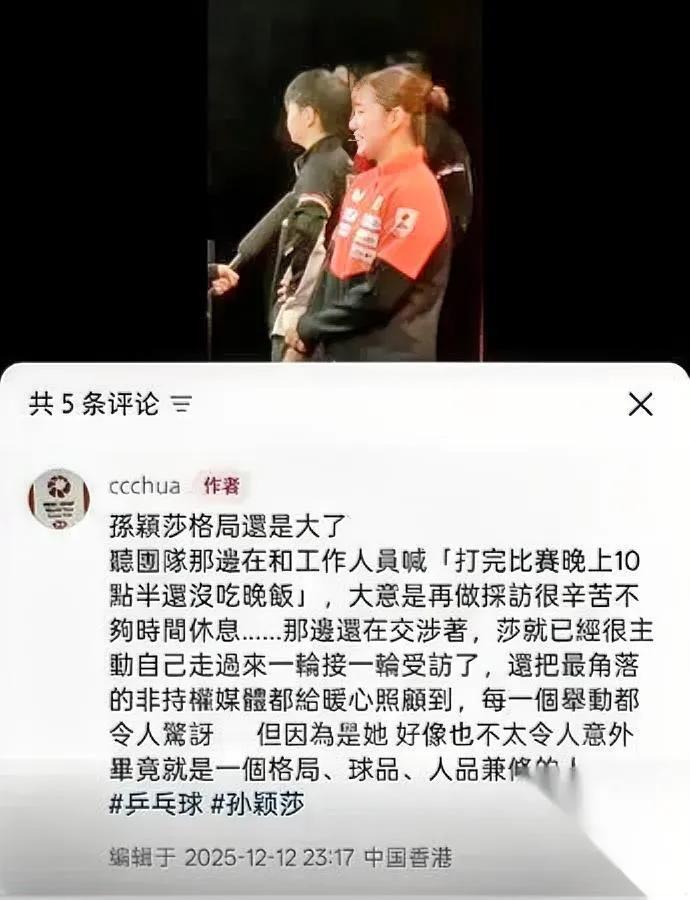八六年吧,突然一对夫妻,带着个孩子来找我,我刚参加工作,所有亲朋没人来"打扰"我,这三个人,突然来找我,不知有什么事?我问他们,男的说,他们路过我们这里,身上钱被偷了,午饭也没吃。男人说话时喉结上下滚动,女人则紧紧搂着怀里约莫五六岁的男孩,孩子眼睛直勾勾盯着我桌上吃了一半的烧饼。 八六年的春天,好像比往年冷一点。我刚在镇政府办公室坐稳,桌上的搪瓷缸还飘着新茶的热气,窗台上那盆仙人掌刚冒了个嫩尖——那是报到时同事送的,说“镇里风大,养点泼辣的”。 突然门被推开条缝,探进来半张脸。 是个男人,三十来岁,穿件灰扑扑的中山装,袖口沾着泥。后面跟着个女人,蓝布褂子,怀里紧紧搂着个孩子。三个人站在门口,像三棵被风吹得发僵的麦子。 “您……您是这里的同志吧?”男人声音有点哑,往前挪了半步,喉结在脖子上滚了滚,“我们……我们路过这儿,包里的钱,刚在车站被偷了。” 我愣了一下。那时候我才二十出头,刚从学校出来,亲戚朋友都知道我“刚上班,啥也不是”,没人来“添麻烦”。这三个陌生人,倒像是算准了时间似的。 女人没说话,只是把怀里的孩子搂得更紧了些。孩子约莫五六岁,头发有点黄,眼睛很大,黑葡萄似的,却不看我,也不看男人,就盯着我桌上那个吃了一半的烧饼——芝麻粒沾着点辣椒油,边缘烤得有点焦,是早上在巷口买的,没吃完就匆匆来上班了。 我刚上班没几天,工资还没发,抽屉里只有两块三毛钱,连自己都得省着花——这钱,给还是不给? 男人还在说,说他们从乡下来,要去县城看亲戚,现在连午饭都没着落。女人的手在孩子背上轻轻拍着,一下,又一下,像是在哄,又像是在按住什么。 我忽然看见孩子的小手——指甲缝里有点黑泥,却干干净净地蜷着,没去碰妈妈的衣服,也没哭闹。就那么定定地看着烧饼,嘴角好像动了动,又抿紧了。 “饿了吧?”我没等男人说完,抓起桌上的烧饼,又拉开抽屉,把那两块三毛钱捏在手里。走到门口时,孩子的眼睛终于抬起来看我,亮得像淬了光。 “这个你先吃。”我把烧饼递过去,孩子没接,怯生生地往妈妈怀里缩了缩。女人这才抬头,眼眶有点红:“这……太谢谢了,同志,我们……” “钱拿着。”我把钱塞给男人,他的手很糙,全是老茧,捏着钱的时候抖了一下。 他们走的时候,孩子忽然从妈妈怀里探出头,举着啃了两口的烧饼,含糊地说:“谢谢叔叔。”芝麻粒粘在他嘴角,像颗小星子。 后来同事知道了,拍着我肩膀笑:“你呀,八成是碰上骗子了!现在这种‘钱被偷’的把戏多着呢。”我没说话,只是想起孩子盯着烧饼的眼神——那不是装的,饿肚子的眼神,我小时候在乡下见过太多了,像小猫盯着鱼干,直勾勾的,带着点可怜的急切。 那时候我刚工作,每月工资三十七块五,自己省吃俭用,连买本《读者文摘》都要犹豫半天。可那天看着那个孩子,突然想起我妈常说的:“人这辈子,谁还没个难的时候?能帮一把,就别冷了人心。” 那天下午,窗台上的仙人掌好像又绿了点。 后来我再没见过那家人。只是偶尔路过巷口的烧饼摊,闻到芝麻和炭火的香,总会想起那个八六年的春天——想起男人滚动的喉结,女人发颤的手,还有孩子嘴角那颗亮晶晶的芝麻。 现在遇到路边求助的人,我还是会多看两眼。有人说“别傻了”,我就笑笑——或许真有骗子,但总有些眼神,是藏不住的;总有些饿,是装不出来的。 就像那个孩子,他没说“我饿”,可他盯着烧饼的样子,比任何话都让人心里发紧。 那天剩下的半块烧饼,我没再吃。下班时包好,放在了办公室门口的石墩上——万一,还有别的“路过”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