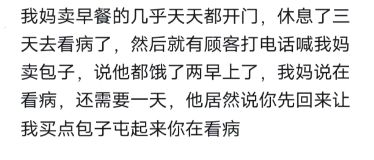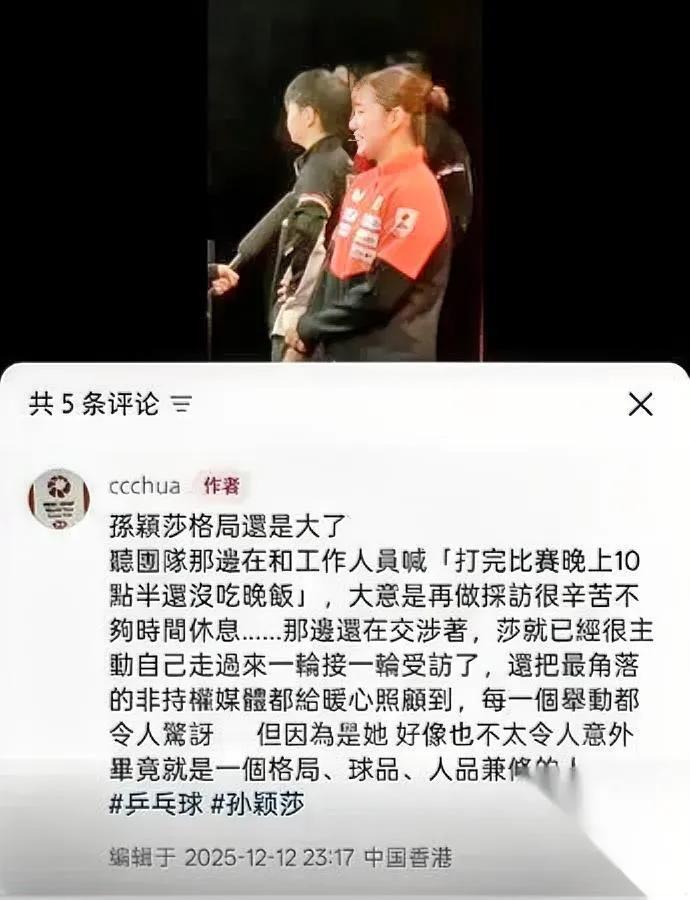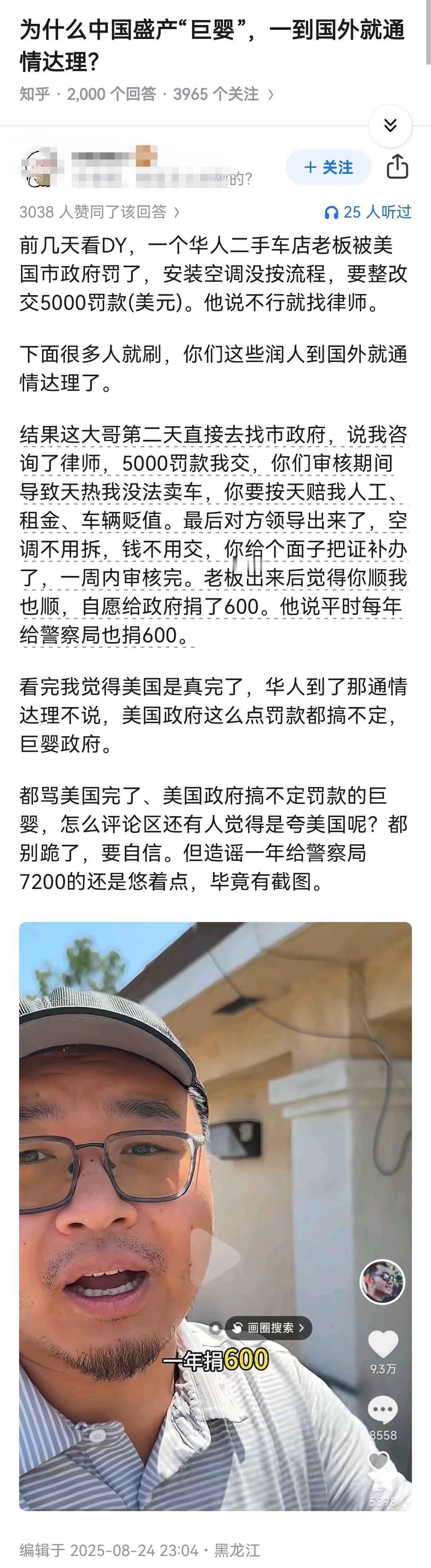女婿把筷子“啪”地拍桌上了,眼睛瞪着我:“妈,那钱是我爸妈给我们小家庭的,跟您家、跟您儿子没关系,今天我把话撂这儿,这钱,谁也别想动,要动,除非我死了,或者离婚。”我手里的汤勺“当啷”掉在碗里,排骨汤溅了一桌子。 傍晚六点半,厨房飘来排骨汤的香,我把最后一盘炒青菜端上桌时,女婿正低头给我那刚毕业没找到工作的儿子发微信,手指在屏幕上戳得飞快。 我坐下时,故意把汤勺在碗沿磕了磕,瓷勺碰着白瓷碗,发出轻脆的响。“阿强昨天说想创业,差十万块启动资金,你看……”话没说完,女婿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指节泛白。 我握着汤勺的手开始抖,这汤是按他喜欢的口味炖的,加了枸杞和玉米,他以前总说“妈炖的汤比饭馆香”,今天怎么就变了脸? 突然“啪”一声,筷子拍在桌上,木纹被震出细碎的白痕。他抬眼瞪我,眼里的红血丝像刚熬过夜:“妈,那钱是我爸妈给我们小家庭的,跟您家、跟您儿子没关系。” 我手里的汤勺“当啷”掉在碗里,排骨汤溅了一桌子,油星子溅到他手背上,他没躲,反而往前倾了倾身:“今天我把话撂这儿,这钱,谁也别想动,要动,除非我死了,或者离婚。” 我愣了愣,想起上个月他出差,我偷偷拿他工资卡给阿强转了五千,被他发现后冷战了三天——那时我以为是小摩擦,现在才明白,那是他在给我留体面。 钱是他爸妈卖了老家房子凑的,去年我们搬新家时给的首付,他当时红着眼圈说“妈,这是我们小家庭的根”;我那时只觉得他客气,没承想是刻在骨子里的界限,像他腕上那块旧手表,时针分针永远走在自己的轨道里。 排骨汤还在冒热气,溅在桌上的油星子却像凝固的疤,儿子的微信消息还在女婿手机屏幕上亮着,他却再也没看一眼,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摔门走了,楼道里的声控灯跟着灭了两盏。 那晚之后,女婿再没登过我家门,阿强的创业梦也黄了,我对着空荡荡的餐桌喝汤时,总听见汤勺掉在碗里的“当啷”声,比那天更响,像在敲我的心。 后来才懂,家庭像碗里的汤,各有各的火候,硬要混在一起,只会溅得谁都烫;可我那时总觉得,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做什么? 现在厨房的排骨汤凉透了,我用那把摔出豁口的汤勺舀了一勺,没什么滋味——原来有些界限,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就像那碗没喝完的汤,凉了,就暖不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