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一生最大的遗憾:年薪10000美元,却没来得及借钱给杜致仁。 杨振宁,外头人看他,顺风顺水,三十多岁就拿了诺贝尔奖,五十岁站在清华的黑板前,八十多岁了还在讲课,跟神仙似的,看着什么都圆满了,其实心里头有个疙瘩,那个没能救回来的小舅子,搭进去一辈子都换不回来。 那事是1956年,普林斯顿的雪还没化,杨振宁家里,桌上信纸摊着,旁边的论文写了一半,那封信来回看了三遍,没马上回,等到处找人凑钱寄出去的时候,杜致仁那边,人已经不在了。 哈佛有个叫杜致仁的,二十二岁,家里管得严,学习也好,是个稳当孩子,杜聿明的大儿子,杜致礼的亲弟弟,也就是杨振宁的小舅子。 1947年考进哈佛工程系,那会儿杜家还挺风光,父亲手下有兵,母亲在美国陪着两个孩子,日子看着亮堂堂的。 一年功夫天就变了,父亲成了俘虏,母亲带着小的去了台湾,美国这边的钱一下就断了,姐弟俩像断了线的风筝。 杜致礼没辙,转到学费便宜的圣文森学院,还能打工,杜致仁在哈佛那地方开销大,当助教,洗盘子,扫实验室,能干的活都干了,就差最后一年,那点钱实在顶不住了。 他母亲知道儿子快撑不下去了,脸皮都不要了,去求蒋介石,批下来一千美金,还分两次给,学费总共差三千,这点钱明摆着不够,只能再写信给女儿。 杜致礼那时候跟杨振宁结婚六年,日子过得紧巴巴,杨振宁刚换工作,年薪一万美金,算不上富裕,手里没什么闲钱。 信一到,杜致礼的心就沉下去了,有种家要散了的感觉,找杨振宁凑钱,杨振宁直接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又找同事借了些,第二天一早就把汇款单填了,怕路上慢还专门发了电报。 钱刚汇出去,哈佛那边的消息也已经在路上了,杜致仁因为学费的事,课被停了,信又一直没人回,就留了张纸条,姐,我撑不住了,对不住,三天后在宿舍吃了药,波士顿的雪下得很大,学校记录是镇静剂中毒。 杨振宁手里还捏着那张汇款单,就站在窗户前面,外面下着雨,他老婆在哭,他站着一动不动,钱没了还能再挣,时间这东西不等人。 他后来写过,最痛的不是没钱,是信差慢了,钱差了三天,一条命就没了,从那以后杜致仁这个名字再也没人提过,别人问起来他就沉默,家里的账本信件他翻起来手都抖。 台湾那边,死讯传过去,母亲曹秀清整个人都垮了,对蒋介石彻底死了心,后来去了美国跟丈夫团聚,再也没说过党国的事。 杜聿明在大陆,消息是电报传到管理所的,他当场就晕了,醒过来只说这辈子再也不见他们,这事彻底改变了他,开始反思,改造也积极了,历史上都说,杜致仁的死,是推开杜聿明心里那扇门的手。 杨振宁这边,这根刺扎得最深,公开场合从不提,每次有人问他有什么遗憾,他都是沉默,活到这么大年纪,还是放不下。 1957年去瑞典领奖,国王把奖章递给他,全场都在鼓掌,他笑着鞠躬,心里的那个坎儿还在,有记者问他遗憾什么,他说没能帮上一个需要帮助的年轻人,当时没人听懂,他老婆明白,他这话是跟天上的人说的。 信里写着,这是一辈子的债,他办公室有张老电报的复印件,纸都黄了,上面写着,款已寄出,请安心学习,姐夫杨振宁,寄出去的第三天,人没了。 五十年代,钱能凑齐,就是通信慢,国际汇款要十天,信走海路得两个礼拜,一步走错,就是一辈子,杜致礼后来经常念叨,要是早点去借钱,或许就是另一条路了。 杨振宁没怪过杜致礼,也没怎么安慰,就是把自己埋进实验室,天天早出晚归,好像做实验能把那口气给补回来。 杜致礼2003年去世,杨振宁整理东西,卧室里有个木盒子谁都不让碰,里面就三样东西,杜致仁的哈佛学生证,一封没寄出去的信,还有那张1956年的汇款收据,他自己默默把盒子盖上了。 就那一次错过,成了他后半辈子的闹钟。 后来有次讲座,学生问他怎么看待遗憾,他停了很久,笑了笑,说遗憾是不会消失的,但能让人明白要珍惜时间,千万别等,这话是说给学生听的,也是说给他自己听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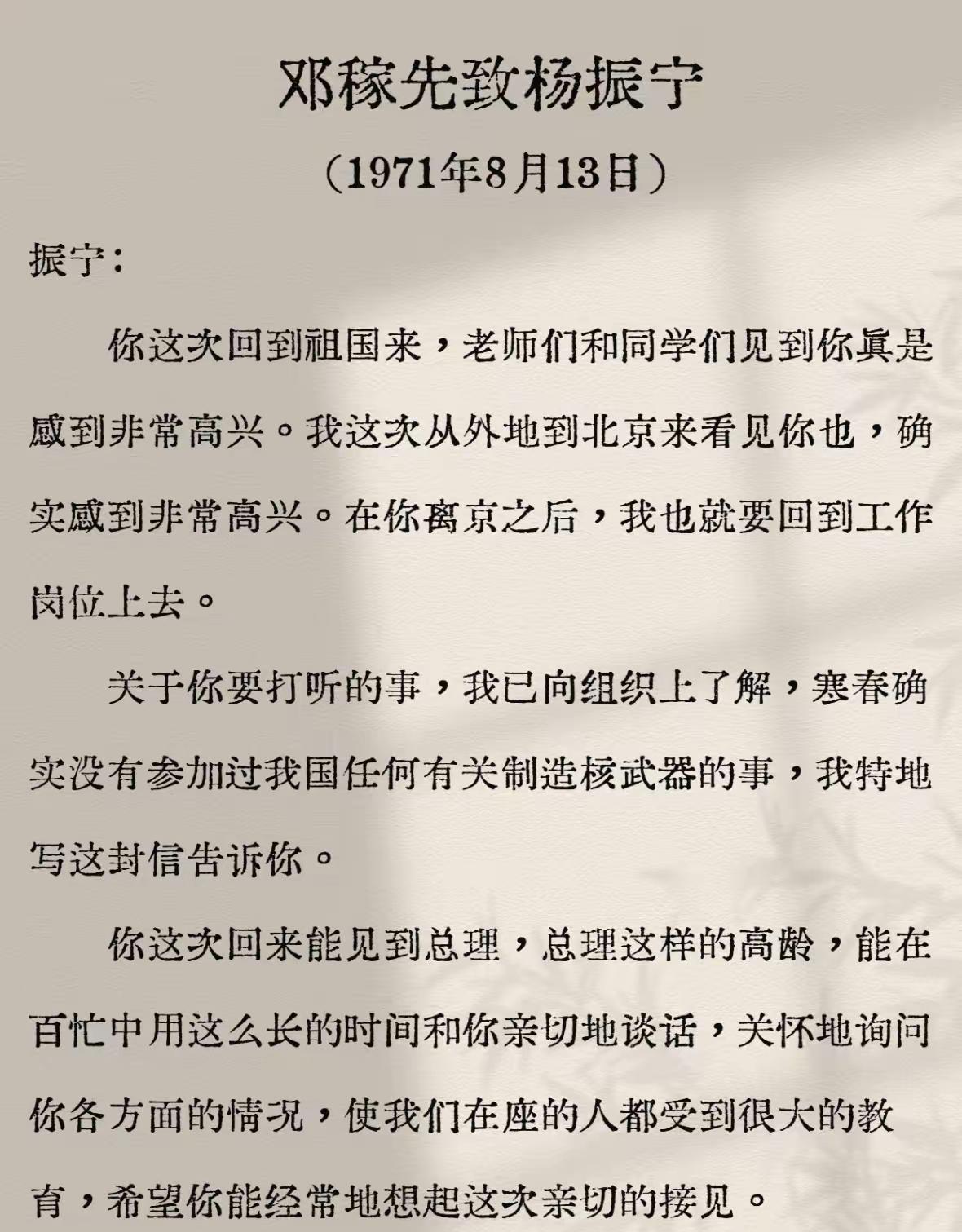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