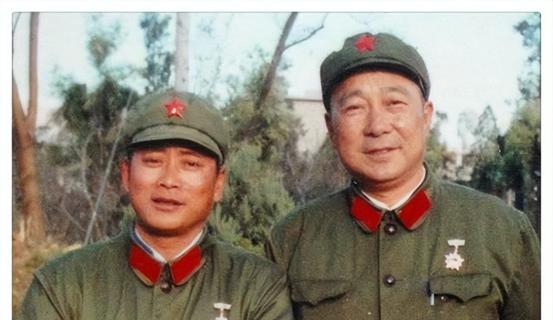从越战中,走出来的五大名将,个个都是军中骨干 “1984年7月12日,老班长,你当年在谅山指挥的那一仗到底怎么赢的?” 探亲探到前线的年轻参谋倚在战壕口,小声发问。灰尘里,老兵把钢盔往下一压,只回了四个字:“胆大、心细。” 一问一答之间,越南边境炮声渐远,然而那场持续十年的较量早已在共和国军史上烙下深痕。正是在这片丛林与山地交错的战场,一批后来撑起中国军队脊梁的将领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浴火成钢。 1979年2月17日炮声打响时,他们的军衔并不耀眼,有的是团职,有的是连长甚至普通参谋,没人料到日后他们会站在更高指挥席上勾画国防蓝图。但战争一旦开始,资历、年龄、出身都退到一边,冲锋时谁扛着背囊往前冲,胜败就写在谁的履历表上。湖南安化籍的李作成就是那个把“尖刀”两字扛到极限的人。连夜穿插、雨中拔点,他的连吃下了敌军最硬的一口骨头。战后,尖刀英雄连的旗子从广西前线直送北京,紧接着,他被推荐到更大的舞台——先是师、后是军、再是区,从南宁市郊到川西雪山,都有他的足迹。2015年佩戴上将肩章时,他仍喜欢把当年的绿色锈迹钢盔挂在办公室墙上,据说每逢新人来汇报工作,他都会敲一下那顶旧盔,提醒对方什么叫真正的“生死令”。 比起李作成的锐气,贵州思南人廖锡龙身上多了一丝学院派味道。1963年入伍时,他拿着比同龄战友更漂亮的文化成绩单,很快被挑去高等军事学院深造。越南边境炮火燃起,他已是副团长。2月下旬,他的团顶着敌人“火力封锁圈”把高地咬住,七昼夜没让出一寸。后来,同一批副团长里,有人留守原地,有人调至机关,他却被直接拉去负责后勤。有人觉得这像“冷板凳”,可转眼十年对峙,正是他统筹的大型野战物资滚动储备,保证了前线弹药与口粮不断线。等到2002年他坐上总后勤部部长的位子,熟悉他的老兵常说:“那年边境阵地夜里缺水,他扛着马口铁皮桶爬陡坡,部长帽子就是那时打下的底子。” 山西原平出身的傅全有,资历最老。1946年立起一杆红缨枪加入部队,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国防现代化改革三大阶段全都赶上。1979年对越反击,他的身份是某军作战处副参谋长。人常笑他“老参谋”,可真正的突破口恰是他找的。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敌人依托纵深密集火网,正面突击屡屡受挫,他大胆主张“斜插穿心”,从侧翼切断公路,断粮、断救护、断退路,最终令对手不得不弃阵而逃。这份灵活思路后来延伸到部队体制改革上:臂膀更短,拳头更重。1995年出任总参谋长时,他把那份手写战役示意图留在机关专门展柜,俨然一张“及时行变”的活教材。 四川三台的梁光烈被誉为“硬骨头司令”。1955年,他十四岁,跟着征兵卡车一路颠到部队。二十多年磨砺,让他练就一身“顶不住就再顶一下”的狠劲。1984年老山、者阴山局部反击中,他是第二十军五十八师副师长。前沿阵地海拔一千六百米,坡陡林密,越军常用坑道偷袭。他干脆带工兵炸塌对方暗堡,用三天时间凿出“野战机场”供直升机起降,极大改善了前线的弹药运补。后来担任国防部长,有记者问他最自豪的事是什么,他答得干脆:“那三天每小时都想睡,但一想到战士们能喝上热水,就不困了。” 五人中,山东龙口汉子张万年最像传统意义上的“虎将”。1945年入伍,血战孟良崮、解放南京、渡江南下,他样样不缺。越战爆发时,他指挥第43军127师。该师是出了名的“钢七连”“火箭炮一营”所在部队,历史名气大,现实难度也大。2月24日凌晨,127师分三路翻山越岭突击,主峰拿下,可敌人反扑凶猛。张万年钻进最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完敌阵后只说一句:“准备用大刀了。”当晚全师短兵相接,四战四捷。胜利电报发到军委,指挥所却只回了一句“无伤亡统计,先追敌”。当年种下的凶悍作风,十余年后让他接连坐上广州、济南两大军区司令的位置,再往后,总参谋长、军委副主席的担子向他递来也就顺理成章。 有人好奇,十年边境对峙,到底给这些人留下了什么?答案并不复杂:一是实战决策能力,二是对于现代化供给、训练与体制的深层理解。尤其进入90年代,信息化浪潮扑面而来,他们正是凭那段山地丛林里的摸爬滚打,为陆军改装、合成旅改革、后勤滚装化运输等新思路打下了现实依据。有意思的是,当别国军校分析中国军队转型路径时,越战战场采集到的数据经常被当作“第一手”。换句话说,那片边境山谷不只淬炼了个人,也提供了实验场。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五位主角,吴铨叙、钱树根、徐永清、王祖训、李乾元、张海阳等一批上将同样在炮火里磨炼成才。他们遍布陆、海、空、后勤、武警多个序列,成为后来联合训练、远程投送、强军目标推进中的关键枢纽。试想一下,如果缺少那段山林与沼泽的历练,纸面兵力再庞大,对现代化战场的理解也难有如此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