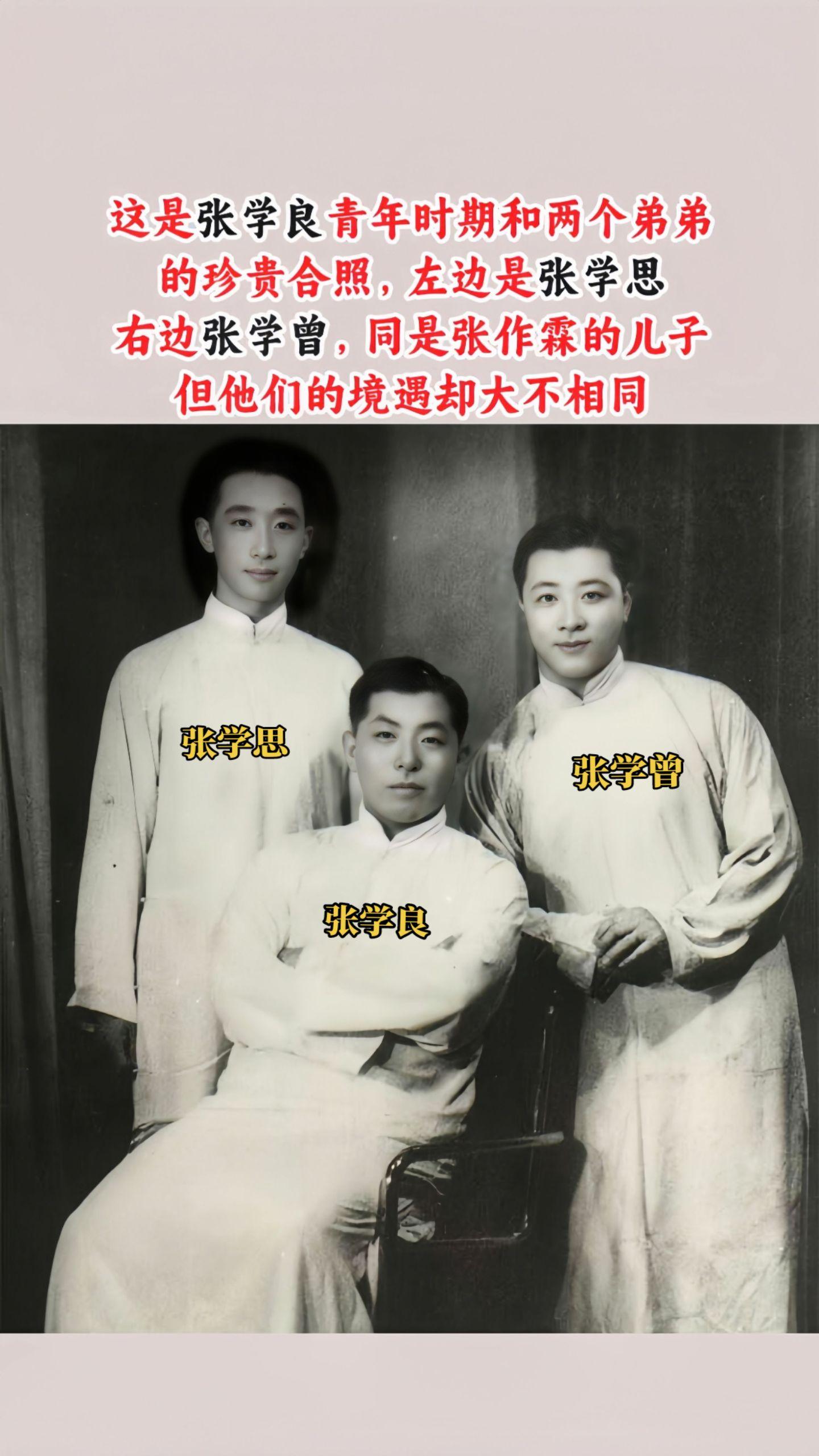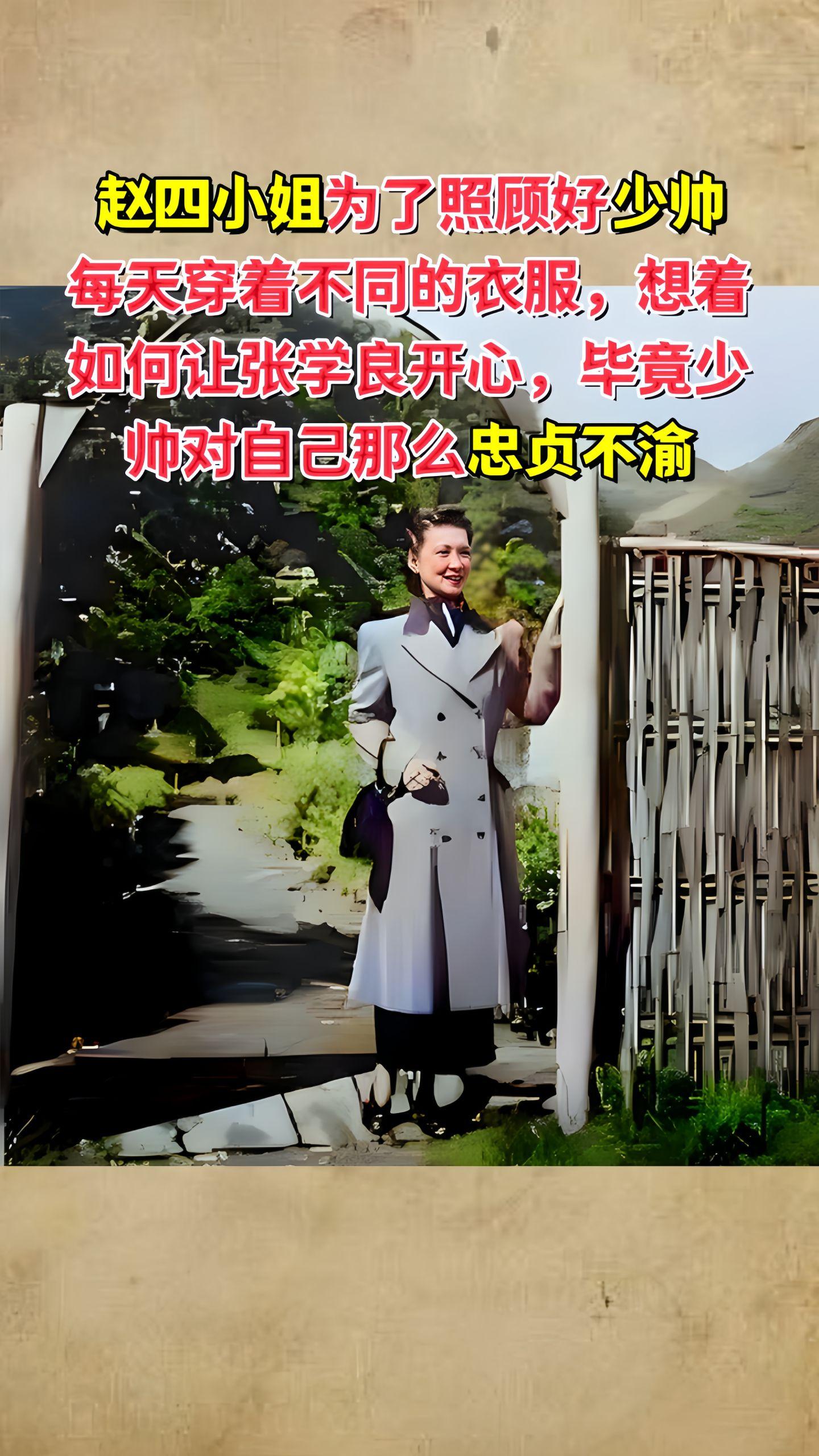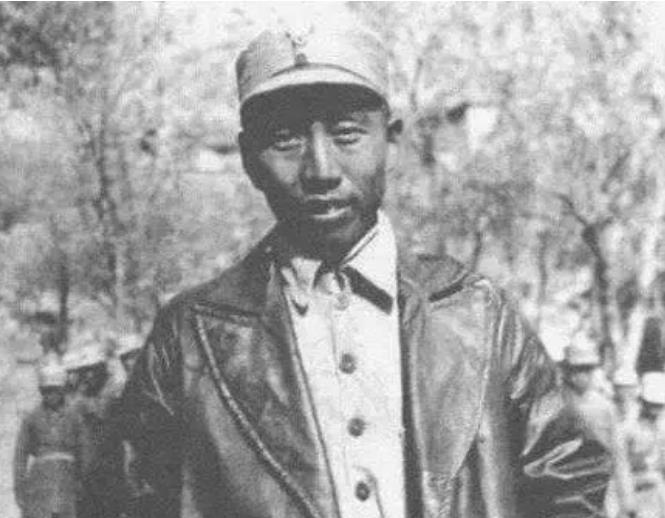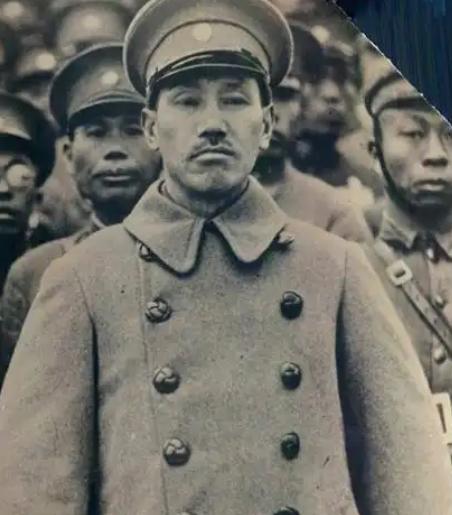1939年7月的一天,张学良在江边钓鱼,见一位叫高应欢的农民在用筝网捞鱼,便上前搭话聊天。在交谈中,张学良了解到高应欢家中人口多,生活困难,老母久病在床,无钱就医,非常同情。张学良当即取出3块银元,送给高应欢说:“我身上仅留下3块钱,你就收下吧。” 高应欢被张学良的关怀所感动,但他说什么也不肯收张学良钱。而张学良却执意让高应欢收下钱,还好言相慰。高应欢在盛情之下,只好收下张学良送的3块银元,激动得热泪盈眶。 不久后的一个夜晚,沅江上游下了大暴雨。顿时,平地三尺洪水,冲毁了沅江两岸许多房屋,不少人畜被卷入江中,顺着洪流向下江冲来。第二天,洪流殃及沅陵境地。 清晨,张学良起来,站在望江楼上用望远镜观看沅江,发现洪流中有些人骑在木头上或站在屋背上求救。而岸上的人竟不顾水中人的危难,只顾着在江边打捞财物。 张学良见到这种场景,心急如焚。他喊来看管他的特务队长刘乙光队长和宪兵连长童鹤连,一反平常的神态,以命令的语气对俩人说:“赶快集合队伍下山,到江上救人。” 于是,张学良和刘乙光、童鹤连带着人赶赴救灾现场,并亲自指挥救人。张学良向大家说:“凡是有木船的群众,都要先救人,救得一人,奖银元5块,由我当场兑现!”在张学良的鼓励下,大家救上了许多老百姓。当便衣队和宪兵把老百姓转移到安全地带后,张学良并不食言,慨然从自己的积蓄中给每个便衣、宪兵5块银元,供他们买衣服。 1939年秋,湖南时局紧张,日军占领武汉后,直逼长沙。戴笠给刘乙光拍电报,指示将张学良转移到贵阳。路线是:沅陵、辰溪、芷江、黄屏、贵阳。在转移途中。为了防止遭受袭击或劫持,宪兵连的十多辆卡车分做两处:一部分在前面引路,一部分在后面押队。卡车座楼顶上都架着机关枪,随时准备对付突然发生的情况。在转移途中,车队艰难地爬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张学良、于凤至夫妇在车上饱尝了长途颠簸之苦,身体像散了架一般。 在这次转移中,张学良虽没有发生身体方面的问题,于凤至却经受不住,加上一路受到不少惊吓,身体很虚弱。刘乙光的车队到达贵阳后,张学良夫妇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暂住。刘乙光立即与军统局戴笠联络,得到命令:将张学良转移到距贵阳以北60里的修文县龙岗山阳明洞幽禁。 刘乙光按着戴笠的指示,率车队载着张学良抵达贵州修文县城北的龙岗山阳明洞。此处岩石嶙峋,古树参天,洞内宽敞明亮,可容纳百余人,石凳石桌,不假修凿,自然生成。 在明朝正德元年(1506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不满宦官刘瑾陷害无辜,与之分庭抗礼而得罪朝廷,被谪为龙场驿(今修文县)当驿丞,他在龙岗山东洞讲学,教当地民众学习文化,自称阳明先生,故后人称此洞为阳明洞。洞前面有两棵挺拔苍劲的柏树,据说就是王守仁亲手栽种的。龙岗山上树木茂密,巨石矗立,其间有王文成公祠、何陋轩君子亭等古迹。 刘乙光把张学良夫妇安排在王文成公祠内右侧楼下的房子里,派20名便衣队员住在祠内,执行“保卫”任务。从张学良来到龙岗山起,这里便被划成禁区,防范不测。刘乙光将宪兵连的大部分兵力布置在从县城至山脚的第一道防线上;在第二道防线上,兵力分布在山的四周,分别设岗亭看守;而便衣队大都布置在第三道防线,负责阳明祠内外之安全。每到夜晚,张学良卧室门口还要加设警卫。 张学良来到这里不久,就对龙岗山发生兴趣。这里野兽很多,特别是獐子、野猪、山兔最多。为此,张学良极喜欢上山打猎。他每次出去打猎,都有两名副官和便衣队员6人跟随。早晨8点钟出猎,太阳下山才归,中午饭由厨师把饭菜担送到山野猎场。 张学良最喜欢吃烘煎的野味,在山洞里烧起一堆柴火,把打来的野兔、山鸡或獐子烤得滴油飘香。随着打猎兴趣的增加,张学良开始不满足于打野兔、野鸡和獐子,希望撞到“大家伙”过过瘾。所以,在打猎时,张学良总是拼命地往森林里钻,害得跟随其后的副官、便衣队员个个气喘吁吁。 有一天,张学良打猎到龙岗山西北坡,听到树林深处传来野猪的哼叫声,欣喜地跑过去。“随从”们见此情景,不敢大意,立即紧随其后钻进树林。此时,张学良看到三头凶猛的野猪围着一棵老松树拱土。于是,他端枪向猎物一步步逼近。“随从”们怕野猪受惊发狂,伤害少帅,都端起卡宾枪瞄准野猪,以防不测。 这时,张学良已躲在靠近野猪的树后,“啪啪”两枪,一头野猪应声倒在地上,另两头野猪见势不妙,疯狂地逃进树林深处。“随从”们跑到野猪面前,只见它头部和腹部各中一弹,都称赞副司令的枪法准。 张学良笑了笑说:“多亏这支枪是双筒的啊!”这头野猪是他打猎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野兽。便衣队员们轮流抬着猎物回到驻地,剥掉猪皮,挖出内脏,净肉有百余斤。张学良只留下野猪一条后腿,剩余的肉都给便衣队和宪兵连食用。这天晚上,他们高兴地吃了一顿野猪宴。 在阳明洞软禁期间,打猎成了张学良消磨时间的一个方式,除此之外,他潜心研究明史,几年下来 俨然成了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