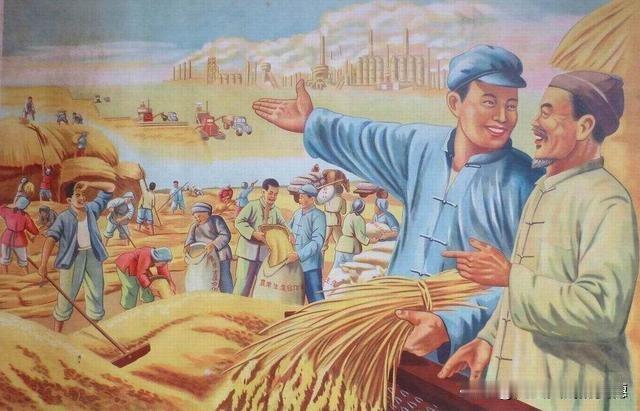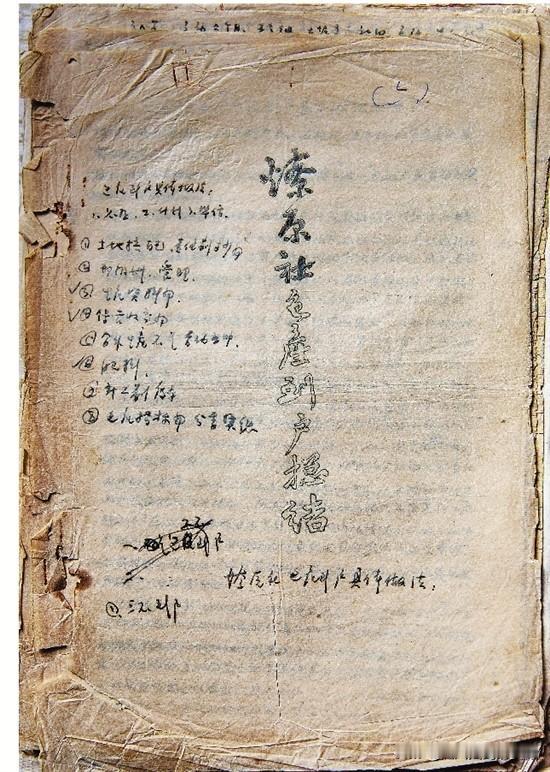万里:只有分田到户,农民才有积极性!农业不能学大寨,要学小岗!包产到户责任制的诞生,绝非偶然之举,它是基层广大干部与群众历经反复探索、借鉴、对比、总结经验后的智慧结晶。自留地的存在为包产到户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农业学大寨搞了那么多年,可农民还是没解决温饱!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能够有效提升产量的农业政策,其成效已被无数生动的事实所验证,这一点无可争辩,亦不容忽视。然而,遗憾的是,仍有一部分同志对其本质属性存在误解,混淆了包产到户与单干的概念,错误地将二者等同视之,并进一步错误地推断,一旦农业生产与“包”字、“户”字挂钩,就意味着方向与道路的选择出现了问题。事实上,今日的包产到户与昔日的单干在本质上有着天壤之别。首要区别在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包产到户是在公有制框架下进行的,而单干则是私有制的体现。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一书详尽地描绘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1956年11月19日,这个表面看似平淡无奇,实则蕴含深意的日子,中共温州地委的机关报《浙南大众报》上,一篇名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犹如一枚重磅炸弹,激起了滔天巨浪。该文措辞严厉,对燎原社推行的包产到户政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将其视为对合作社新兴挑战的“懦弱逃避”,指责这种政策是将集体经营的先进模式倒退回了分散经营的老路。 在这股汹涌的舆论洪流中,李桂茂,这位敢于担当、勇于探索的改革先驱,挺身而出,犹如中流砥柱。在地委会议的激烈讨论中,他不仅与《浙南大众报》的编辑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更是向地委领导呈上了一份正式且充满激情的申诉。他的声音虽然孤单,却穿透了黑暗,为改革的航船指引了方向。 在座谈会上,省委副书记林乎加以深邃的洞察力,对戴洁天等人的汇报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责任到户,其本质是好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巧妙地解决责任制的问题。”随后,他对永嘉提出的四句话进行了巧妙的调整,将“统一经营”置于首位,其次是“三包到队”,再者是“定额到丘”,最后是“责任到户”。这一调整,不仅是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明确肯定,更为其后续的推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实践路径。 紧接着,1957年1月27日,在林乎加的鼎力支持下,《浙江日报》全文发表了李云河的报告,这一举动无疑为包产到户政策正名,使其从地方性的尝试一跃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瞩目的焦点。 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践,实际上是对后来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次成功预演。与潘桥的个人专管地段仅停留在联地而未联产的初步尝试相比,燎原社则更进了一步,实现了联地到人与联产到人的完美结合。在这种模式下,产量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形成了一种紧密的利益共同体。这一创新之举,加之此前三次试验的宝贵经验积累,共同勾勒出了联人——联地——联产的清晰发展脉络,为中国农村的深化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和启示。 提及南街村,这个与中原小县临颍县县城仅一街之隔的村落,其改革历程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南街村话语》一书以生动的笔触,记录了南街村独特的干群关系和村民对村领导王洪彬的深厚情感。王洪彬以其真挚的情感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赢得了村民的衷心信任和拥护。 1986年至1989年间,南街村村民自发地将责任地交回村集体,这一壮举不仅彰显了村民对集体经济的坚定信任,也反映了他们对土地那份深沉而特殊的情感。南街村的故事,再次证明了中国农民与土地之间那种难以割舍的血肉联系,以及他们在改革浪潮中勇于探索、不懈追求的精神风貌。 然而,南街村实行的集体经济体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区域性群众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形式,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从包容性发展的角度来看,一个健康、可持续的经济体系需要多种所有制形式协调共生,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包容性发展从根本上强调人的自由发展。而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往往难以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不仅会阻碍资源的合理流动和配置,还会抑制劳动力的自由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发挥。 从宏观层面分析,单一集体经济体制的管理体系往往缺乏层次的独立性和灵活性。以南街村为例,以王宏斌为核心的“三大班子”对南街村的各项事务进行全面管理。这种幅度过大、层次过少的管理体系不仅增加了管理成本和行政成本,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非生产性浪费。 从微观层面来看,单一的集体经济体制缺乏有效的竞争和激励机制,导致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在南街村集中计划下的生产模式中,劳动者在既定的框架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机械的工作方式取代了自主创新的精神,这种隐形的人力资源抑制作用严重削弱了南街村经济体的活力和竞争力。 综上所述,无论是燎原社的包产到户实践还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中国农村改革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宝贵篇章。它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