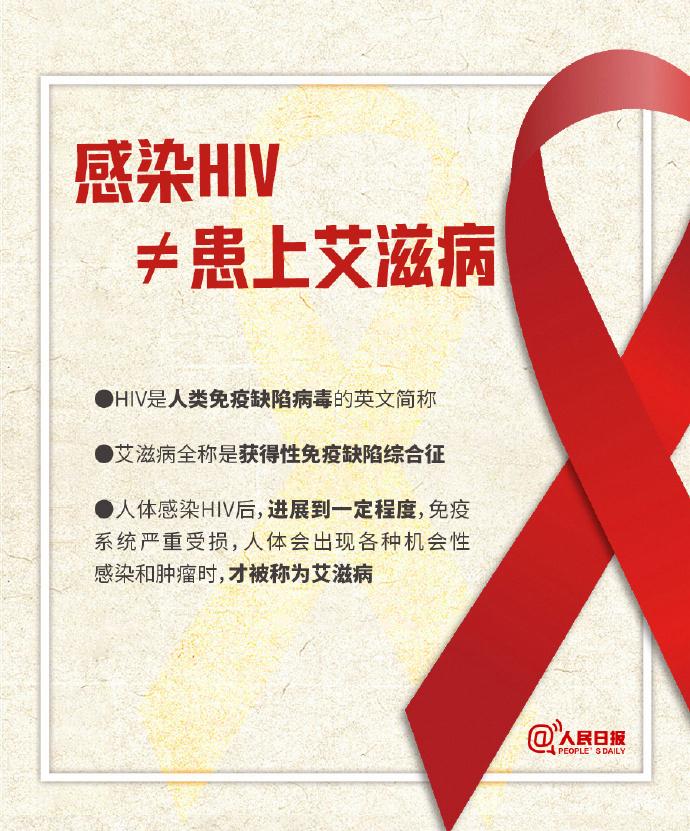谁不难?但日子还得过!
每天清晨七点,天津的老小区里还飘着早点摊的热气,阿勇会准时从药盒里倒出一粒抗艾滋病病毒药物,就着温水咽下。
药片划过喉咙的轻响,像一句持续了20年的开场白——既是他作为艾滋病感染者的日常,也是他作为“艾馨家园”创始人的序章。

第五个服药的感染者
“我是天津第五个服药的感染者。”说这话时,阿勇指尖摩挲着泛旧的药盒。
2005年的夏天,40岁的他还站在事业的高点:从国企行政到下海创业,直到一张HIV阳性报告递到面前,CD4(人体重要免疫细胞,正常成人CD4为500—1600/μL)计数只有20/μL,报告上的每个字都像一把剪刀,瞬间剪断了他设想的所有未来。
“那时候,宣传册上的病人都是骨瘦如柴、浑身溃烂的样子。” 阿勇记得,确诊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料理“后事”——哪笔钱给父母养老,哪批货要尽快交付。当时的他不怕死,怕的是走得不体面。
那时人们对艾滋病认知甚少,连医生都只敢宽慰 “再活五年八年没问题”,专业知识的匮乏像一层浓雾,把他和希望隔得远远的。
转机出现在2006年的一个周末。阿勇偶然听说有场艾滋病知识讲座,抱着 “反正没什么可失去”的念头去了。
教室里坐满了和他一样的人,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了解艾滋病,渐渐明白了艾滋病并非不治之症。那天回家的路上,阿勇第一次没走平时的捷径,而是沿着海河走了一大段。夕阳把河面染成金色,他忽然觉得“原来生命还能这样继续”。
2011年,阿勇与四名志同道合的感染者一起创办了一个艾滋病民间互助组织,最初的设想只是简单地相互帮助、相互依靠,为更多的感染者建立一个可以倾诉的空间。他们为此租下了一间小屋子,门口挂上牌匾:“艾馨家园”。

“那一刻,我更不能放弃这个孩子”
2012年冬天的医院走廊,阿勇第一次见到那个大二学生。男孩攥着确诊报告,手指关节发白。一段时间后又听说,男孩因为药物副作用,全身皮肤开始溃烂,脓水顺着下巴往下滴。
“他是外地人,这副样子不能回学校,在天津又举目无亲。”阿勇把男孩接回自己家,每天早上帮他涂药膏,晚上陪他在小区里散步——因为皮肤敏感,男孩出门必须戴面罩,两人常常在路灯下一圈又一圈地走,不怎么说话,却比任何安慰都管用。
男孩病情最严重时,男孩父亲只在病房待了片刻,留下钱便离开了。
“那一刻,我更不能放弃这个孩子。”目睹这一切的阿勇对自己说。
病情不断出现反复,最难熬的时候,男孩说他 “不想活了”,阿勇拉着他站在窗前,指着楼下的早点摊:“你看那卖豆浆的阿姨,每天四点就起来磨豆子,谁不难?但日子还得过!”
后来男孩通过不断地正规治疗,病情好转,重新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又顺利出国读研,他过去叫阿勇“大哥”,现在横跨网络,微信里会亲切称呼阿勇“干爹”。
阿勇的手机里,还存着很多这样的故事——最小患者是一个9岁的男孩,确诊时连“艾滋病”三个字都认不全,只知道自己病了,每三个月要来医院开药、抽血。
有一位志愿者与孩子结对,给予“一帮一”帮扶。令人欣慰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考上了重点中学,并顺利进入大学。

直面恐惧,才能跨过那道坎
“这些年,感染者的心态变太多了。” 阿勇说,早年的感染者大多带着恐惧,有人甚至会把药藏在床底下,不敢让家人看见;现在有些年轻感染者确诊时会继续无所谓地谈笑。
这种转变背后是复杂的现实:抗病毒药物的进步让疾病变得可控,而确诊也成了某些患者生活不检点与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的借口。
但这种转变也藏着隐忧——一些年轻人从医院取药后,转身就去酒吧,觉得“吃了药就没事”,反而不注意保护自己。
阿勇的劝导方式很直接。他会指着取药处一瘸一拐的人对年轻患者说:“那是打梅毒针的反应,每次都疼得直咧嘴,你想遭这罪?”
遇到情绪崩溃闹自杀的人,他有时会说:“要是真想跳楼,我陪你去20楼!没那勇气,就好好活着。”——不是狠心,是他知道,只有直面恐惧,才能跨过那道坎。
如今,阿勇计划退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旅游,享受久违的安静生活。
“生命这东西,脆弱得像根草,风一吹就弯;但只要扎了根,就能扛过不少事儿。”
每天晚上,阿勇还是会把第二天要吃的药放在床头,药粒在台灯下泛着微光。
20年的时光里,这粒药是他的铠甲,而“艾馨家园”里的那些故事,是他穿过铠甲,留给这个世界的温柔。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