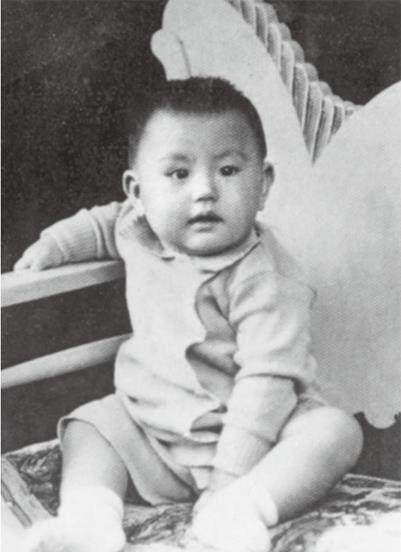前一天还在沈阳飞机厂的办公室里核对军工图纸,第二天就被塞进绿皮火车的闷罐车厢,没人告诉他要去哪儿,只知道“家里出事了”。 军大衣口袋里那枚刻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还留着昨晚锅炉房的余温,可他的身份,已经从“前途大好的军代表”变成了“需要审查的对象”。 在沈阳飞机厂那几年,吴新潮总觉得自己踩着时代的鼓点在走。 父亲是四野的老将领,他打小听着辽沈战役的故事长大,穿上军装时,胸牌上的“军代表”三个字能让车间老师傅们都敬三分。 那时他常泡在总装车间,看歼击机的零件像积木一样拼起来,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该像这些飞机,直上云霄。 闷罐车厢的铁皮被太阳晒得发烫,吴新潮抱着膝盖缩在角落。 “九一三事件”的消息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他家这叶“将门之舟”首当其冲。 隔离审查的日子里,他每天对着白墙写材料,钢笔水用得飞快,却写不清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后来有人来宣布处理决定,说“转业”到山区农场,他盯着对方军帽上的五角星,突然想起父亲以前说的“革命军人是块砖”,只是没想到自己会被砌进猪圈旁的土坯房。 农场的猪圈比他想象的更臭。 第一天喂猪时,猪食桶太重,他摔了个趔趄,粥状的饲料溅了满身。 同屋的老张拍着他的背笑:“吴代表,现在得叫你吴饲养员喽。” 他没笑,只是默默地把溅到搪瓷缸上的饲料擦干净,那缸子是刚参军时母亲给的,底儿已经磕出了豁口。 夜里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他盯着房梁想过一了百了,可摸到缸子上的刻字,又想起母亲送他上车时说的“活着就有盼头”,咬咬牙翻了个身,第二天照样凌晨四点起来铡草。 1980年冬天,吴新潮收到通知,说父亲可以保外就医到济南。 他收拾行李时,老张帮他捆扎铺盖卷,说:“不再申诉申诉?你本来……”他打断对方,把那枚搪瓷缸塞进帆布包:“不了,我得去给我爸做饭。” 在济南的高校行政楼里,他成了管档案的吴老师,每天和牛皮纸袋子打交道。 有同事聊起“将门之后”的往事,他总是笑着递烟:“都是过去的事了,我爸现在就爱摆弄阳台上的花。” 看着父亲佝偻着背在院子里拔草的样子,我觉得所谓的身份、前途,在那一刻都不如这声“吃饭了”来得实在。 父亲走后,他退休搬去了济南郊区的老房子。 这几年四野后代聚会,他总带着相机,给老兄弟们拍合影。 有人问他镜头里最喜欢拍什么,他举着相机对准窗外的玉兰花:“拍那些活得好好的东西。” 现在他总爱在傍晚摆弄相机,镜头里的夕阳落在济南高校的梧桐叶上,和当年农场猪圈旁那棵老槐树的光影,竟有几分相似。 搪瓷缸还摆在窗台上,里面插着晒干的野菊花。 他常说:“父辈们从老百姓变成将军,我们从将军后代变回老百姓,转了一圈,其实都是过日子。” 这日子里有闷罐车厢的颠簸,有猪圈旁的汗水,也有相机里定格的每一朵花开,原来平凡,才是最稳当的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