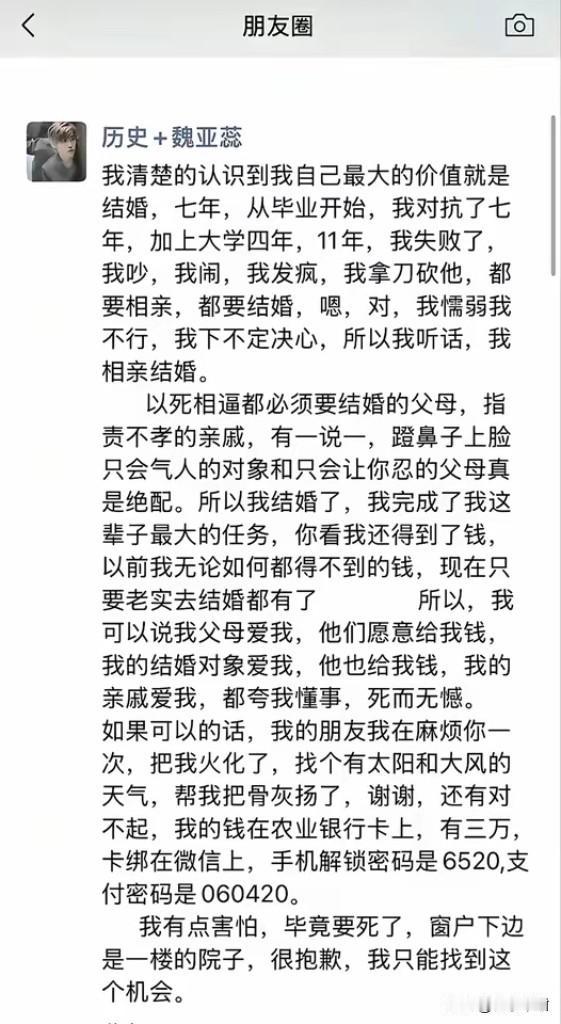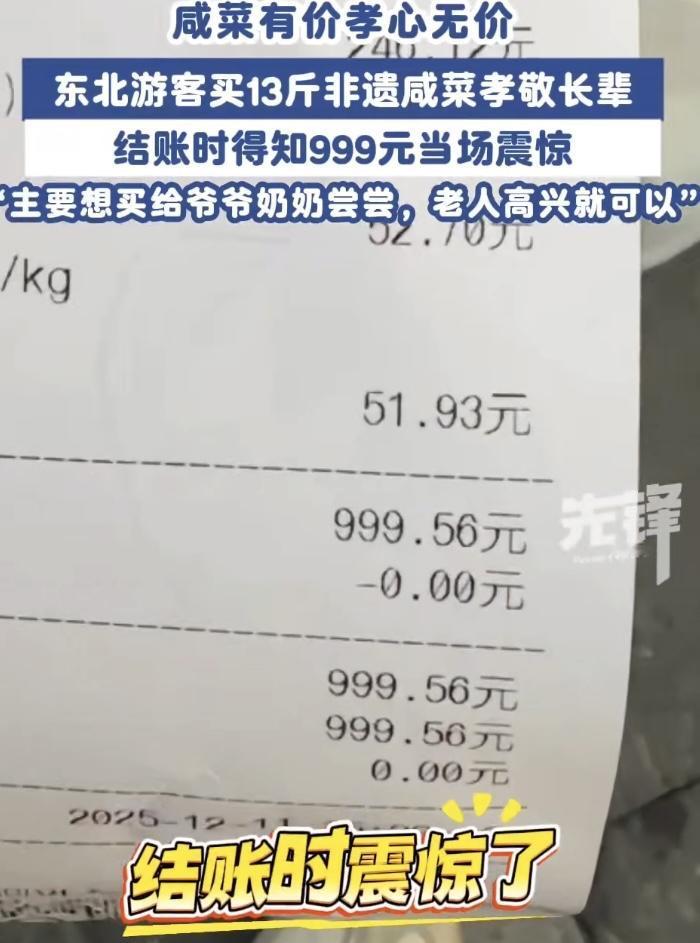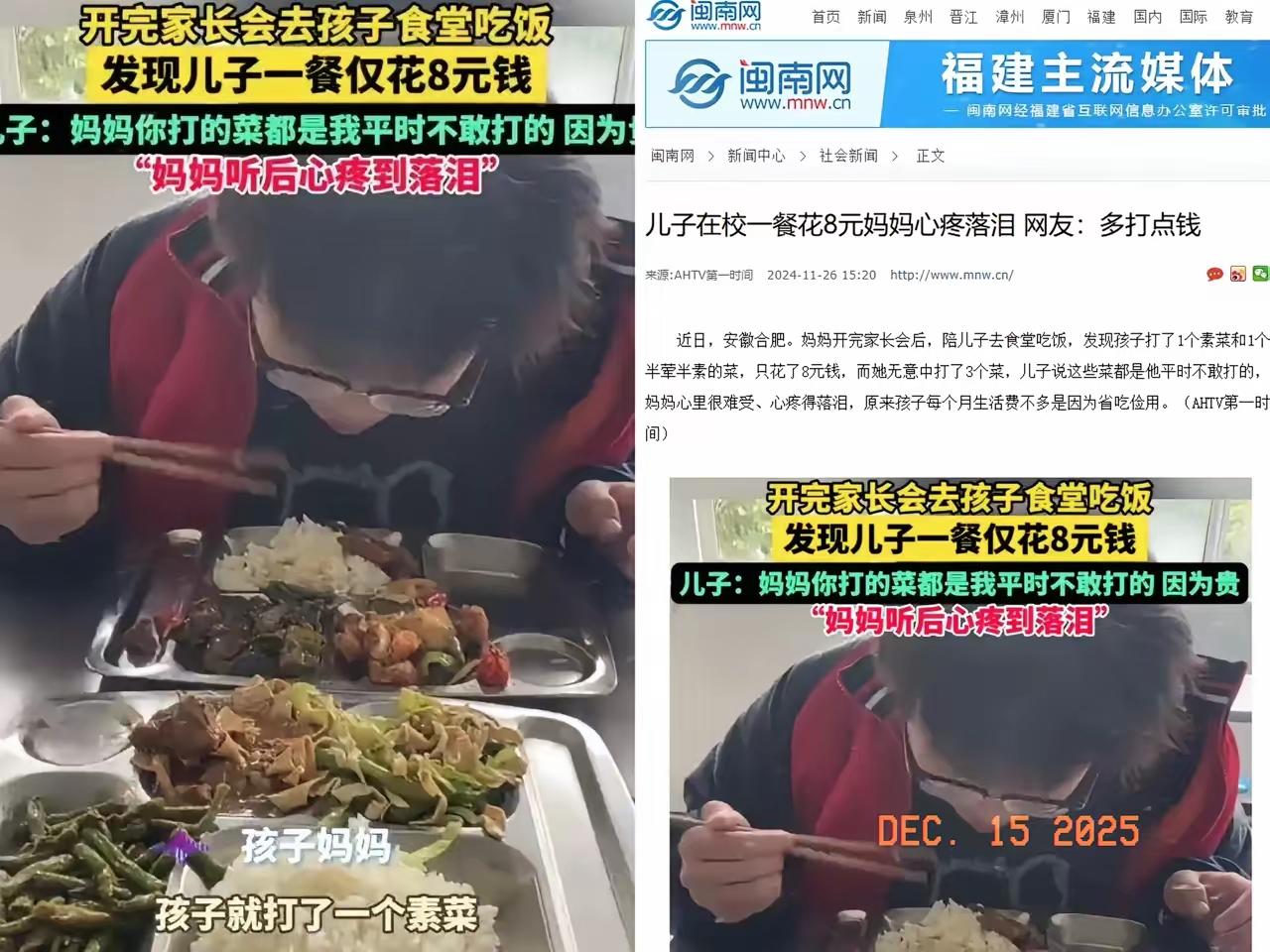我是辽宁的,却有一个安徽的小学同学,姓畗。 小畗刚转来我们班时,棉袄袖口还沾着没洗干净的泥点,一张嘴是带着水汽的安徽口音——“俺叫畗(fú)强”,把“福”字咬得又轻又软,后排男生噗嗤笑出了声。 他姥姥就住在村东头那间带柴火垛的土房,我们后来才知道,这孩子是跟着妈妈“逃”回辽宁的。 “逃”字是小畗姥姥蹲在门槛上择菜时说的,手里的豆角筋被她扯得老长。1960年代的冬天,小畗妈揣着户口本站在院子里,雪花落在她军绿色的旧棉袄上,像撒了把碎盐。“俺跟他走。”她对着屋里的父母说,声音比北风还硬。 那时小畗爸刚从部队复员,兜里揣着三十块复员费,老家在安徽乡下,土坯房三间,薄田两亩。姥姥拍着炕沿骂:“本地农民不比安徽的强?抬腿就能回娘家,非要往那山沟里钻——是嫌辽宁的雪不够冷?” 没人劝得住。复员兵的绿皮火车开走那天,小畗妈没敢回头,她知道站台上有母亲哭肿的眼,却不知道这一去,就是十一年。 十一年里,她没回过一次娘家。直到小畗哥俩长到能帮着挑水的年纪,她才把家里的棉被拆了重做,把哥俩的蓝布书包洗得发白,揣着攒了半年的粮票,带着孩子往东北赶——这次来,她连学籍证明都带来了。 小畗的安徽腔成了班级的“新玩意儿”。数学课上他回答问题,“二加二等于四(sì)”,尾音像被猫尾巴勾了一下,我们跟着学,他也不恼,只是把铅笔在指间转得飞快。后来我们发现,这“土气”的同学会用麦秸编蚂蚱,会把冻梨揣在怀里捂软了分给大家,开春时还带着我们在河套边挖荠菜。 那年秋天,小畗突然不来上学了。他的铅笔盒还放在桌肚里,里面有半块橡皮,和一张画着辽宁地图的草稿纸,安徽的位置被红铅笔圈了个小圈。 姥姥说,他妈妈夜里悄悄收拾了行李,还是那捆带着四季衣服的蓝布包,只是这次,里面多了我们送的野核桃和晒干的黄花菜。 三十年后同学聚会,有人说在安徽打工时见过一个叫畗强的包工头,说话带着点东北味儿。我对着酒杯愣了愣——当年那个在雪地里追着我们喊“等等俺”的安徽男孩,会不会也在某个瞬间,突然想起辽宁的土炕和带泥点的棉袄? 如今村东头的柴火垛早没了,可我总觉得,那间土房的门槛上,还蹲着个择豆角的老人,等着一个再也没回来的女儿,和她那个安徽口音的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