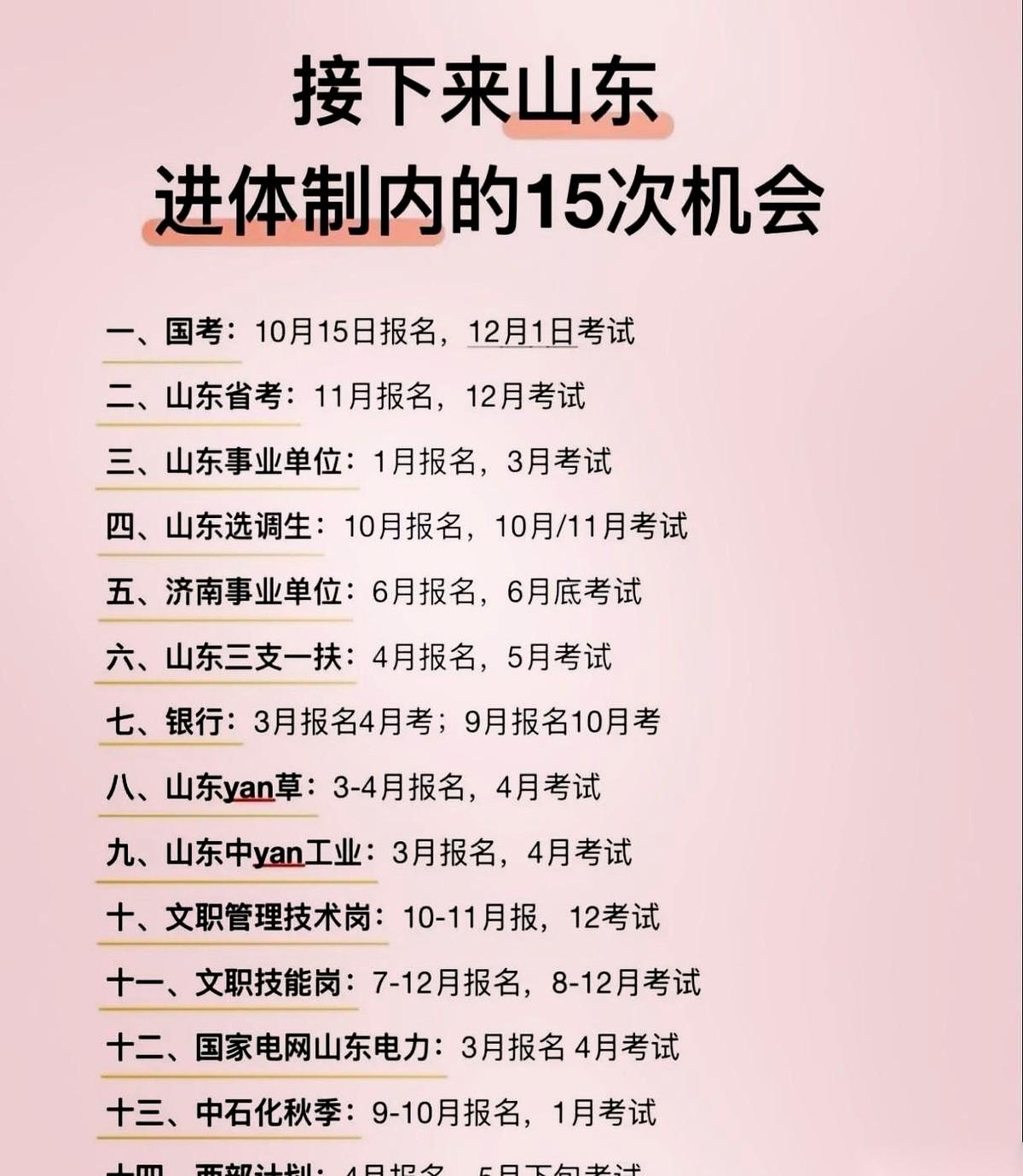1959年,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 这个“狠心”的父亲,名叫顾方舟,当时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谁能想到,这个让他含泪愧疚的举动,背后藏着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攻坚——彼时,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正在中国大地肆虐,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孩子被这种病毒夺走健康,有的终身瘫痪,有的甚至夭折。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大规模疫情,短短几个月就有1680人患病,其中大多是儿童,死亡率高达20%,街头随处可见拄着拐杖的残疾孩子,家长们谈“疫”色变,连让孩子出门都提心吊胆。 顾方舟留学英国时,亲眼见过脊髓灰质炎疫苗的研发过程,回国后便立志要攻克这个难题可疫苗研发到临床试验阶段,却卡在了最关键的一步——需要志愿者验证安全性。 这种病毒对儿童的致病性最强,疫苗试验风险极高,没有哪个家长愿意把孩子推到未知的危险里看着病房里孩子们痛苦的呻吟,听着家长们绝望的哭声,顾方舟彻夜难眠,他知道,每多等一天,就可能有更多孩子失去站立的机会。 “既然没人愿意,那就用我的孩子试!”这个念头在他脑海里盘旋了三天三夜,最终咬着牙做了决定——他的儿子顾烈东,刚满一岁,正是疫苗试验的关键年龄段。 妻子出差回来后,顾方舟如实坦白,妻子当场崩溃大哭,抱着儿子不肯松手:“那是我们的骨肉啊!你怎么忍心?”顾方舟红着眼眶紧紧抱住妻儿,声音沙哑却坚定:“我是父亲,也是科研工作者,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更多家庭破碎。 如果疫苗出了问题,我陪儿子一起扛!”那段时间,顾方舟每天守在儿子身边,观察他的体温、精神状态,哪怕孩子只是轻微咳嗽,他都吓得浑身冒冷汗夜里,他常常摸着儿子熟睡的小脸,泪水打湿了枕头,心里一遍遍默念:“儿子,再等等,爸爸一定让你平安,也让所有孩子平安。” 更让人动容的是,顾方舟的决定打动了团队里的同事,有三位研究员也主动提出,用自己的孩子参与试验四个不满两岁的孩子,成了中国首批脊髓灰质炎疫苗的“试药者”。 在封闭的观察室里,四位父亲轮流值守,记录着孩子们的每一个细微变化,他们既盼着疫苗有效,又怕孩子出现不良反应,那种煎熬,没经历过的人根本懂不了幸运的是,一个月后,四个孩子都安然无恙,疫苗安全性得到了初步验证。 可顾方舟并没有停下脚步,他知道,口服疫苗更适合在全国推广,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孩子。 为了研发口服减毒活疫苗,他带着团队扎根云南昆明的深山里,那里气候适宜培养病毒,却也条件艰苦,没有像样的实验室,他们就用木板搭建简易工作台;没有冷藏设备,他们就用冰块保存疫苗菌株。顾方舟和同事们吃着粗茶淡饭,住着简陋的平房,一干就是八年。 期间,他的儿子顾烈东也成了口服疫苗的“试验者”,每次儿子喝下疫苗糖丸,顾方舟都会仔细记录反应,这份特殊的“父女情”,成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 1965年,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在全国推广,一颗颗小小的糖丸,成了孩子们的“健康护身符”。 到1994年,中国最后一例本土脊髓灰质炎病例报告出现,再到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中国消除脊髓灰质炎,顾方舟用一生的坚守,让中国孩子彻底摆脱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如今,那些曾经吃过糖丸的孩子,大多已经为人父母,他们或许不知道顾方舟的名字,却享受着他用勇气和牺牲换来的健康。 顾方舟常说:“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一颗小小的糖丸”可这颗糖丸背后,是一位父亲的愧疚与担当,是一群科研工作者的执着与奉献。 在那个物资匮乏、技术落后的年代,正是因为有了顾方舟这样的人,愿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我们才能一步步战胜疾病,守护家园。他们的故事,不该被遗忘,他们的精神,值得永远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