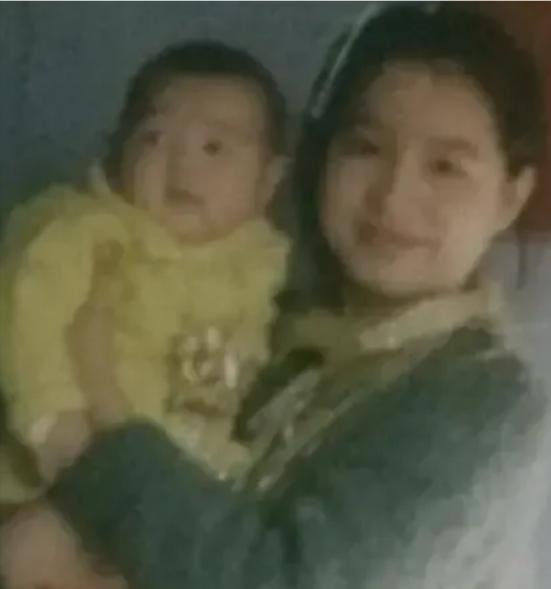1976年,25岁女知青抱着4岁儿子返城,母亲怒骂:未婚先孕,不知羞耻!可得知孩子身世后,竟然抱着孩子痛哭流涕,哥哥嫂子也抢着要抚养孩子...... 那年,她刚满十八岁,名字叫邵红梅,梳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里盛着对远方的憧憬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忐忑。 火车的汽笛声长鸣,载着他们这些热血青年,一路向西,奔向那片只在课本上读到过的黄土高原,最终,她落脚在陕西延川县一个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小村庄赵家沟。 出发前,她在心里无数次告诉自己,要“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做好了吃苦受累的全部准备,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沟壑,远比想象中更深。 陕北的干旱、贫瘠,日头底下的强体力劳动,还有那与江南水乡截然不同的粗粝生活,迅速消耗着她的体力与热情。 更雪上加霜的是,水土不服加上劳累,她很快病倒了,发起高烧,浑身无力地躺在那孔简陋的窑洞里,别说下地干活,就连从土炕上撑起身子喝口水,都眼前发黑,费尽全身力气。 不幸中的万幸,她遇到了赵家沟最善良厚道的人家,赵砚田和他的婆姨闫玉兰,这对中年夫妻闻讯赶来,看着炕上脸色蜡黄、气息微弱的城里姑娘,心疼得直叹气。“这娃遭罪了,” 赵砚田搓着粗糙的大手,语气沉重,闫玉兰则二话不说,直接坐在炕沿,用湿毛巾轻轻擦拭邵红梅滚烫的额头。 接下来的日子,赵家夫妇拿出了对待亲人的心肠。赵砚田跑了几十里山路,去公社卫生院抓来草药。 闫玉兰更是日夜守候,把家里仅有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一点白面擀成细软的面片,滴上几滴珍贵的香油,一口一口吹凉了喂给她。 为了给她补充营养,赵砚田甚至咬牙将家里正下蛋的老母鸡炖了汤,闫玉兰像照顾亲妹妹一样,为她擦洗身子,更换衣物,夜里就趴在炕边打个盹。 窑洞里那盏昏暗的油灯,映照着闫玉兰忙碌而温暖的身影,也一点点照亮了邵红梅冰凉的心。 在夫妻二人倾尽所有的精心照料下,邵红梅的身体一天天好转,这份恩情,重如山,她能下地那天,握着赵砚田和闫玉兰的手,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 那个窑洞的窗户上还糊着旧报纸,墙上的喜字也掉了色,但这份纯粹的善意,让邵红梅感觉像家,她也把家里寄来的好东西,饼干罐头什么的,都分成三份,三个人就像真正的一家人。 可老天爷似乎总爱开玩笑。1971年,闫玉兰拼尽力气生下一个儿子后,因大出血撒手人寰。 邵红梅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婴儿,和几近崩溃的赵砚田,想都没想就把孩子接了过来,用米汤一口一口地喂养他,她给孩子取名“玉刚”,就是为了纪念他的妈妈闫玉兰。 为了不让村里人嚼舌根,说她想“给死婆姨的汉子当填房”,她认下玉刚做干儿子,从此像个真正的母亲一样,教他说话,陪他长大。 1976年,一场特大暴雨来袭,公社的粮仓眼看就要塌了。在大家拼命抢救粮食时,一根烂透了的房梁突然断裂。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赵砚田用尽全身力气,一把将邵红梅推出了门外,而他自己,却永远留在了那片废墟之下。 这一推,推出了一条生路,也彻底锁死了邵红梅的后半生,面对成了孤儿、哭得撕心裂肺的四岁玉刚,她在赵砚田夫妇的坟前发下重誓:从今往后,我就是玉刚唯一的妈。 1976年夏,二十五岁的邵红梅抱着四岁的玉刚,风尘仆仆地站在北京的家门口,七年的黄土高原生活在她身上刻下了痕迹,却也在她眼里沉淀下别样的坚毅。 门开的瞬间,她还没来得及喊一声“妈”,母亲的脸色已骤然阴沉。 目光扫过她怀中那个怯生生的孩子,母亲的声音尖利地划破了重逢的寂静:“没结婚就带个野孩子回来,我们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 一个搪瓷茶缸被狠狠摔在地上,刺耳的碎裂声惊得玉刚猛地一颤。“滚!”伴随着这句冰冷的驱逐,大门在她面前重重关上,震落了邵红梅肩头还未拍净的黄土。 四周邻居的窗户后,隐约传来窃窃私语。邵红梅却异常平静,她先是缓缓蹲下,用那双在赵家沟磨出薄茧的手,轻轻拍掉玉刚裤腿上沾着的黄土,又用指腹擦去孩子眼角将落未落的泪珠,柔声道:“玉刚不怕。” 待安抚好受惊的孩子,她才直起身,目光平静地望着那扇紧闭的门,没有解释,没有哭泣,她只是用一种带着陕北口音的语调,清晰而缓慢地,将她在赵家沟那七年的岁月,从头讲起。 最后,她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了两样东西。一张是赵砚田的烈士证明,另一件,是一只用蓝布包着、还没做完的小虎头鞋,那是闫玉兰留给儿子唯一的念想。 真相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所有人。母亲颤抖着手接过这个“外孙”,当场号啕大哭,为了女儿的将来,家里人商量着把玉刚挂在哥嫂名下,由他们抚养,但邵红梅都拒绝了。 后来,她遇到了一个好人,一个善良的铁路工人,他不仅接受了她的全部过去,还把玉刚当成自己的亲儿子。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的小不点已经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