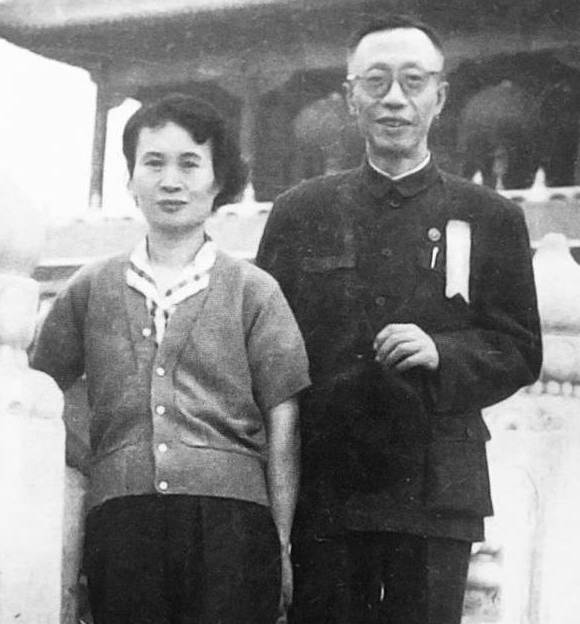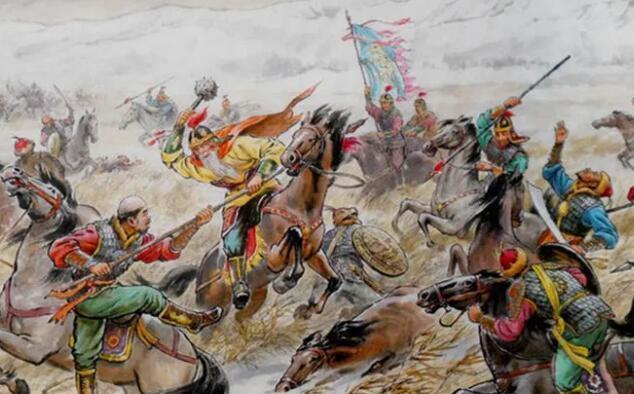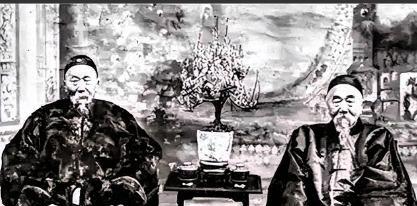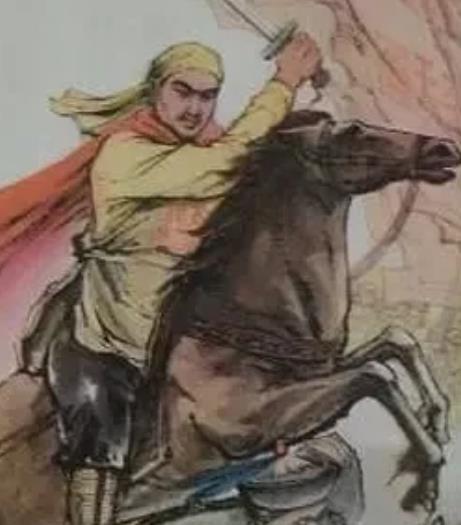1858年1月5日,广州城寒风刺骨,总督衙门内却灯火通明。叶名琛端坐在书案前,手握朱笔,正在批注一本《靖海氛记》。案头还摆着一卷《春秋繁露》,空气中弥漫着墨香和淡淡的檀香。 他抬头望向窗外,远处隐约传来炮火声,那是英法联军攻城的信号。作为两广总督,他曾是清廷重臣,掌控东南门户,可这一刻,他却无力回天。 幕僚汪瑔在《随山馆日记》中记载,叶名琛曾每日在“长春仙馆”内卜卦,误信“虎陷泥沼”的卦象,以为英军后勤不继,迟迟未动用藏在越秀山的200门铁炮。 直到英军破门而入,他才从容整冠,对仆从轻声道:“吾此行必不生还,尔等归报朝廷可也。” 那一夜,英军士兵冲进衙门,叶名琛没有反抗。他被押解出城,身后是燃烧的广州城,眼前是冰冷的铁链。 曾经的权贵,如今成了阶下囚,命运的转折来得如此猝不及防。被押上“无畏号”囚船时,他抬头看了一眼广州的天空,心中是否在想:这一去,便是永别? 1858年1月,叶名琛被押往印度加尔各答,囚禁在威廉堡一艘名为“无畏号”的囚船底舱。据《伦敦新闻画报》1859年报道,船舱狭小潮湿,仅有一扇小窗透光,地铺草席,空气中满是海水的咸腥和木材腐朽的气味。 叶名琛每日面壁盘坐,拒绝使用英方提供的餐具,只用自带的青花瓷碗吃从广州带来的丝苗米。他身着灰褐色棉布便袍,腰系素色麻绳,布鞋边缘早已磨损,昔日的官服玉带早已无踪。 在囚船上,他刻下了一首诗:“零丁洋泊叹无家,雁札犹传节度衙。海外难寻高士粟,斗牛远虑使臣槎。”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海上苏武”的见证,字里行间透着不屈与孤寂。 美国汉学家斯蒂芬·普拉特在《帝国暮色》中描述,叶名琛常手握一卷《吕祖经》,眼神空洞地望向舷窗外,背景是交错的帆缆绳索,宛如囚笼将他困住。 1859年3月,最后半袋广州丝苗米耗尽,他开始绝食,每日仅饮恒河水。临终前,他剪下自己的辫子,装入锦匣,托英兵转交家人。 据《泰晤士报》1859年4月12日讣告记载,叶名琛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依然保持着清廷官员的尊严,拒绝向英方低头。 4月9日,这位曾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总督,在异乡囚船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德国诗人冯塔纳在《十字报》中感慨:“这位东方总督的死亡使加尔各答的胜利蒙上阴影……他证明精神比炮舰更高贵。” 回溯这一切的起点,还要提到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这艘船看似不起眼,却成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 香港注册文件显示,亚罗号的执照在1856年9月27日到期,而清兵登船检查时已是10月8日,执照已失效12天。 船上14名船员中,12人为中国籍,船主方亚明也是华人,仅船长肯尼迪为英籍。 英方声称清兵撕毁英国旗,但船员李喜进供词却说:“当日因暴雨未升旗,水师仅降下船桅信号旗检查。” 叶名琛作为两广总督,面对此事态度强硬,拒绝英方无理要求。或许他未曾料到,这一决定将广州推向战火,也将自己推向生命的终点。历史总是充满讽刺,一艘小船,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叶名琛死后,清廷将责任尽数推卸,咸丰帝谕令称其“刚愎自用,办理乖谬”,却隐瞒了曾密谕“勿轻启战端”的真相。 而广东民间对他的评价则更为复杂,番禺县志中一句乡谚道出了百姓的矛盾心情:“船坚炮利终不惧,最叹仙馆迷心窍。”他们敬佩他的气节,却也叹息他的迷信误事。 站在今天回望,叶名琛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身处清廷与列强夹缝之间,既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自身局限的受害者。 那张囚船上的最后照片,定格了他的空洞眼神,也定格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的绝食,他的诗句,他的辫子锦匣,无不让人感慨:一个人如何在绝境中坚守尊严?一个国家又如何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那张拍摄于1859年的黑白照片,如今静静地躺在历史档案中。照片中的叶名琛,眼神空洞,手握经卷,身后是囚笼般的绳索。 他没有等到回国的机会,也没有等到清廷的救援,但他用生命书写了“海上苏武”的传奇。 从广州总督衙门的灯火通明,到加尔各答囚船的昏暗潮湿,他的故事跨越了时间与空间,刺痛着每一个读到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