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回到1969年,河北保定一个偏僻的村庄,土路上尘土飞扬,夕阳把茅草屋顶染成金黄。18岁的马爱茹刚从天津下放到这儿,背着破旧的行李箱,脸被风吹得发红。 她站在村口,望着满眼的菜园和泥墙,内心既好奇又孤单。城里来的知青,穿着蓝色粗布衣,扎着麻花辫,像个格格不入的外来者。 村里的小学老师范志刚,是她遇到的第一个暖心人。他中等身材,穿深色中山装,笑起来眼睛弯弯的,像夏天的月牙。 范志刚递给她一碗热水,嗓子低沉:“城里娃,喝口水暖暖身子。”马爱茹接过碗,手指触到粗糙的陶碗,暖意从指尖传到心底。那一刻,她觉得自己在这陌生的土地上有了依靠。 两人渐渐熟络。范志刚教她劈柴、挑水,教她怎么跟村民打交道。夜晚,油灯下,他念着《红岩》的片段,她听得入迷,忘了屋外呼啸的寒风。爱情像春天的野草,悄悄发芽。 1972年,他们结了婚,第二年生下女儿香香。小女孩圆脸大眼,穿着花布衣,笑声像银铃,村里的狗听见都摇尾巴。马爱茹抱着香香,觉得日子苦是苦,但有丈夫和女儿,日子也有甜。 1979年春末,村里来了封信,纸张泛黄,字迹工整:知青返城通知。马爱茹捏着信,手抖得像筛糠。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天津城里工厂招工,户口能迁回,知青们像候鸟般躁动。马爱茹站在破旧的木窗前,阳光从缝隙洒进来,尘土在光束里飞舞。 她盯着院子里玩耍的香香,六岁的小女孩追着一只蝴蝶,笑得无忧无虑。范志刚在旁劈柴,汗水浸湿了衣背。 “回去吧,城里才是你的家。”范志刚放下斧头,语气平静却沉重。马爱茹咬紧嘴唇,泪水在眼眶打转。 她想起了天津的家,父母的期盼,还有那份工厂文员的工作——对她来说,那是逃离泥泞、重新做城里人的机会。 可香香呢?范志刚呢?她看着丈夫粗糙的手,想到这些年他默默撑起这个家,心像被刀剜。 那天晚上,油灯昏黄,马爱茹收拾行李,动作生硬,像个木偶。香香睡在土炕上,小手攥着她的衣角,嘴里嘟囔着“妈妈”。范志刚坐在木椅上,椅子吱吱作响,他低头不语,只说了一句:“你走吧,孩子我养。” 马爱茹想抱抱女儿,却怕自己会舍不得。她咬牙推开门,拖着行李箱,头也没回。身后,风吹过窗帘,窸窣作响,像在低语她的背叛。 回到天津,马爱茹成了工厂文员,住进筒子楼,生活像上了发条。她努力工作,攒钱寄回村里,却不敢问香香的近况。 每晚,她盯着天花板,想起河北的茅草屋、香香的笑声,愧疚像潮水淹没她。她再婚,生了个儿子,但婚姻平淡如水。城市的高楼、喧嚣的街道,填不满她心里的空洞。 而远在河北的范志刚,一个人拉扯香香长大。他继续教书,省吃俭用,把香香送进县城的中学。香香成绩好,却从不提母亲。村里人偶尔议论:“那城里女人,扔了孩子跑了。” 香香低头走过,拳头攥紧。18岁那年,她考上天津的大学,范志刚送她到车站,递给她一个旧布包,里面是她小时候的花布衣。香香红着眼说:“爸,我不会去找她。” 2014年,天津第三医院的候诊大厅。马爱茹拄着拐杖,肺病让她喘气都费劲。她无意间瞥见范志刚,岁月在他脸上刻下沟壑,可那双深邃的眼睛没变。她心跳得像擂鼓,想喊他,却被一声怒吼打断:“离我爸远点!” 香香,40岁,穿着朴素的毛衣,眼神像刀,冲到她面前,推了她一把。马爱茹踉跄后退,拐杖差点掉地。 “你还敢来!”香香声音颤抖,周围的人投来好奇的目光。马爱茹嘴唇哆嗦,想解释,却一个字也吐不出。 她盯着香香的脸,依稀看到那个追蝴蝶的小女孩,可那双眼里现在只有愤怒和陌生。范志刚走过来,拉住香香,低声说:“别这样,她……是你妈。” 香香愣住,眼泪夺眶而出。她转身跑出大厅,留下马爱茹呆立原地。护士喊她名字,她却像没听见,泪水滑过满是皱纹的脸。 几天后,马爱茹病情恶化,住进重症病房。香香来看她,站在床边,握着那件旧花布衣,低声说:“我恨你,但爸说,你也苦。”马爱茹想伸手摸摸女儿的脸,却没力气。几天后,她闭上眼,带着无尽遗憾离开。 马爱茹的故事,是1979年知青返城潮里无数家庭的缩影。1970年代的上山下乡,造就了爱情,也埋下了分离的种子。 35年后,医院的重逢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性的挣扎与救赎。香香最终原谅了母亲,可那只蝴蝶,早已飞不过岁月的风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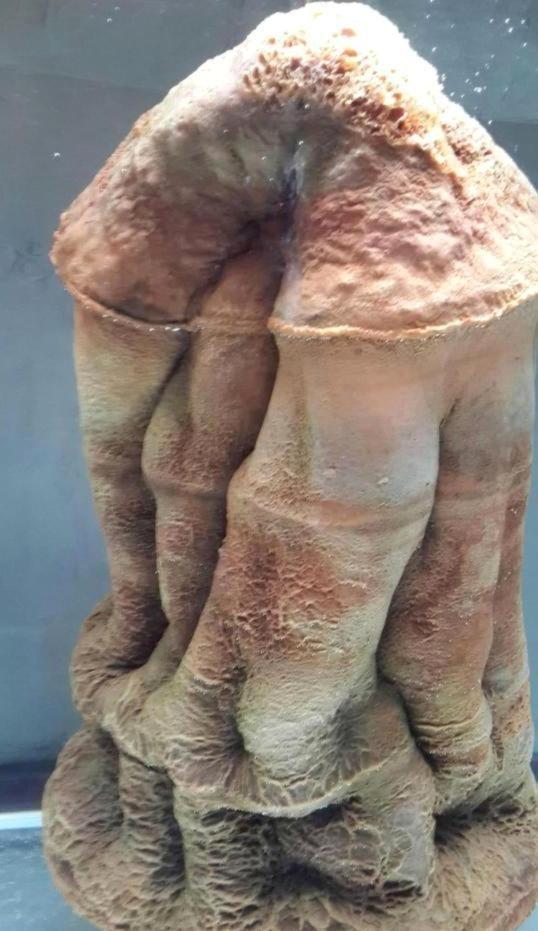




![接楼上的帖子,原来她两是这样闹掰的[吃瓜]](http://image.uczzd.cn/755899212032516226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