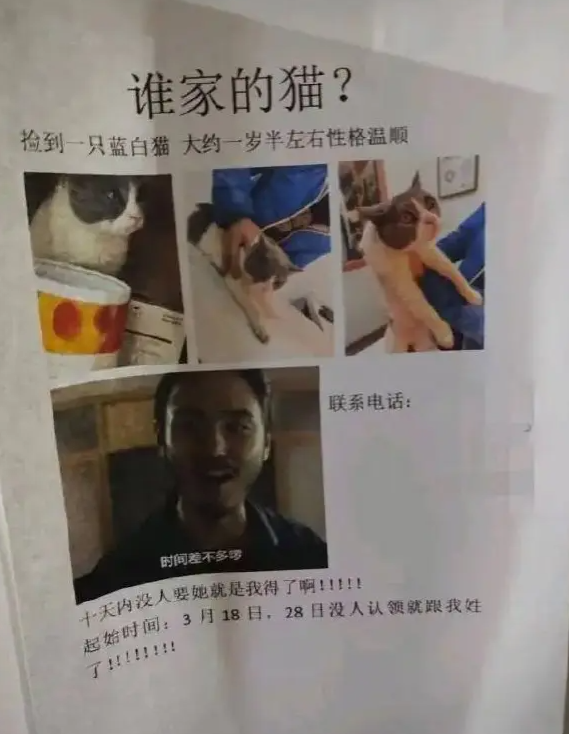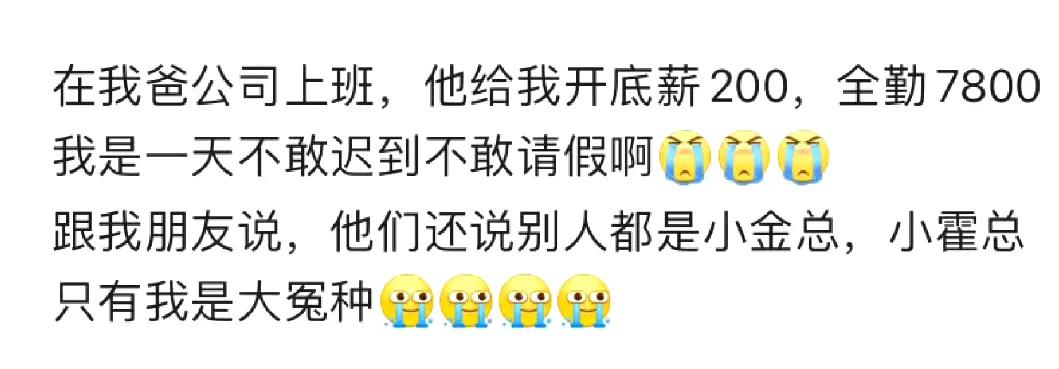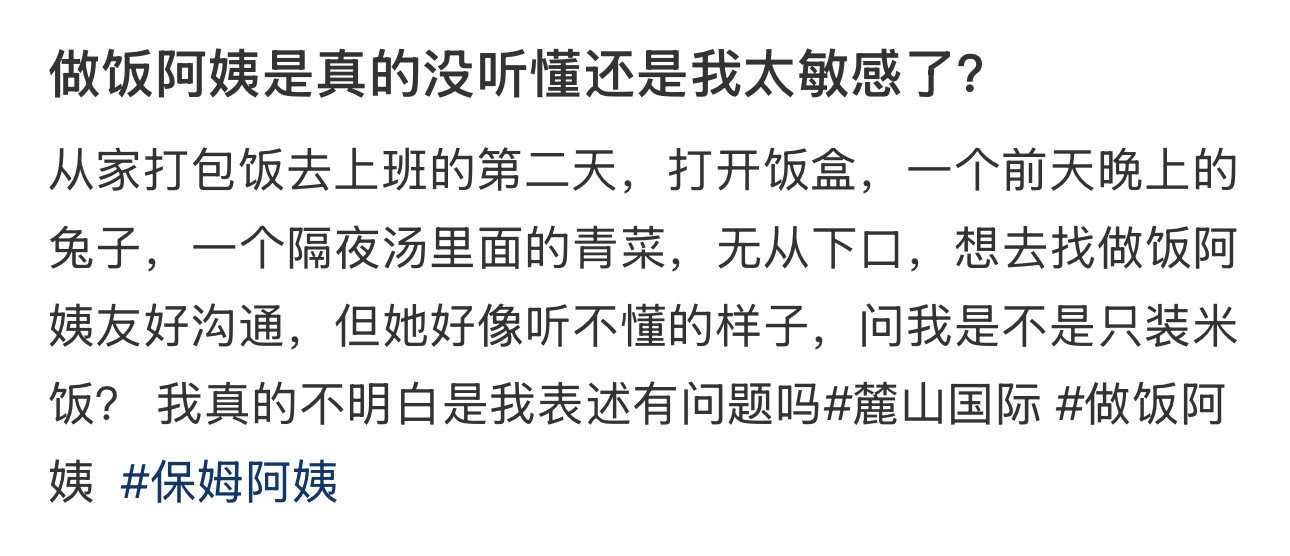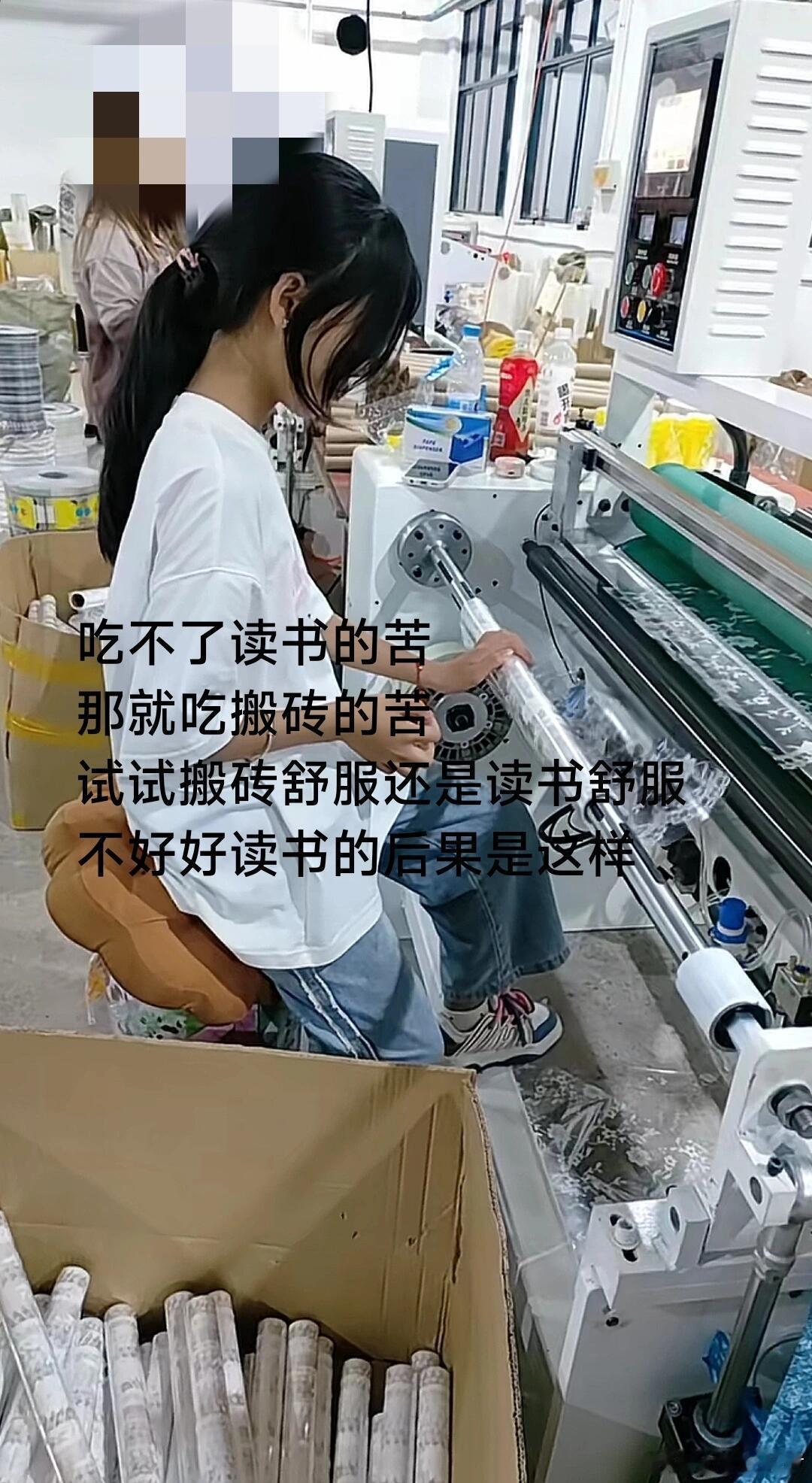1617年,徐霞客意外宠幸了发妻的侍女周氏,并让她怀了身孕,谁料,待徐霞客云游回家时,周氏已经被妻子卖了,她生下的孩子没有被认回。谁知,就是这个孩子让徐霞客的名字名垂千古。 1617年那会儿,徐霞客因为家里老人走了,正处在守丧期,心里头那个闷啊,正好侍女周氏天天围着他转,一来二去的,俩人就擦出了点小火花,结果周氏肚子就鼓了起来。徐霞客呢,跟个没事人一样,背起包袱就出去溜达了。 徐霞客这一走,家里可炸了锅。 发妻王氏可不是省油的灯。她出身书香门第,嫁给徐霞客这些年,早就习惯了丈夫“不着家”,可这回不一样——周氏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藏不住了。 王氏看着周氏那隆起的小腹,心里像塞了团火。在她眼里,这不仅是丈夫对自己的怠慢,更是徐家的脸面被踩在地上摩擦。一个侍女,竟敢怀上主子的种?传出去,徐家门楣都得被唾沫星子淹了。 她没等徐霞客回来,找了个牙婆,塞了点银子,趁着月黑风高,把周氏拖上了一辆驴车。“去江南,越远越好,别让她再出现在江阴。”王氏说这话时,声音冷得像寒冬的冰。 周氏哭着抓车门,喊着“夫人饶命”,喊着“等徐公子回来”,可驴车轱辘轱辘转,很快就没了影。那会儿她肚子里的孩子,刚满六个月。 徐霞客在外头转了大半年,踏遍了浙东的山山水水,直到鞋底磨穿了才想起回家。一进门没见着周氏,随口问了句,王氏眼皮都没抬:“手脚不干净,打发走了。” 徐霞客愣了愣,张了张嘴,没再追问。 他这人就是这样,对山水的执念比啥都深,家里的事,向来是“过得去就行”。或许他心里有愧,或许他觉得王氏做得“有理”,总之,这事就这么翻篇了。他转身就去整理自己的游记手稿,那些歪歪扭扭的字迹里,记着山的海拔、水的流向,唯独没提周氏半个字。 可他不知道,周氏被卖到苏州一户姓许的人家后,没多久就生了个男孩。 许家是做笔墨生意的,心肠还算不坏,给孩子取名“许默”。周氏没敢说孩子爹是谁,只说自己是个苦命人。许默长到七八岁,就跟着养父学做墨锭,闲暇时总爱蹲在书铺门口,看那些南来北往的文人翻书。 有回,一个游学的秀才捧着本手稿念叨:“这徐霞客写的山水,真是绝了……可惜啊,东一篇西一篇,没个章法。” 许默耳朵尖,追着问:“先生,徐霞客是谁?” 秀才笑了:“江阴人,爱爬山,走到哪儿记到哪儿,是个奇人。” 就这一句话,像颗种子落进了许默心里。他总觉得“徐霞客”这三个字耳熟,夜里问娘,周氏抱着他掉眼泪,这才断断续续说了当年的事。许默攥着小拳头,没哭,只说了句:“娘,我知道了。” 从那以后,许默变了。 他白天做墨锭,晚上就往书铺跑,把能找到的、跟徐霞客有关的零散手稿都借来抄。那些纸页泛黄,字迹潦草,有的还沾着泥点、带着水迹,一看就知道是在野外急急忙忙写的。 他发现,这些手稿里藏着太多宝贝——雁荡山的奇峰、黄山的云海、漓江的暗礁……可就是太乱了,东一段西一段,没头没尾。 “得把它们理顺了。”许默暗下决心。 他凭着娘模糊的描述,跑到江阴徐家村,远远地看了眼徐家的老宅,没敢进去。他怕被赶出来,更怕打扰了那个素未谋面的爹。他只是悄悄打听徐霞客的行踪,听说他还在外面游历,就托人带话,说“有个姓许的年轻人,想帮他整理文稿”。 徐霞客收到消息时,正在云南的澜沧江边。他摸着胡子,愣了半晌,心里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下。他想起那个被王氏打发走的周氏,想起那个没见过面的孩子。他没回信,只是从那天起,游记写得更规整了,还特意在末尾标注了日期和地点。 再后来,徐霞客老了,走不动了,才回了家。 许默听说后,揣着一箱子抄好的文稿,鼓起勇气去了徐家。徐霞客躺在床上,看见这个眉眼间有点像自己的年轻人,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只是把床头那堆新写的手稿,轻轻推了过去。 许默接过手稿,指尖碰着爹的手,都是粗糙的茧子——一个是爬山磨的,一个是做墨锭磨的。 徐霞客去世后,许默花了整整十年,把那些零散的手稿一篇篇核对、排序、誊抄。他给这本书取名《徐霞客游记》,送到了江南的书坊。 谁也没想到,这本书一出版就火了。 文人墨客争着看,地理学家拿着它勘舆,连后来的朝廷编方志,都得翻一翻这本游记。徐霞客的名字,就这么跟着这本书,传遍了大江南北,直到今天,还被人念叨着。 有人说,徐霞客这辈子值了,游遍名山大川,还留下这么本奇书。 可少有人知道,若不是当年那个被卖掉的侍女,若不是那个没被认回的孩子,那些沾满风霜的手稿,或许早就散落在哪个角落,被虫蛀了,被水泡了,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 徐霞客对山水的痴迷,成就了他的眼睛;许默对父亲的执念,成全了他的文字。 信息来源:《徐霞客游记·序》《江阴徐氏宗谱》《明史·徐霞客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