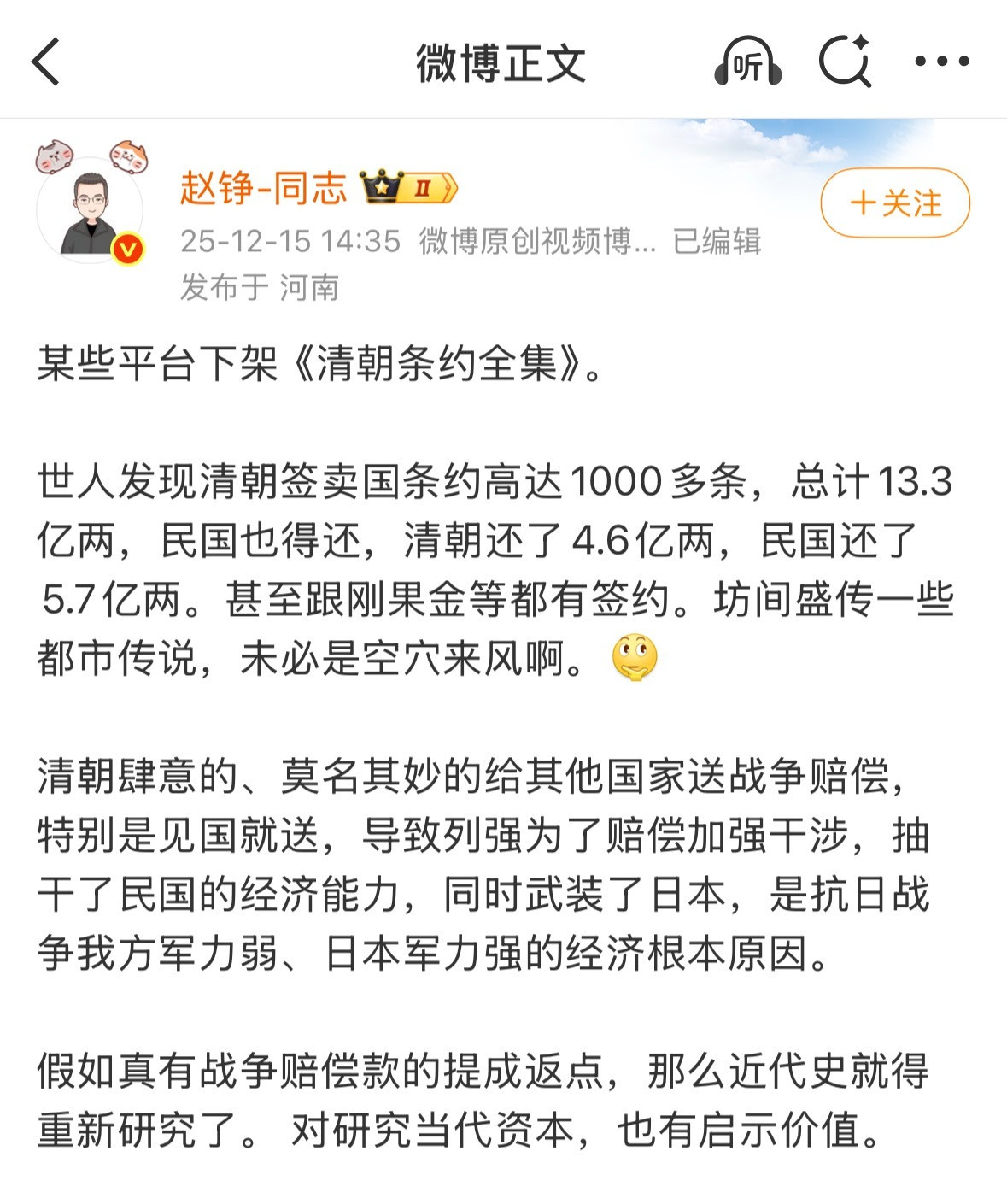>十七岁那年,我率三百铁骑夜袭吐蕃大营,斩敌数千。
>陛下抚我背笑曰:“此子将来必是朕之霍去病。”
>二十年间,我身兼四镇节度使,大唐万里边疆尽托我手。
>直到那天,陛下要我攻打一个不该打的石堡城。
>我跪在殿前:“此城险固,纵得之亦不足制敌,徒耗数万性命耳。”
>贵妃在旁轻笑:“王将军莫非是怕了?”
>后来我被打入天牢,才明白——
>这世上最锋利的刀,从不在战场。

朔风卷着砾石,抽打在脸上,细微的刺疼。王忠嗣勒马立于赤岭之上,身后是沉默如铁的唐军大营,身前,是沉入墨色的吐蕃疆域。星斗硕大,寒芒逼人,缀在丝绒般的夜幕上,也映着他身上冰冷的甲叶。
他闭上眼,鼻尖仿佛还能嗅到十七岁那场雪夜突袭的血腥气。三百铁骑,衔枚疾走,马蹄裹着厚布,像一群扑向猎物的幽影。火起,嚎叫,刀锋砍进骨肉的闷响……那一夜,他斩首数千,浑身浴血地踏营而归,用吐蕃贵族的头颅,垫起了自己通往将星之路的第一级台阶。
记忆里,是陛下——那时尚是英姿勃发的当今圣人大步走来,带着爽朗的笑意,重重拍打他稚嫩未脱的肩背,甲胄铿锵:“此子英果类吾!将来必是朕之霍去病!”
声音犹在耳,滚烫。
二十年了。他从一个锐不可当的先锋小将,成了这大唐北疆、河西、陇右、朔方四镇的节度使,万里边陲,帝国的安危系于一身。旌旗所指,诸胡屏息。他不再是那个只需冲锋陷阵的少年,他懂得了山川的脉动,敌我的虚实,更懂得了每一道军令背后,那千万条士卒性命的重量。
身后的亲兵递上来一份刚刚送到的敕令。帛书精致,带着长安宫廷特有的淡香。他展开,就着亲兵举起的火把光亮,目光扫过那一行行朱笔御批,最终,凝固在“石堡城”三个字上。
心,猛地一沉。
那不是开战,那是驱民入水火。
他猛地攥紧了帛书,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风更冷了,刮过荒原,发出呜咽般的声音。
……
长安。大明宫,紫宸殿。
金兽吐着袅娜的香烟,暖得让人发腻。舞姬的彩袖翻飞,乐工的丝竹靡靡,都隔着一层无形的屏障,传不到王忠嗣的耳中。他跪在冰凉的金砖地上,脊梁挺得笔直,像边塞风雪里不肯弯腰的胡杨。
御座上的圣人,面容已见富态,眼神不似当年锐利,却更添了几分深沉的威压。
“爱卿,石堡城,乃吐蕃东进之要冲,势在必得。”圣人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朕意已决,着你即日整军,克期攻取。”
王忠嗣深吸一口气,压下胸腔里翻涌的情绪,声音沉厚而清晰:“陛下,石堡城地势险绝,三面孤悬,吐蕃以重兵据守,粮秣充足。我军若强攻,仰面而上,贼据高临下,檑木滚石,箭矢如雨……”他抬起头,目光灼灼,直视天颜,“臣估算,非填进去数万将士性命,不可得!然得之又如何?其地偏狭,不足以制吐蕃之命,反成我巨大负担,徒耗国力,空流碧血!陛下,此实乃得不偿失之举,望陛下三思!”
殿内一时静极。只有香炉里烟丝断裂的微响。

忽然,一声轻笑响起,带着女子特有的娇慵,打破了死寂。坐在圣人下首的杨贵妃,玉手轻掩朱唇,眼波流转,落在王忠嗣身上,那目光里有好奇,有玩味,更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讥诮。
“王将军,”她的声音甜糯,却像冰针扎入耳膜,“说得这般骇人,莫不是……怕了?”
“怕”字出口,轻飘飘的,却比万千指责更重,狠狠砸在王忠嗣的心上。他看到圣人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眼神瞬间冷了下去。
一股寒意,从尾椎骨沿着脊梁瞬间窜到了天灵盖。那不是面对吐蕃万千铁骑时的寒意,那是一种更深沉,更绝望的冷。他知道,有些东西,比石堡城的悬崖峭壁,更难攀越,也更易摔得粉身碎骨。
他没有再辩驳,只是将头深深低下,额头触着冰冷的地面。
……
天牢。黑暗,潮湿,腐臭的气息无孔不入。
沉重的铁链锁住了手脚,冰冷的触感早已麻木。曾经能开三石强弓、挥舞马槊荡平敌阵的手臂,如今连抬起都觉费力。身上华丽的明光铠早已被剥去,只剩下破烂的囚衣,遮掩不住底下纵横交错的鞭痕与烙铁留下的印记。
王忠嗣靠坐在冰冷的石壁上,望着从那扇极高、极小的窗户里透进来的一缕微光。光柱中,尘埃飞舞。
他想起赤岭的朔风,想起河西的烈酒,想起麾下儿郎们粗豪的战歌,想起他们信任的目光,最终,都化作了紫宸殿里,君王那冰冷的眼神,和贵妃那一声轻笑的“怕了”。
呵。
他扯了扯嘴角,干裂的嘴唇渗出血丝。

石堡城……后来他还是被迫下令进攻了,在李林甫等人的构陷之下,在圣意已决的压迫之下。果然,尸山血海,数万忠魂埋骨荒山,才换来那座空无一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价值的孤城。
捷报传回长安时,不知陛下可曾在庆功的宴乐中,听到边卒妻母的恸哭?
铁链哗啦作响,他艰难地挪动了一下身子,牵动伤口,一阵剧烈的咳嗽。
这阴湿的牢狱,这蚀骨的冤屈,这来自背后、来自曾经最信任之处的刀……远比吐蕃最勇猛的武士,更懂得如何摧毁一个人。
他缓缓抬起被枷锁磨得血肉模糊的手腕,看着那无法挣脱的禁锢。
半生戎马,纵横万里,自以为掌中横刀,胯下战马,便可护国安民。到头来才明白。
这世上最锋利的刀,从不在战场。
![有没有可能当年朱允炆就是这么干的,但朱允炆不体面自然有人帮他体面[吃瓜]](http://image.uczzd.cn/114214455203619464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