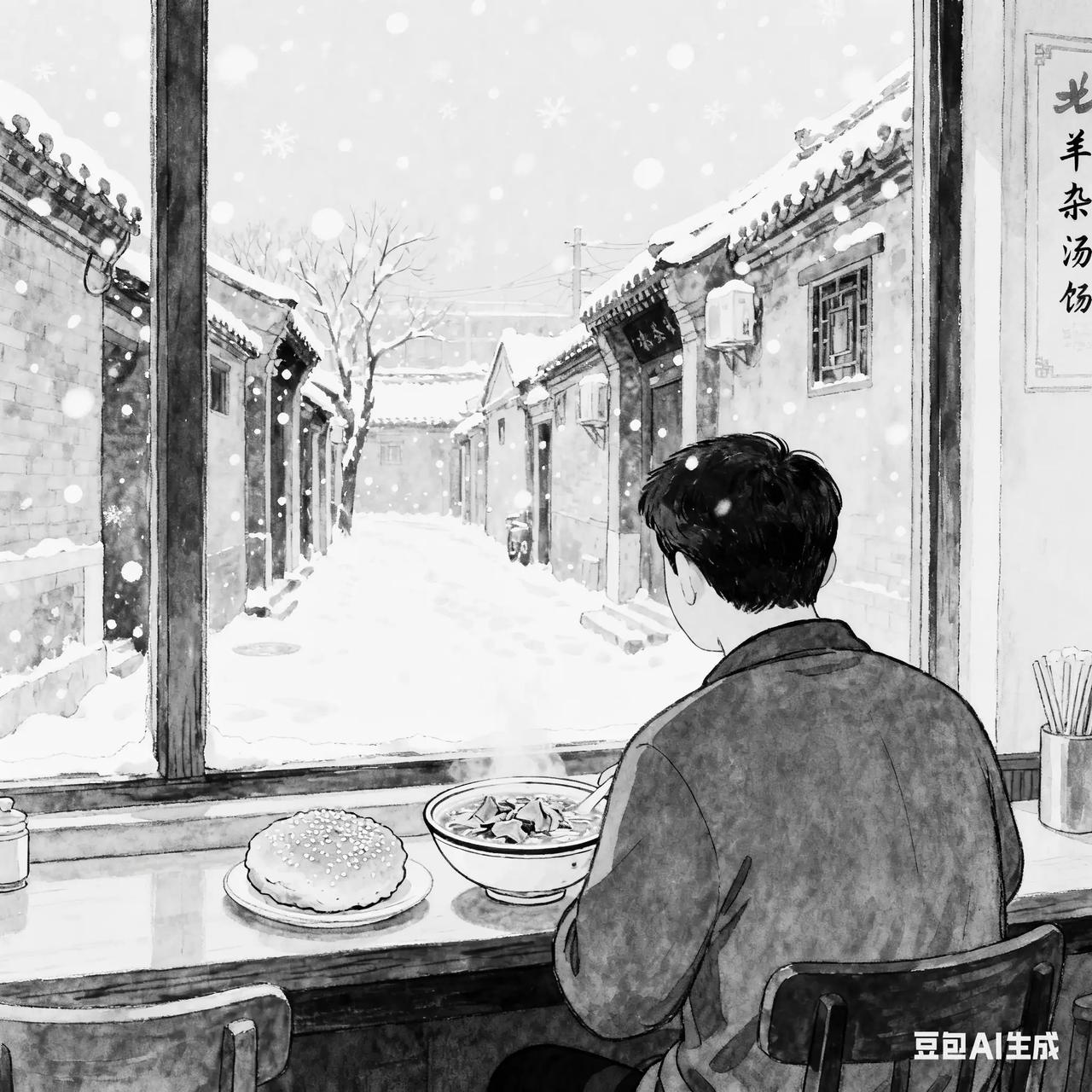凌家滩的玉琮在地下埋了五千年,挖出来时还沾着长江中下游的湿土,
这是安徽最早的模样,新石器时代的人在这里磨玉、种稻,把文明的根扎进江淮平原。
后来楚越在这里争得头破血流,
秦一统后设九江郡,“江淮之域,地兼吴楚,风杂南北”,
这句旧志里的话,道尽了它的地缘宿命。
到了北宋设徽州府,这片山地才算活出了筋骨。
徽商挑着茶叶走徽杭古道,脚底板磨出血泡也舍不得扔半块干粮,
赚来的银钱没堆成银山,倒建起了白墙黑瓦的马头墙,
还养出了新安理学的朱熹、画新安画派的弘仁。
歙砚在匠人手里磨了几百年,墨汁渗进纸里,就是半部江南文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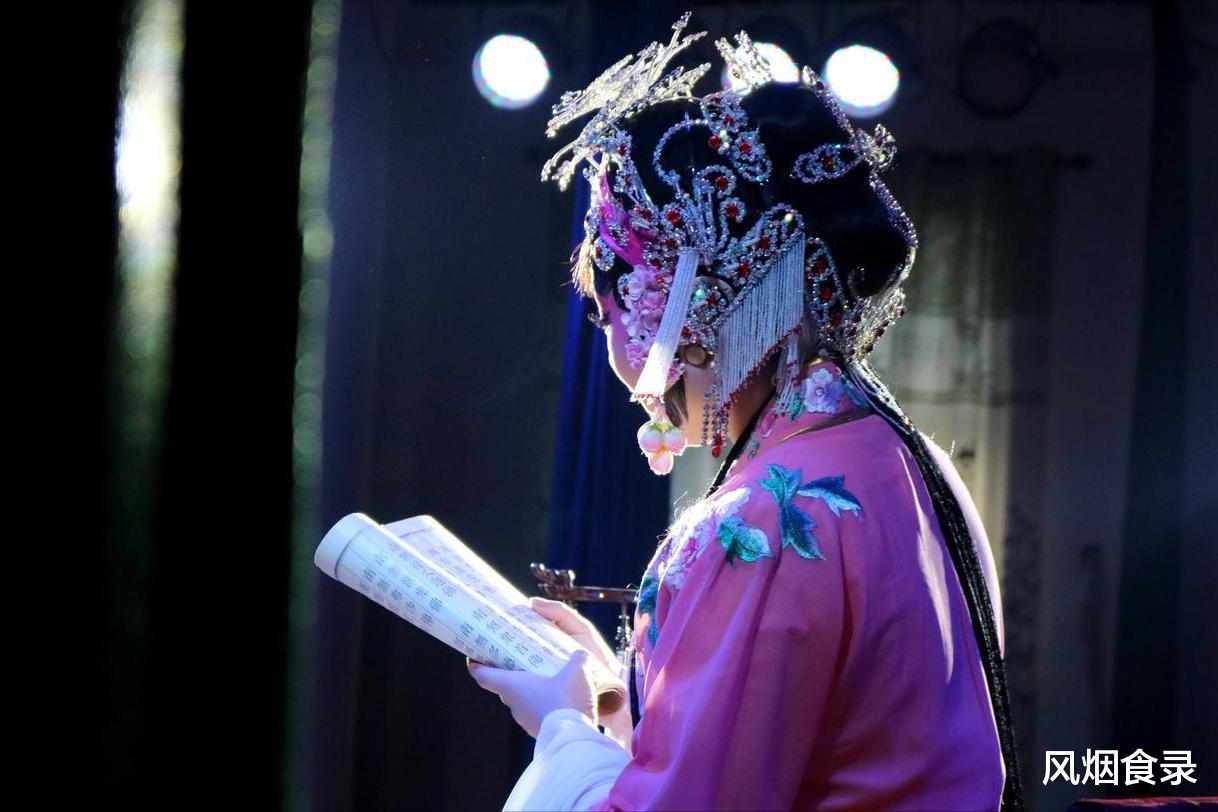
民俗是刻在骨子里的。
黄梅戏的调子从安庆乡下飘出来时,还带着稻花香;
冬至徽州人做麻糍,捶打糯米的声音能传半条街。
“程门立雪”的典故就出自洛阳,但杨时是歙县人,他站在雪地里等老师的模样,
早被安徽人揉进了待人接物的规矩里。
如今马头墙还在,只是墙下的路,早已不是当年徽商走的石板路了。
今天,跟诸位聊聊安徽的十大糕点……

元末朱元璋兵败徽州,饥肠辘辘时啃了农户塞来的烧饼,直咂嘴:“救驾有功!”
登基后便赐名“救驾烧饼”。
清乾隆下江南,徽商江春献上改良版烧饼,乾隆尝罢拍桌:“堪比朕的皇印!”
从此又名“皇印烧饼”,这俩典故在《歙县志》里白纸黑字写着,不是瞎编。
这烧饼形似蟹壳,
金黄酥脆,梅干菜扣着肥膘肉,咸香里裹着甜,外皮“咔嚓”一咬就碎,内里润得直冒油星。
徽州人说“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烧饼”,
从前徽商走南闯北,腰里别包烧饼,耐嚼扛饿,如今屯溪老街现烤的烧饼,
还是炭火贴炉烘,松木香混着芝麻香,闻着就挪不动步。

是安徽黟县渔亭镇的“徽商干粮”,因产自古时“七省通衢”的渔亭码头得名。
据《黟县志》载,明清徽商“十三四岁往外一丢”时,
雨伞、包袱、干粮三件套里,这黑灰糕点能占两成,
用本地黑芝麻、米粉混麦芽糖压模烘烤,不沾牙、耐储存,配黄山茶吃更香,“香得嘞”成老辈人年节必打糕的由头。
典故里它藏着“能吃的徽雕”名号:
模具刻着玉如意、麒麟等徽派木雕纹,脱模时“噼啪”声像放鞭炮,年味便从这声响里冒出来。
如今这糕已列非遗,黑灰主调与徽州粉墙黛瓦呼应,
咬一口酥脆松香,甜而不腻,是活着的徽商文化密码,
当年商帮走南闯北靠它充饥,今儿游客捎它当伴手礼,尝的是历史,品的是烟火。

安徽黄山的“能吃的徽墨”,诞生于1978年程积如团队之手,却藏着千年典故,
南唐后主李煜被汴京软禁时,徽州制墨高手奚廷珪急中生智,
用黑麻馅混墨模制成假墨锭,助李煜躲过“私取贡物”之罪。
这“墨香救主”的传说,让徽墨酥从糕点升格为文化符号,成了徽州人“肚里有墨水”的祝福载体。
它形如徽墨锭,6厘米长、4厘米宽、1厘米厚,
乌黑油亮似浸墨,入口先融后化,芝麻香裹着清甜漫开,甜而不腻,油酥柔韧如宣纸轻触舌尖。
更妙的是,它用黟县“五黑”之黑芝麻为主料,经三晒三炒、石磨细研,
配麦芽糖、糯米粉调和,既锁住墨香,又添润喉滋肺之效,
连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都夸“甜得有文化”。

安徽黄山屯溪的“顶顶好”酥糖,南宋始,明清扬名,乾隆亲赐“顶市”二字。
当年徽商江春夫人以麦芽糖、芝麻、面粉制酥,乾隆尝后直呼“顶顶好”,遂得名。
这红纸包的麻酥糖,藏着徽州人“拜年不带它,
别进厅堂”的讲究,四平八稳的长方体,白里透黄,抓起成块,提起成带,
咬一口,甜香裹着芝麻的浓烈直冲鼻腔,不粘牙不粘纸,老幼皆宜。
2014年,这手艺列入安徽非遗,
熬糖的火候、拉糖的力道、铺粉的匀称,全凭老师傅的手上功夫。
如今,它仍是徽州人春节的“利市糕点”,红纸上的店招,是乡愁的印章。
吃一口,麦芽糖的甜、芝麻的香、饴糖的柔在嘴里化开,
像极了记忆里围炉守岁的年味,热乎、实在,带着烟火气的甜。
这口酥,不仅是美食,更是徽州人“四季平安”的祈愿,嚼着嚼着,就嚼出了岁月里的暖。

宋神宗年间,王安石游天柱山遇雪,当地工匠献上洁白米糕,他脱口而出“顶雪”,
后献糕于神宗,遂成贡品。
明永乐年间再献朱棣,封“宫廷名点”,
清光绪时更在南京赛会获慈禧盛赞,近六百年间,
它从山野小食蜕变为皇家贡品,如今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逢年过节,当地人互赠贡糕,图个“步步高升”的吉庆。
这糕片薄如纸、捻如牌,白得像雪,咬一口软糯香甜,入口即化,
麻油香混着糯米甜在舌尖打转。
制作要经二十道工序:
陈化糯米粉、精炒拌糖、润湿压糕、清蒸切片,每片都切得匀称,点着能燃如烛。
老辈人说,“真当得味!”

安徽黟县、歙县一带的“酥中翘楚”。
它诞生于明清徽商鼎盛时,商人带回外地制糖技艺,与本地黄芝麻、麦芽糖融合,成糕点“新贵”。
旧时徽州孩童过年的“顶市酥”红包里,
常塞着这金黄油亮的酥条,取“芝麻开花节节高”之意。
这酥条讲究“三无”无添加剂、无色素、无防腐剂。
精选徽州土黄芝麻,柴火炒香后拌入熬得稠稠的麦芽糖,
再掺入核桃、枸杞碎,手揉成条,切段冷却。
咬一口,外层酥脆得“咔嚓”响,内里却软糯不粘牙,芝麻香混着麦芽甜在舌尖打转,像极了徽州人“外刚内柔”的性子。
当地老话讲:“玉条酥下肚,日子甜过初。”如今它仍是徽州茶馆的“黄金搭档”,配一盏黄山毛峰,甜而不腻,香而不齁,满口都是老底子的烟火气。

清同治年间余庆堂古戏台下,总飘着黄豆香,
那时人们听黄梅戏,必嗑这糖,咬下“福”字,甜得直咂嘴。
这糖不简单,28道手工工序,黄豆粉裹麦芽糖,黑芝麻嵌成“寿”“喜”,
黄黑双色如太极,刀切时字不乱、味不散,像把福气锁进方寸间。
如今这糖更“有文化”:
非遗传承人金惠民在糖里刻“一盔一带”,让老手艺活成新信物;
2020年阿斯塔纳世博会,它成了徽文化“代言人”,老外尝一口直喊“真得味”。
咬开糖皮,豆香、芝麻香、麦芽香三股子冲上头,甜而不腻。
这哪是糖?
是徽州人的“年味密码”,是手艺人对汉字的敬畏,
是方寸间藏着的千年烟火气,
咬一口,甜到心里头,也甜到文化根里去。

清道光二年,天长状元戴兰芬将“龙岗雪饺”献给道光帝。
皇帝咬下酥脆饼皮,甜香裹着油润在舌尖炸开,如饮甘露,当场赐名“甘露饼”。
民间更传主考官为避“史球”谐音“死囚”不吉,
力荐戴兰芬,取“天长地久,代代兰芬”之吉兆,这饼便成了皇家贡品,名扬四方。
这饼形似白牡丹,九层酥皮薄如蝉翼,炸后撒霜粉缀青梅红丝,一口“剋”下去,酥脆化渣,甜而不腻,低糖低油,老人小孩都爱。
如今它是安徽非遗,
制作全靠手工,张春根夫妇守着老手艺,春节每天要做五百盒。

池州九华山的“佛国味道”,起于唐代地藏菩萨金乔觉修行时。
传说高僧将素斋余料制饼济贫,百姓争相效仿,后成寺庙供品,如今是安徽金牌旅游小吃,2015年制作技艺列青阳非遗。
这饼子“蛮灵光”,外皮金黄酥脆不沾牙,内馅藏着九华山野生黄精的清甜,
咬一口,麦香混着黄精的草木香在舌尖打转,甜得“嗲嗲的”,却丝毫不腻,咽下后喉间还回荡着淡淡的回甘。
它不仅是茶点,更是九华山禅意时光的载体。
香菇木耳馅最经典,山间云雾滋养的菌菇,搭配黄精的温润,咬开是酥脆的“咔嚓”声,接着鲜香在嘴里“炸开”,最后是黄精的清甜缓缓收尾。
如今,这素饼从佛堂走向市井,成了池州人日常的“烟火气”,
也成了游客“朝九华、拜地藏”后最妥帖的伴手礼,
毕竟,不吃素饼,九华山的禅意可就少了一半呢!

北宋淝河岸边,翁家媳妇为病中婆婆烤了块金黄酥脆的薄饼。
婆婆咬一口便问:“这是哄糕?”(合肥话“什么糕”),儿媳随口应:“是烘糕!”
这声“哄糕”便成了八百年前的美味密码。
金兵南犯时,刘琦将军率兵过此,翁老太捧出存了许久的烘糕犒军。
将士咬开那层酥皮,米香混着糖甜在舌尖炸开,连说“得味”!
从此“烘糕”名震四方。
如今的烘糕,外皮微脆似月牙,内里松软如云絮,甜得清润不齁嗓,咬一口“咔嚓”响,连碎渣都带着糯香。
当年岳家军啃着它打胜仗,如今老合肥人走亲访友还拎它当伴手礼。
不是啥稀罕物,却比蜜甜,比岁月长。

这些糕点躺在橱窗里,像褪色的老照片。
你掰开一块徽墨酥,黑色的碎屑落在掌心,突然想起外婆用皱纹纸包糖的手。
甜味在舌尖化开的瞬间,石板路醒了,马头墙醒了,徽商驮着茶饼的脚步声从地底传来。
原来我们都带着一个安徽的胃,
它记得炭火炙烤烧饼的焦香,记得麻糍捶打的节奏,记得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乡愁。
现在你知道了,当甜味漫上喉头,
五千年的江淮平原正在你身体里下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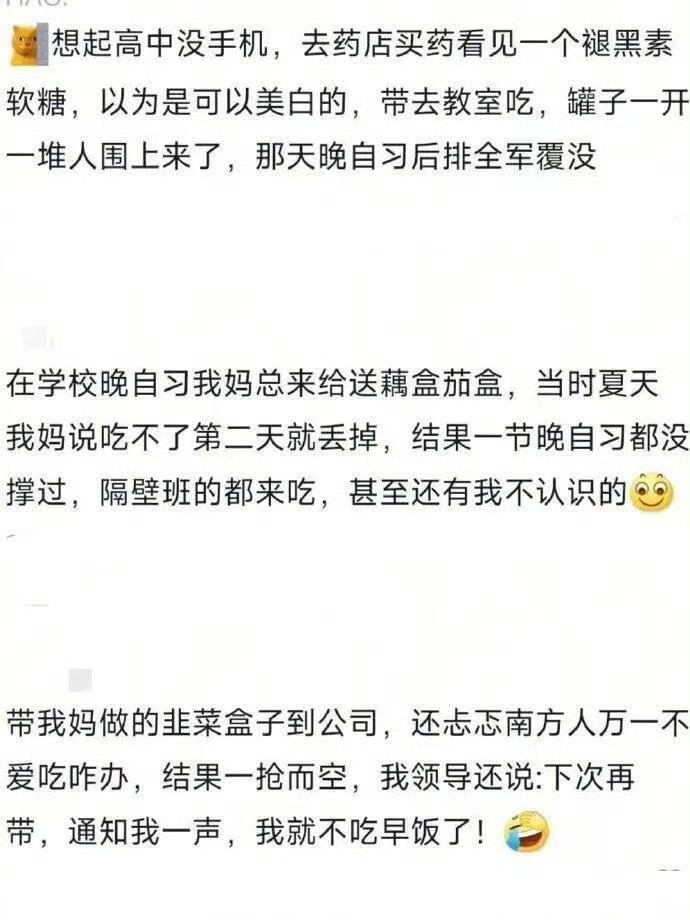
![我国没有争议的南方12省过年吃饺子的就是北方这个最准[呲牙笑]南北方是以](http://image.uczzd.cn/2211055942514969960.jpg?id=0)
![蛇肉真的好吃吗?手都被咬了还想着吃[捂脸哭]才给我吃我也不敢吃](http://image.uczzd.cn/1355193433960644355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