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诗,一段历史,一个小故事

历史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可以让无聊的人,有点事干,比如造个谣。
反正古人已经作古,谁也没见过他们真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去自证清白。
于是,另一波“无聊之人”,也有了事干,开始辟谣,也许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产能量化。
可人往往有个共通点,“看热闹不嫌事大”,总是容易轻信那些新奇的,比较炸裂的故事,哪怕从未发生过。
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二十七岁的李绅赴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写了一组干谒诗,即《悯农二首》,其二为: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诗的经典程度,已经可以和骆宾王的《咏鹅》相媲美了,是学龄前儿童必读之作,更是被写进了小学课本,尤其诗的寓意很适合良性教化。
拒绝浪费,自古就是传统美德。
但是1200多年以后,这首诗几乎又成了反面教材,因为都传诗人李绅奢侈无度,为了一盘鸡舌,一餐可以杀掉300只鸡。最重要的是,李绅还好色,家中歌妓成群。

有一次刘禹锡应邀赴李绅宴,酒过三巡后,李绅爽快地将佐酒的歌妓赠给刘禹锡,欲成好事。心直口快的刘禹锡实在看不下去,遂作一首讽刺诗,即《赠李司空妓》:
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
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
如此也就罢了,李绅还是个“酷吏”,草菅人命不眨眼。总之,李绅成了“坏人”的典型,拍成影视剧,绝对是大反派,毕竟他曾位极人臣,为文宗朝宰相。
他的这些“坏事”,许多知名学者也在传,各家百科多有收录,相信很多人也都在网上读过这样的文章,或者刷到过这样的视频,讲的真是有鼻子有眼,连出处都有。
所以几乎见不到有人为李绅辟谣。
我不能说,李绅是一个好官,毕竟中晚唐局势复杂,但在我的印象里,他绝对没有黑化到这种程度。
首先,李绅受知于韦夏卿,韦夏卿是元稹的岳父,所以李绅和元稹的关系特别好,他入京科考,住的就是元稹在长安的故宅。

受李绅影响,元稹才写了《莺莺传》,著名的“新乐府运动”就是由李绅和元稹率先发起的,白居易还要略晚一点才参与进来。
而李绅、元稹同为“李党”成员,亲李德裕,李德裕为李党首领,中唐时期著名宰相,死对头是“牛党”牛僧孺。
因此,元稹也有许多绯闻,比如和“四大女诗人”中的薛涛、刘采春,此事我们之前就辟过谣,这里不再多讲。
牛李党争前后持续了四十多年,在朝官员几乎无人幸免,就连老好人白居易,也有牛党之嫌,但他两边都能做朋友,尤其和元稹、李绅关系特瓷实,这也是一种本领。
两党成员相互倾轧,元稹得器重时,蒋防为了巴结元稹,特意写了一本《霍小玉传》,来恶心牛党李益。
因此我们说过,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莺莺传》为元稹自传体小说,极有可能是来自政敌的舆论攻击。
现在我们看回刘禹锡那首讽刺李绅的《赠李司空妓》,许多人都说,李绅的“坏事”载于唐人范摅(shū)所著的《云溪友议》,以及唐人孟棨(qǐ)编撰的《本事诗》。
“刘尚书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集贤学士。李司空罢镇在京,慕刘名,尝邀至第中,厚设饮馔。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刘于席上赋诗曰:“鬟髯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江南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
这是《本事诗》中的原文记载。

入唐后,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正一品,轻易不授,多为死后以荣誉追赠。
所以十分肯定,李绅生前和死后,从未授司空,但同一时期,李德裕却被授予司空一衔。倒也不是李德裕做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过是刚刚即位的武宗李炎贪玩,半夜出去游猎,遭宰相李德裕斥责。
李炎为了安抚李德裕,随手就封了一个司空。这一年是公元740年。
恰巧,这一年前后刘禹锡作《秋声赋》和李德裕,两个人私交一直很好,所以刘禹锡笔下的《赠李司空妓》,当是写给李德裕,至少不是写给李绅的。
尤其,《云溪友议·卷中·中山诲篇》对此事也有记载,乃刘禹锡与牛僧孺之间论诗的趣事,却被移花接木,硬按到李绅头上。为此,笔者特意查了《云溪友议》刻板,作者自序为:
“街谈巷议,倏有裨于王化。野老之言,圣人采择。孔子聚万国风谣,以成其《春秋》也。江海不却细流,故能为之大”
意思就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或对教化有用,才写了这本书。圣明的君主,连乡下老者的话都会参考,就像孔子收集各国民谣,最终著成《春秋》一样。江海之所以浩瀚,因为广纳细流。
你看,连作者自己都很不自信,偏偏有人信了。

笔者翻遍了两本书,也不曾见李绅豪奢之语,“鸡舌宴”更是无稽之谈,而其他后代诗选、笔记等,皆是参考这两本书,毕竟时间点更接当事人。不同的是,唐以后的著作,和李绅有关的,皆是一点点加料,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但李绅是否为“酷吏”这件事,更值得仔细说一说,毕竟这不是花边绯闻了,而是一个人的品节清白。
李绅有一个侄子,叫李虞,小有名气,自视清高,常对人说自己不愿当官。
李虞有一个堂伯父,叫李耆,经李绅提擢,授左拾遗。李虞得知这件事后,又觉得自己可以当官了,遂写信给李耆,希望他能向朝廷举荐自己。
然而这封信,却阴差阳错送到了李绅手中,也是神奇,所以李绅很生气,将李虞训斥了一通。
李虞很不服气,就来到了长安,对向前宰相李逢吉说,李绅背后讲过他坏话。李逢吉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遂物色了一个狠人,即刘栖楚。
原本,刘栖楚只是一个司仓小吏,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因事惩罚他时,刘栖楚以头撞地,坚决抗辩,胆识过人。李逢吉觉得,如果用他为谏官,窥伺李绅过失,必定能将其扳倒。
不久,李逢吉将李虞、刘栖楚都提拔为拾遗,同时请宦官王守澄来助自己。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穆宗崩,太子李湛即位,为敬宗。李逢吉认为时机已到,便让王守澄上奏,称:先帝始议立储时,李绅劝立深王,只有李逢吉请立陛下,而李虞也曾助他。
于是,刚登基还一脸蒙的敬宗,将李绅贬为端州司马。不得不佩服,这的确是好手段,中晚唐政坛,腹黑者众。

李绅被外放后,朝中百官纷纷祝贺李逢吉,唯独右拾遗吴思不贺,李逢吉又将他改为吐蕃告哀使,一放万里。
为此,翰林学士韦处厚看不下去了,为李绅鸣冤,刚好敬宗翻阅旧书时,发现了穆宗生前留下的一箱书信,其中就有一封李绅曾拥立他的证据。
于是敬宗下旨,为李绅量移,出江州刺史,再转滁州、寿州刺史。在任期间,政绩突出,屡得嘉奖。
公元826年,敬宗被宦官所害,江王李昂在宦官王守澄、杨承和等人拥护下,登基称帝,为文宗。
次年,郑覃得重用,欲召回李德裕,却被宰相李宗闵(牛党)所阻。随后,李宗闵将牛僧孺召回,牛僧孺再登相位,李党遭到沉重打击,几乎全被外放。
公元840年,文宗崩,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拥立其弟李炎为帝,是为武宗。同一年,李德裕回朝,拜相,加司空,随后李绅升淮南节度使,没过多久就被召回,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封赵国公。
为相四年后,李绅因有足疾,无法上朝议事,故而请辞,再出淮南节度使。到任后第二年,也就是公元845年,李绅卷入“吴湘案”。
就是这件案子让李绅晚节不保。
此事错综复杂,还要追溯到李德裕父亲李吉甫为相期间。时沣州人吴武陵因贪墨,被贬为潘州司户参军,侄子吴汝纳坐罪流放,一直没有被调回。吴汝纳因憎恨李吉甫,便依附于李宗闵。
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吴汝纳复官为永宁尉,弟弟吴湘任江都尉。有一天,部下告发吴湘贪污粮银,并强娶百姓颜悦之女为妻。
按唐律,地方官员不得娶自己辖区范围内的平民女子为妻为妾,违者杖刑。于是,李绅命人彻查此事,经核审,吴湘犯罪属实,上报后将吴湘处死。
但李绅的政敌,在朝中放出风说,吴湘、吴汝纳与前宰相李吉甫有仇,而李绅结党李德裕,这才罗织罪名,对吴湘打击报复。
武宗命御史崔元藻、李稠复查此案,崔元藻取证后回禀,吴湘贪墨证据确凿,强娶民女或有不实,因颜悦曾担任青州衙推,其女自然出士家。
李德裕此时在相位,觉得崔元藻、李稠身为御史,态此飘忽不定,不堪大任,遂将其贬出。
公元846年,李绅病逝于扬州,终年七十五岁,追赠太尉,谥号“文肃”。

同一年,武宗驾崩,宦官马元贽拥立“皇太叔”李忱称帝,为宣宗。随即,李德裕被罢相,前宰相崔铉唆使吴汝纳为吴湘伸冤,于是吴汝纳上奏,称弟弟吴湘被屈打成招,实为李绅枉杀。
随后又上书说,吴湘死后,李绅下令立即埋葬,不得归乡,即便是有罪之人,也要秋后处斩,可李绅镇守一方,罔顾国法,竟将吴湘于盛夏时分处死。
崔元藻因怨恨李德裕将自己贬出京师,也翻改证词说:从淮南审理此案归来,本该当面向皇帝奏明情况,奈何李德裕扣表不报,御史台只好维持李绅判决。
此时李德裕已经失势,牛党令狐绹、崔铉、白敏中皆身居要职,遂指使崔元藻等人构陷李德裕,将其贬为崖州司户参军。虽然此时李绅已经病逝,但依旧被定性为“酷吏”,削三官,令子孙不得入仕。
同时吴汝纳升左拾遗,崔元藻出任武功令。
纵观整件事,皆因党争而起,而且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吴湘的确贪墨,按律当斩。凭此把李绅定为“酷吏”,委实有些牵强。
当然,李绅依附李德裕,参与党争,也是不争的事实。
李德裕死后,牛党对其成员多有污蔑,所以才有了《云溪友议》、《本事诗》这样连史书都算不上的著作。李绅、元稹皆曾为相,政敌强加毁誉,没想到现如今,依然有人相信。
这种不加考证,亦不思辨的行为,对研究历史这样严肃的事而言,属实不妥。
纵观上下五千年,古人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在为后人搭桥铺路,就连隋炀帝杨广那样的昏君,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财富。
而我们却人心不古,常常添油加醋、讹附夸张去对待古人,当自问自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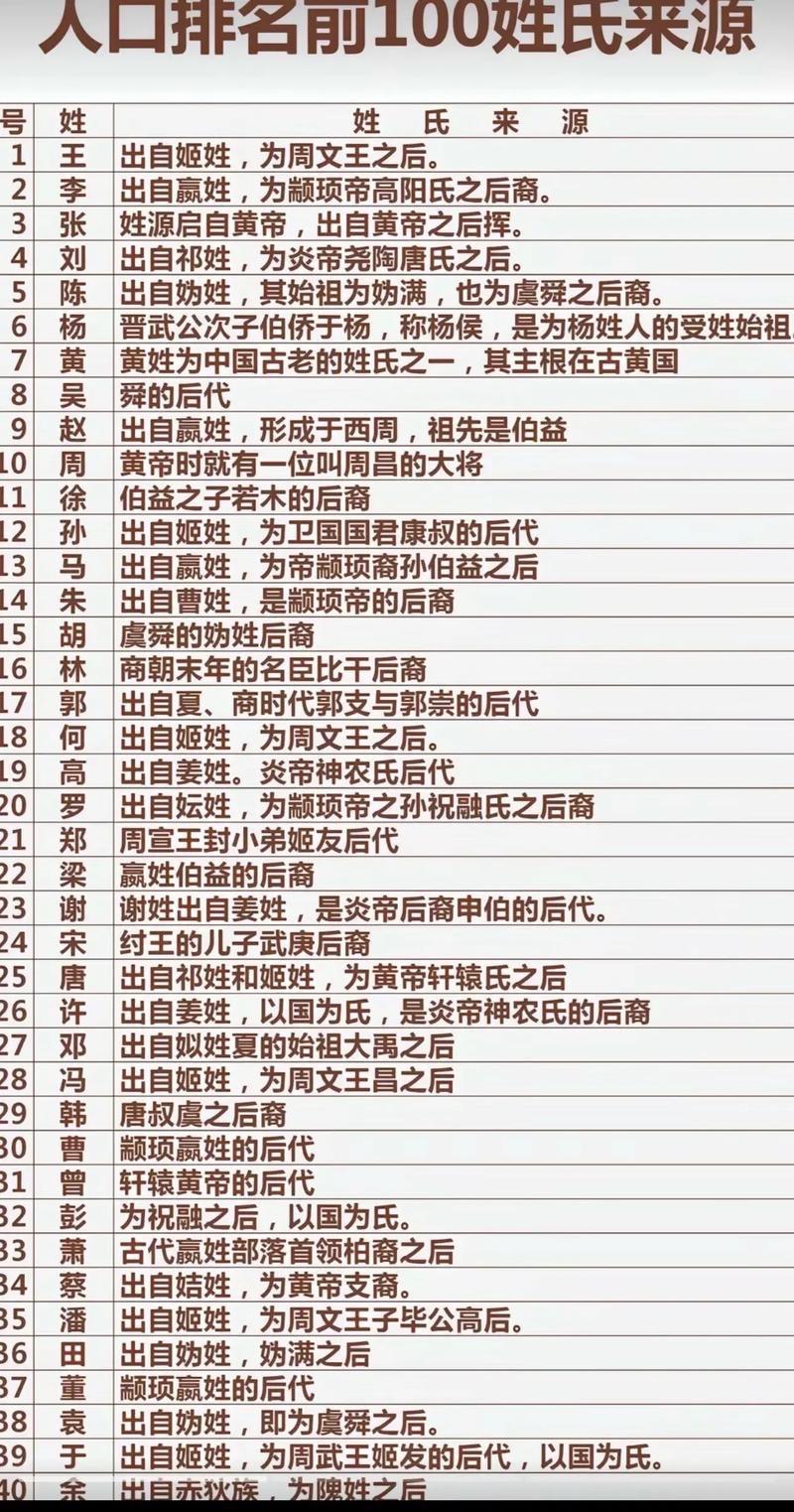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