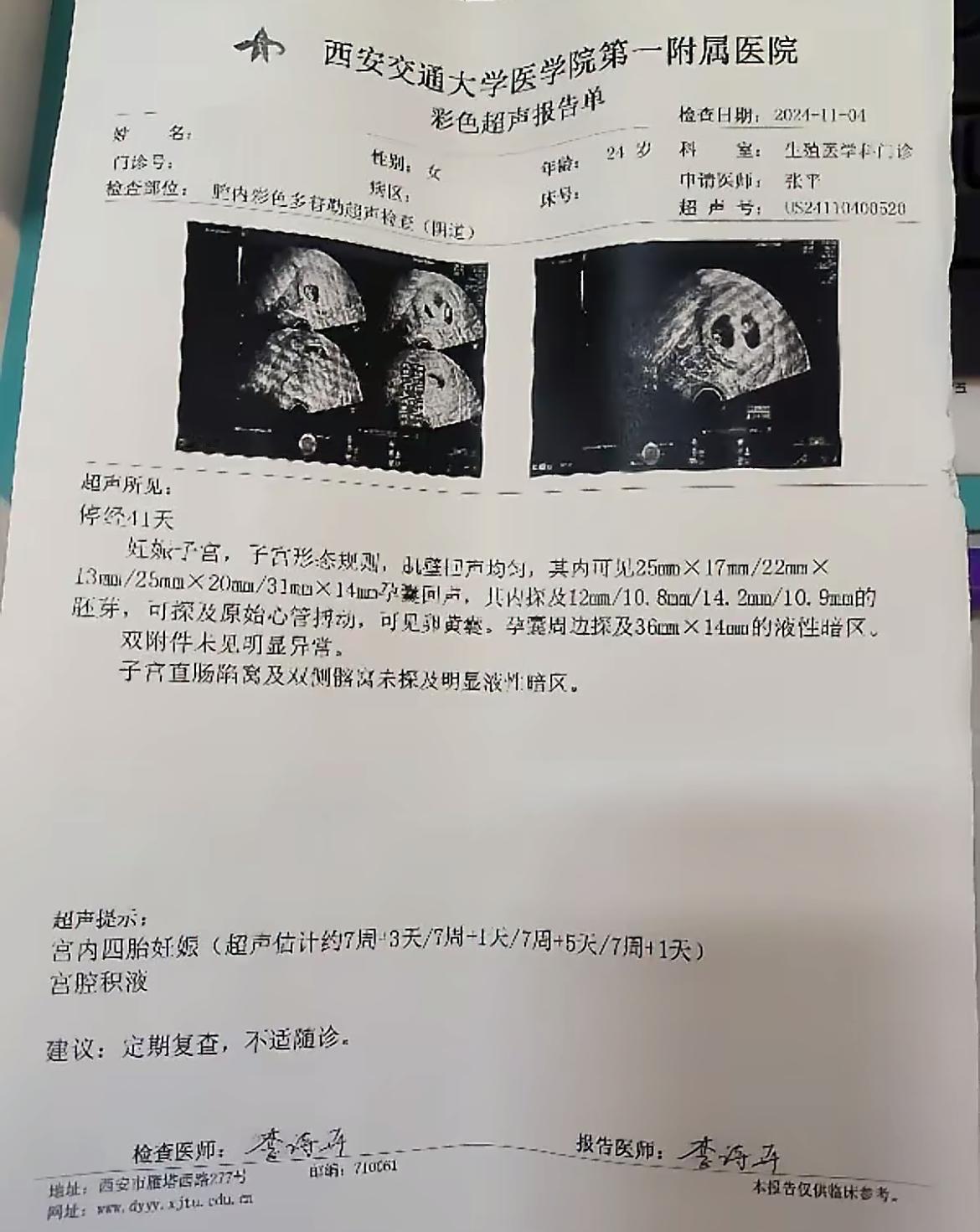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 1992年5月,84岁的毛森坐着轮椅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这个曾经的军统上海区区长,离开大陆已经43年了,机场大厅里“上海欢迎您”的牌子刺得他眼眶发酸,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领口别着褪色的梅花扣,那是军统的象征,半晌才憋出一句上海话:“没变……又好像全变了”。 推着轮椅的是他的孙子,一个在台湾出生长大的年轻人,听不懂这句带着浓重吴语腔调的感慨。 毛森的手指颤抖着,划过机场光洁的大理石地面,记忆里的上海机场,还是泥地跑道,候机楼是简陋的平房,如今的高楼玻璃幕墙晃得他有些睁不开眼。 他的思绪一下子飘回了1949年的春天,那天也是在上海,天阴沉沉的,他穿着同样的中山装,领口的梅花扣擦得锃亮,手里攥着飞往台湾的机票,身后是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的慌乱,身前是不知归期的漂泊。临走前,他站在十六铺码头,看着黄浦江的水滚滚东流,以为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 毛森这辈子,活得像一出跌宕起伏的戏。他早年加入军统,凭着狠辣的手段和过人的胆识,一路坐到上海区区长的位置。 抗战时期,他带着手下潜伏在上海,刺杀汉奸,破坏日军的补给线,好几次差点被活捉,肩膀上的枪伤就是那时候留下的。 那段日子,他觉得自己是英雄,是在为国家做事。可到了内战后期,他手里的枪指向了不同的人,那些曾经并肩抗日的同胞,变成了他要抓捕的对象。 他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离开,看着上海的街头从硝烟弥漫变成红旗招展,心里说不清是愧疚还是迷茫。1949年的那个清晨,他没敢和任何人告别,悄悄登上了去台湾的飞机,从此,故乡成了遥不可及的念想。 在台湾的几十年,毛森过得并不如意。军统改组,昔日的同僚要么失势,要么流亡,他也渐渐被边缘化。他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摩挲着领口的梅花扣,那是他从上海带出来的唯一念想。孙子问他,梅花扣是什么,他只说,是一个老朋友送的。 他不敢说,这枚扣子,见证了他的荣耀,也见证了他的过错。晚年的他,身体越来越差,腿脚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唯一的心愿,就是回上海看看。这个心愿,他藏了四十多年,直到两岸关系缓和,才终于敢说出口。 车子驶出机场,驶入上海的街头。毛森的眼睛一刻都不敢眨,生怕错过什么。曾经的石库门弄堂还在,只是墙上刷上了崭新的标语;黄浦江的水还在流淌,只是江面上多了座宏伟的大桥;街头的叫卖声换成了汽车的鸣笛,却依旧带着他熟悉的上海味道。 车子路过他曾经的住所,那里已经变成了热闹的商场,他让孙子停下车,坐在轮椅上,久久地望着。当年的院子里,种着一棵梧桐树,如今,商场门口也有一棵,枝繁叶茂,和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路过一家老字号的点心店,毛森让孙子买了一笼小笼包。咬下一口,熟悉的鲜甜在嘴里散开,他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四十多年了,味道没变,还是小时候的滋味。他想起小时候,母亲带着他来吃小笼包,那时候的上海,还没有这么多高楼,那时候的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随行的接待人员看出了他的情绪,轻声说:“毛老先生,上海的变化很大,但根还在。”毛森点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他知道,自己曾经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他曾经站在时代的对立面,如今,他以一个游子的身份,回到了故乡。领口的梅花扣依旧褪色,可他的心境,早已不同。 离开上海的那天,毛森把那枚梅花扣取了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了纪念馆的展柜里。他对孙子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看着窗外的上海,渐渐变小,变成一个模糊的点。他知道,这次回来,了却了他半辈子的心愿。 叶落归根,是每个游子最深的执念。毛森的一生,有过荣光,有过过错,可当他踏上故乡的土地,所有的恩怨情仇,都化作了一句“没变……又好像全变了”。故乡的变化,是时代的进步,而不变的,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没钱上海只是上海,有钱哪里都是上海[吃瓜]](http://image.uczzd.cn/2375813697858735623.jpg?id=0)

![你们一堆成年人欺负我….[笑着哭]近日上海,高铁上发生了这样的一幕,一个宝妈带着](http://image.uczzd.cn/17583722748837147198.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