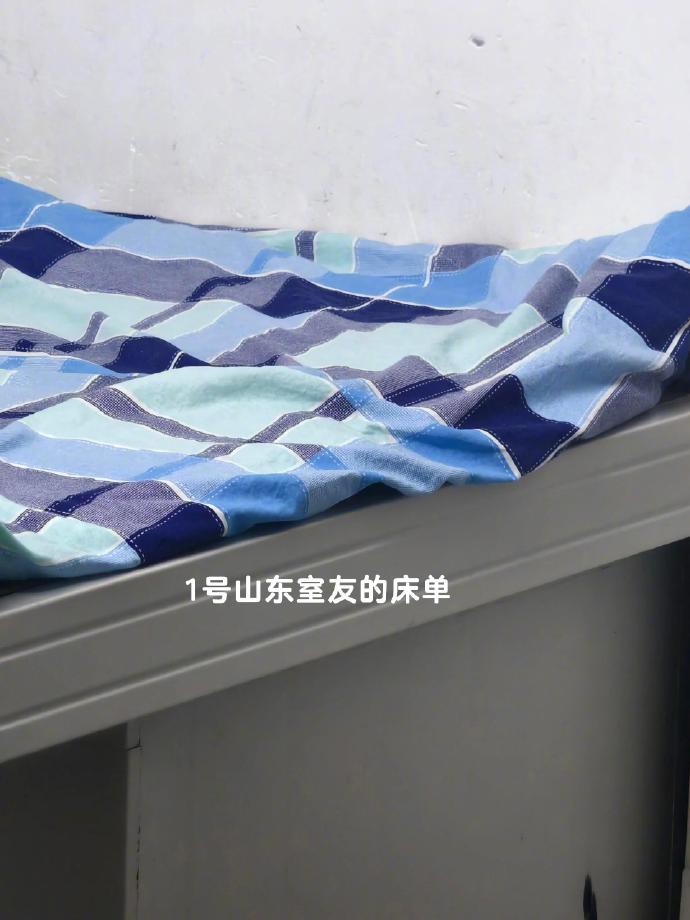我同学儿子的婚礼取消了。昨天同学说十一儿子的婚礼取消了,原来是儿子在领证之前,要两人一起做个婚检,在去领证,结果女友不同意,说都已经同居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病还不知道么,没有必要到医院检查。 昨天傍晚接到老同学电话时,我正往阳台收晾干的床单。 她声音哑着,像被砂纸磨过,说:“十一的席,散了。” 我手里的床单“啪嗒”掉在地上,印着淡蓝格子的那面沾了灰。她儿子小宇,我们看着长大的,去年带女友回家时,她兴奋地发朋友圈,九宫格全是女孩给她织的围巾——米白色,针脚歪歪扭扭,配文“未来儿媳的心意,暖到心窝”。 从三月就开始跑酒店看场地,七月定了喜糖——杏仁味的,说准儿媳喜欢,连请柬上的字体都是小宇选的,说是女友名字里有个“月”字,得配月光银的烫金,印出来像撒了把星星。 “怎么回事?”我蹲下来捡床单,指尖摸到布料上的潮气。 “小宇提的,”老同学叹口气,“说领证前,先去做个婚检。” 电话那头有杯子碰撞的轻响,大概是她在倒水。“他觉得这是流程,也是责任,毕竟要过一辈子的人,健康是底线。” 我想起小宇,话不多但实在,大学时帮室友带饭永远记得多要双筷子,工作后给父母换了智能马桶,说“冬天不冻屁股”。这样的孩子,会提婚检,不奇怪。 “女孩不同意。”老同学的声音低下去,“说‘都住一起两年了,床都一起睡了,有没有病我能不知道?’小宇说‘这不是信不信任的事,是对彼此负责’,女孩就火了,说‘你是不是怀疑我?’” 我想起小宇女友,去年同学聚会上见过,穿浅绿连衣裙,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给大家分水果时,细心地把葡萄皮剥了。那时谁不夸小宇有福气,找了个温柔懂事的姑娘。 “吵了三天,”老同学说,“小宇坚持要检,说‘不是不信你,是万一呢?万一有什么,我们一起面对,总比以后害了孩子强’;女孩就说‘你就是没把我当自己人,同居这么久,我的事你还有不知道的?’” 最后是女孩提的“算了”。 “她说‘婚检都要争,以后日子还怎么过’,小宇没再劝,”老同学的声音突然带了点颤,“我昨天去收拾他房间,看见桌上的请柬样本,还夹着张纸条,是小宇写的:‘婚检报告出来那天,就去领证’。” 我捏着床单的手紧了紧,布料上的潮气好像渗进了皮肤。 其实谁都知道,婚检早不是强制项了,可它像块试金石——有人觉得是多此一举的麻烦,有人觉得是摊开底牌的坦诚。 你说,两个人住同一屋檐下两年,连一张婚检报告都不敢一起面对,这婚结了,真能走得远吗? 老同学今天发了条朋友圈,删了又发,最后只写:“喜糖还在,谁要,来拿。”配图是那个印着月光银“囍”字的盒子,边角有点皱,像被人攥过。 或许女孩只是怕医院排队麻烦,或许小宇把“负责”想得太简单,可感情里最忌讳的,不就是“我以为”和“你应该”吗? 短期看,是一场婚礼的取消;往远了想,是两个年轻人在“要不要把最真实的自己摊开”这件事上,走岔了路。 要是当初小宇换个说法呢?不说“必须检”,说“我有点怕,想跟你一起安心”;要是女孩愿意问问“你是不是担心什么”,而不是直接炸毛呢? 可生活哪有那么多“要是”。 挂电话时,老同学轻轻笑了一声,像风吹过空瓶子:“也好,总比结了再散强。” 我看着地上那床沾了灰的蓝格子床单,突然想起小宇小时候,攥着我的衣角问:“阿姨,结婚是不是两个人要把所有糖都分对方一半?” 那时候他手里攥着颗大白兔奶糖,糖纸都快被捏化了。 现在想来,分糖容易,分真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