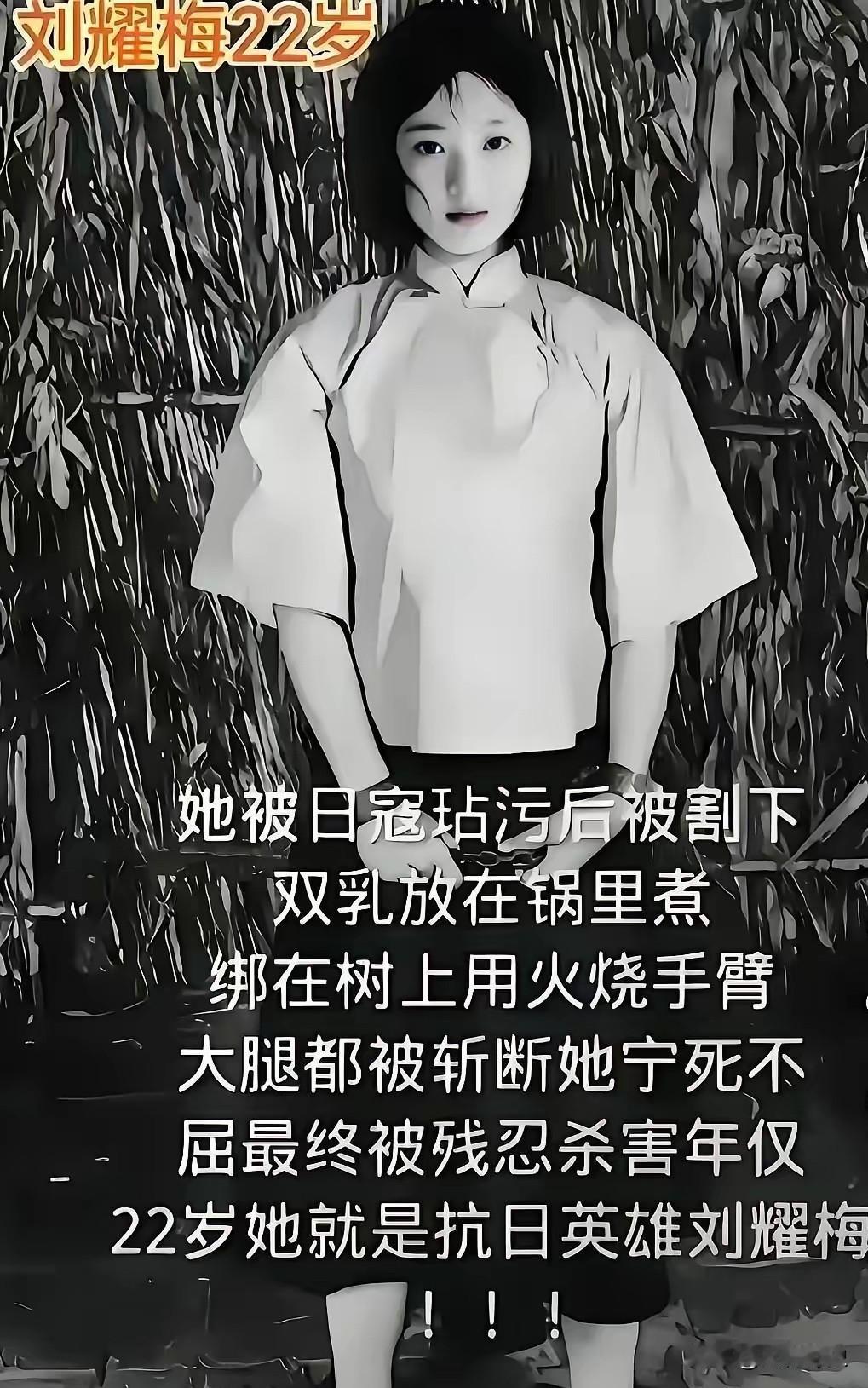1950年,周养浩被押回监房后,举着板凳往沈醉头上砸,被一旁的宋希濂攥住胳膊,小板凳摔到了地上。四人扭作一团。 这一幕被沈醉写进回忆录,只提“略有龃龉”。但当时的唾沫与喘息,实实在在揭开三人二十五年恩怨的序幕。 白公馆关着王陵基、钟彬等国民党高官。这些往日“大人物”挤在同一牢房,填资料、写交待都互相提防,表面客气藏着心思。 三天前的提审,彻底改变局面。 墙角堆着霉味的稻草,宋希濂的粗瓷碗沿缺了个口——1949年冬的西南,败局已定的旧官僚与特务们,在铁窗内仍维持着最后的体面博弈。 周养浩签完供词,文件里滑出一张纸条:“建议判处死刑”,下方是沈醉的字:“周养浩参与渣滓洞大屠杀,杀三十四名共产党员”。 他盯着那行字,喉咙像被砂纸磨过,指甲深深抠进缺漆的木桌。 回到监房时,徐远举正用烧焦的树枝在地上画棋盘,宋希濂捏着石子当棋子。 “姓沈的,你不是人!”周养浩抓起板凳就砸,徐远举嘴角撇了撇——他本就恨透了这种临阵倒戈的“变节者”。 宋希濂左臂肌肉猛地绷紧,板凳砸在胳膊上发出闷响,他顺势踩住凳腿,将周养浩拽开。 沈醉缩在墙角擦眼镜,镜片裂纹里映出徐远举阴鸷的脸,他突然想起三个月前昆明的雨夜。 卢汉副官举着起义通电闯进来:“沈站长,签了它。”18岁入复兴社、28岁当少将的沈醉,握着笔的手抖得像风中的枯叶。 妻儿老母的脸在眼前晃,他最终还是签下名字。可云南日报登出他手令那天,看守却端来一碗没油花的清水面:“卢主席的意思。” 旧部见他绕着走,西南银楼孙老板却探监塞来两根金条:“党国不会忘你。”金条硌得掌心发烫,他忽然明白——自己成了哪边都不待见的棋子。 徐远举的日子也没好到哪去。作为黄埔七期特务,他清楚自己手上的血比周养浩还多,夜里总盯着宋希濂的铺位,怕这位抗日名将因陈赓的关系提前“宽大”。 “送终将军,还能指挥千军万马吗?”徐远举故意踢翻宋希濂的搪瓷缸,缸子在地上转了三圈才停。 1956年春,功德林的阳光透过铁窗洒进来时,沈醉正看着徐远举教战犯们跳集体舞。 穿补丁蓝布衫的徐远举皱纹里夹着汗,递来一缸热小米粥:“老沈,来试试。”这是白公馆扭打后,两人第一次平和说话。 洗澡间飘着肥皂味,洗衣间的搓衣板摆得整整齐齐,病号还能喝到加了红糖的小米粥——沈醉摸着新发的毛巾,突然想起戴笠焦黑的遗体,1946年那具在南京郊外找到的残骸,指甲缝里还嵌着飞机残骸的碎片。 “我们都是棋子。”他对着铁窗喃喃自语,月光落在新添的白发上,像撒了一层霜。 军管会改叫“学员”那天,有人偷偷抹眼泪。参观汽车厂时,杜聿明开着国产汽车绕场一周,沈醉站在人群里,看着厂房顶上的五星红旗,忽然明白对岸的“反攻”不过是场幻梦。 1960年特赦大会念到“沈醉”时,周养浩正在医务室量血压。 水银柱缓缓上升,他想起1948年沈醉教他用勃朗宁手枪:“你枪法比我准,三枪就能打穿门板。” “再量一次。”他按住医生的手,第二次水银柱依旧爬到危险刻度。 1975年周养浩特赦后申请去台湾被拒,滞留香港时打开铁盒,里面是1958年秦城农场沈醉塞给他的云南白药——当时两人蹲在田埂上挖草药,谁都没说话。 1980年统战部电话里的“起义将领”四个字,让沈醉握着钢笔的手停在《文史资料选辑》的“军统三剑客”上。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病逝,1996年沈醉在北京去世。两个斗了大半辈子的人,到死都没真正解开那个结。 或许历史的吊诡正在这里——他们曾以为自己是搅动风云的棋手,最终却都成了棋盘上被遗忘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