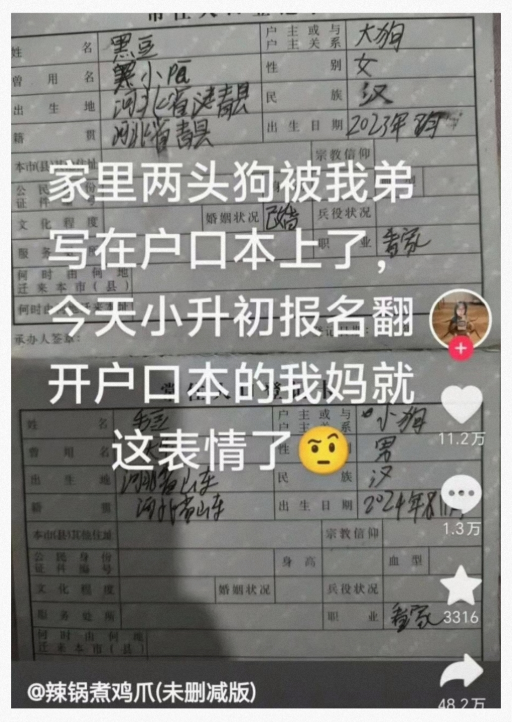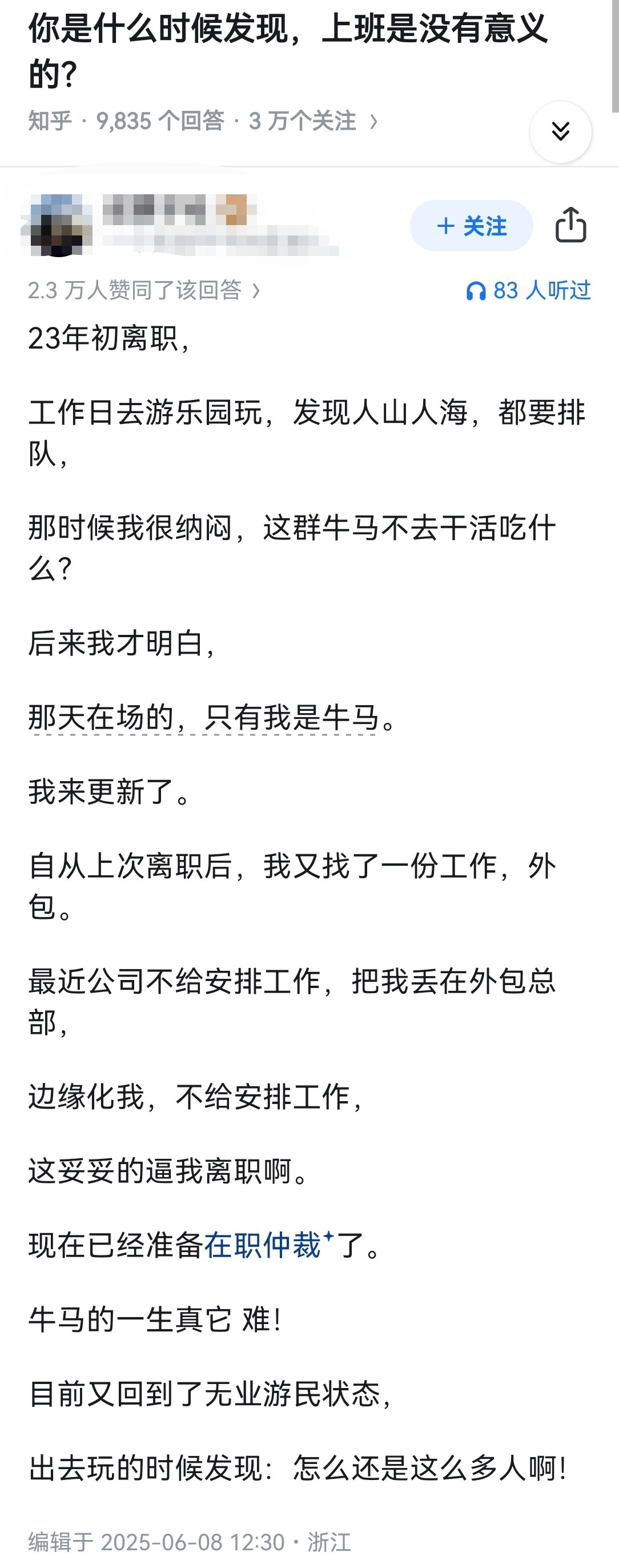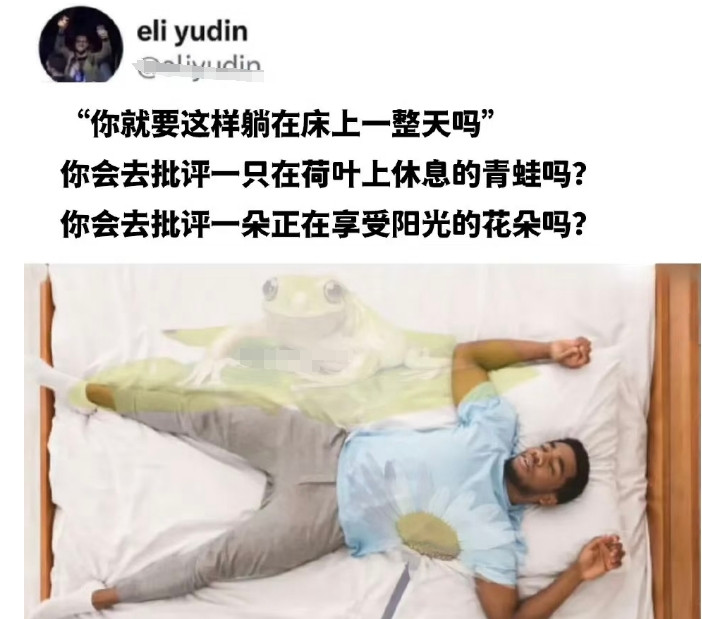公司裁掉她那天,四月的阳光把工位照得发亮。她的键盘上,半干的珍珠还嵌在回车键缝里——是前晚加班喝的芋圆奶茶,吸管还插在桌角空杯里。行政小姑娘抱着纸箱过来时,指尖先碰着了抽屉里那包护肝片,铝箔板已经空了大半。“姐,我帮你装”,话没说完,小姑娘的睫毛就湿了。我们几个躲在茶水间,听见她给儿子打电话,声音软得像泡发的棉花:“妈妈今天早回,带你吃汉堡王,就吃你最爱的皇堡好不好?”她走得快,香水味混着打印机碳粉味在走廊飘了好久。保洁阿姨推清洁车经过,弯腰捡起她工位下的红绳发圈——去年年会抽的纪念品,塑料小元宝被磨得发亮。我记得她当时还笑,说“讨个好彩头,今年多拿点绩效”。晚上部门群少了个头像,她退群前,朋友圈更了张全家福。她老公抱着上小学的儿子,冰箱上贴满房贷还款计划表,红色磁铁压着的数字扎眼:还剩87个月。财务部同事私下算过,十万块的N+1,连她半年开销都不够——学区房每月房贷1.2万,儿子的剑桥英语和编程课,光续费就8000多。上周团建她还说,想给孩子换个好点的小提琴,又怕这个月绩效不达标。我在地铁站口看见她老公,电动车筐里塞着儿童安全座椅。她抱着纸箱坐上去,硬纸板角把装赔偿协议的牛皮纸袋戳出个洞,几张纸露在外面。红灯亮时,她侧过脸擦眼睛,指腹把双十一拼单的打折围巾蹭得发白,风一吹,围巾边的线头飘起来。吸烟区传来人事经理的声音:“补偿金按基本工资算的,绩效本来就不算数……”楼梯间里,两个外包员工正蹲在地上改简历,把年龄栏的“42”涂改成“39”,笔尖把纸戳出了毛边。保洁阿姨把那只小元宝发圈系在清洁车把手上,叮当响着拐进消防通道。第二天,她的工位就坐了个99年的实习生。小姑娘抱着笔记本问WiFi密码,指尖在键盘上敲得飞快,没看见桌底还沾着她掉的一根长发。饮水机换桶装水时,桶身映出我们几个三十大几的脸,像窗台上的绿萝,叶子垂着,没一点精神。后来听说她去应聘便利店店长,老板嫌她不会用新型收银机,连试工机会都没给。送外卖的老同事碰到过她,说在商场扶梯口见她蹲在地上填申请表,年龄那栏被橡皮擦得破了个洞,露出下面隐约的“4”。赔偿金到账那天,公司楼下停了辆搬家车。新来的实习生们围着讨论团建去露营还是漂流,没人注意车窗里的她。她攥着手机反复按计算器,车后视镜映着对面写字楼的玻璃幕墙,强光晃得人睁不开眼。茶水间的微波炉突然“叮”一声,热好的便当飘出隔夜青菜的味道。我的手指悬在键盘上,看着屏幕上的工作周报,突然想起她说过,儿子总问“妈妈为什么总在打字”。窗台上的绿萝又黄了两片叶子,不知道是水浇多了,还是晒得不够——就像我们这些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叶子,会在哪天突然黄掉。那十万块放在银行卡里,到底烫不烫手?大概只有抱着纸箱坐在电动车上的人,才说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