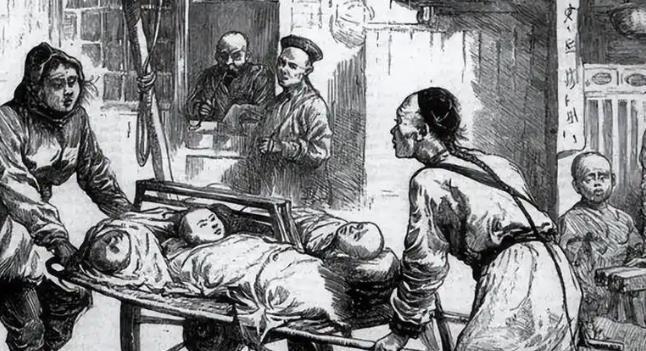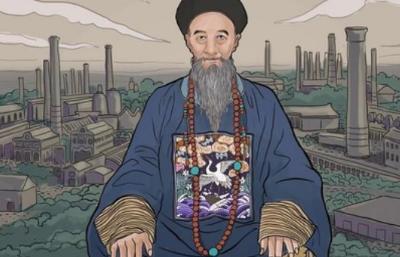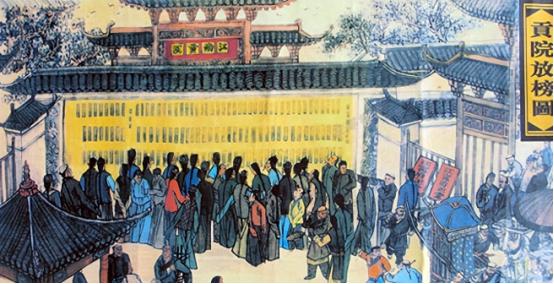1935年,一妓女恳求37岁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递给老鸨一沓钱,没想到老鸨却冷笑道:“带她走?没门!” 1935年那会儿,上海滩正热闹着,租界里洋楼林立,十里洋场里头藏着多少故事。张伯驹这人,家底厚实,父亲张镇芳办了盐业银行,他自己当总稽核,平日里管着账目,闲下来就爱钻研书画诗词。生于1898年,三十七岁了,早不是毛头小子,娶过几房,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北平琉璃厂的古董摊子他是常客,康熙御笔一见钟情,从此爱上收藏,散尽家财也眼不眨。 潘素二十岁出头,原名潘白琴,苏州书香门第后人。父亲潘智合败家,母亲沈桂香早逝,继母王氏狠心,把她卖进妓院。她天生聪慧,从小学音律绘画,进了天香阁,艺名潘妃,靠一手琵琶和琴棋书画,勉强守住清白,没卖身,只卖艺。国民党中将臧卓早看上她,许下婚约,这姑娘就成了香饽饽。民国那年代,军阀混战,达官贵人一句话,就能定人生死。 张伯驹来上海查账,顺道应酬,进了天香阁,本想听听曲儿散散心,谁知撞上潘素一曲《昭君怨》,那音调里头的凄凉,直戳人心窝子。俩人聊起书画诗词,潘素见识不输名士,张伯驹直呼难得。民国四公子之一的他,平日里见惯风月场,可这次不一样,动了真格。 潘素家道中落那几年,辗转上海,进了天香阁半年,日子过得提心吊胆。客人多是军政要人,她弹琴作画,勉强周旋。老鸨收了她卖身契,天天催着接客,可她咬牙顶着,就想找条出路。张伯驹那天听完曲,俩人聊得投机,潘素忽然开口,声音低低地说:“张先生,我守了半年清白,求您带我走吧。”张伯驹一愣,立马从兜里掏出一沓钞票,足有几千大洋,递给老鸨:“赎身,立契走人。”老鸨接过钱,眼睛眯成缝,可一听是赎潘妃,脸拉得老长,冷笑起来:“张先生,您这钱再多也没用。 潘妃早被臧中将订了,带走?没门!”臧卓是国民党中将,手握兵权,在上海滩说一不二,他许的婚约,谁敢碰?潘素闻言,脸色煞白,抓着张伯驹袖子不放。张伯驹没慌,点点头走了,可心里有数,这事儿得从长计议。果然,没几天,臧卓察觉苗头不对,派人把潘素软禁在一品香酒店,门前卫兵把守,潘素哭肿了眼,饭也吃不下。 张伯驹急了,四处托人打听,找上老友孙曜东帮忙。孙曜东那时在上海滩有点门路,俩人商量,买通卫兵,趁臧卓外出,摸黑潜入酒店,把潘素带出。潘素出来时,腿软得站不住,张伯驹扶着她上了车,直奔北平。 路上,俩人没多话,可从此绑在一起。臧卓气得跳脚,扬言要崩了张伯驹,可张伯驹后台硬,父亲老底子在,盐业银行的资源一使,事儿就压下去了。这段插曲,暴露了旧社会军阀的丑陋嘴脸,女子命如草芥,达官随意摆布。张伯驹虽是富家子,可他没仗势欺人,而是用钱和人情化解,保住了潘素的自由。 婚后,俩人回了苏州,拜印光法师,法师给取法号,潘素叫慧素,张伯驹叫慧起,从此她改名潘素,洗手不干旧业。张伯驹请名师教她古文山水画,潘素底子好,很快就上手,画山水人物花鸟,青绿设色直追南宋。俩人夫唱妇随,游山玩水,论诗作画,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张伯驹收藏瘾头大,遇上国宝就砸锅卖铁,《平复帖》花了四万大洋,卖宅子换《游春图》,潘素从不抱怨,还变卖首饰凑钱。 1941年,张伯驹在上海被绑,匪徒要三百万伪币,潘素四处借钱,卖了所有细软,就是不动那些书画,因为张伯驹说过,那比命还重。她跪求旧友,凑齐二十根金条,才赎回丈夫。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够呛,可潘素咬牙扛住,夫妻情分更深。旧社会动荡,军阀土匪横行,张伯驹这样的收藏家,随时可能丢命丢宝,可俩人互相扶持,守住了底线。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文物保护,张伯驹和潘素商量,把家藏的《游春图》《平复帖》《伯远帖》等八件国宝,无偿捐给国家。1956年捐时,有人劝给点奖励,他摇头说:“这些东西本该属于国家,我买来就是防着流失海外。”这举动,体现了爱国情怀,在党的领导下,文物有了好归宿。潘素也跟着捐画,支持丈夫决定。俩人晚年粗茶淡饭,潘素画艺精进,张大千夸她神韵高古,直逼唐人。她画作还作为国礼赠外宾,名声传开。张伯驹1982年走,潘素1989年随他而去,留下一段佳话。 这故事说到底,是旧中国乱世里一对普通夫妻的坚守。张伯驹从纨绔子弟变成收藏大家,潘素从青楼女子变成画家,都靠着对艺术的痴迷和对国家的忠诚。搁今天看,俩人那股子劲头,接地气得很,不摆架子,就实打实干事儿。国家强了,文物才稳当,这也是我们这代人该记取的。 MCN双量进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