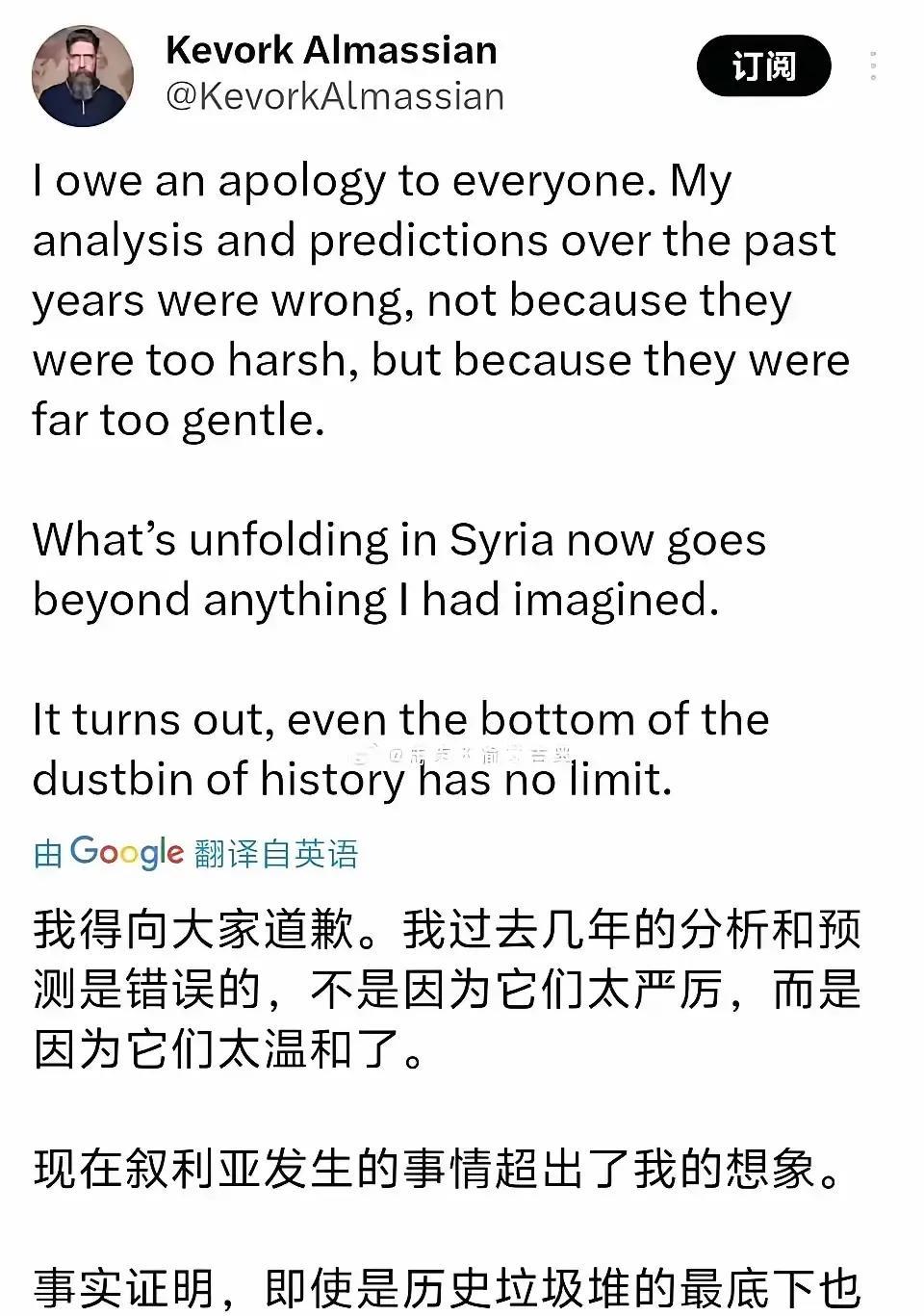叙利亚人后悔了,但没有后悔药了,国家可能就要这么被别人瓜分了!这个穆斯林长老在社交媒体上认错,他说他怀念阿萨德了。 当初他觉得阿萨德搞世俗化,是异教徒,就是一个垃圾,现在才知道与恐怖分子朱拉尼、种族灭绝以色列、奥斯曼大梦土耳其相比,阿萨德简直是天大的好人! 然而,一切都晚了,没人会再为叙利亚人兜底,现在阿萨德恐怕也不会再回去了,回去等于送死,干嘛去送死呢? 长老的手机屏幕上,还存着 2010 年女儿在大马士革女子学校的毕业照。 照片里的女孩穿着蓝色校服,露出小臂,笑容里没有黑袍的束缚。如今在土耳其控制的阿夫林地区,12 岁的孙女每天要裹着及地的黑袍去 HTS 开设的 “宗教学校”。 课本里满是 “圣战” 字眼,连数学题都改成了 “一颗炸弹炸死 5 个异教徒,3 颗能炸死多少”。 长老摸着屏幕上女儿的笑脸,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 当年他正是举着 “清除世俗毒瘤” 的标语 站在抗议队伍最前面,如今却要靠偷偷变卖祖传的地毯,才能给孙女换点能看懂的旧课本。 阿勒颇的面包房早就没了炊烟。土耳其军队在城市边缘设下检查站,每袋面粉过关都要抽成三成,美其名曰 “安全管理费”。 面包师萨利姆记得,阿萨德时期,政府会给面包房补贴,5 叙镑就能买到一个热乎乎的麦饼,现在同样的钱连半块发霉的玉米饼都买不到。 上个月,他试图绕过检查站运面粉,被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分子打断了腿,躺在难民营的帐篷里,听着外面 HTS 的巡逻车播放 “禁止售卖酒精和烟草” 的广播... 而以前,他的面包房隔壁就是卖啤酒的杂货店,没人会因为喝瓶酒被拖到广场上鞭打。 戈兰高地的橄榄树又到了挂果的季节,只是再也没人敢去采摘。以色列的推土机推倒了成片的橄榄林,在上面建起新的定居点,铁丝网拉到了村庄边缘。 村民哈桑的父亲曾在 1998 年获得政府颁发的 “优秀种植户” 证书,那时政府会派技术员指导嫁接,收获的橄榄能卖到欧洲。 现在,他只能看着定居点的犹太人用他父亲种下的橄榄榨油,瓶身上印着 “以色列特产”。 去年他偷偷越过铁丝网想摘几个果子,被以色列士兵用橡皮子弹打中后背,至今阴雨天还疼得直不起腰。 德拉省的医院成了老鼠的乐园。朱拉尼的手下把手术室改成了审讯室,墙上还留着干涸的血迹。 护士法蒂玛藏在衣柜里的旧工作证上,有阿萨德时期的国徽,那时她每月能领到稳定的工资,医院里有从俄罗斯进口的抗生素。 现在,她在难民营里用生锈的剪刀给人接生,最常用的药品是草木灰,因为 HTS 禁止使用 “异教徒发明的西药”。 有次一个孕妇大出血,她想去邻镇的土耳其医院求助,却被检查站的武装分子拦下,理由是 “女人不该抛头露面”,等她第二天找到愿意帮忙的司机,孕妇已经没了气息。 大马士革的倭马亚清真寺,宣礼塔的影子被分割成好几块。一部分在政府控制区,一部分被 HTS 的狙击手占据,还有一块成了以色列无人机的监控范围。 长老还记得,阿萨德时期,不同教派的信徒能在这里一起祈祷,政府会派人维护寺内的文物,连清洁工人都能领到体面的薪水。 现在,他在视频里指着寺顶破损的穹顶:“朱拉尼说这是‘不纯的建筑’,要炸掉重建。 土耳其人想把它改成奥斯曼风格的博物馆;以色列的炮弹说不定哪天就会落下来。” 他的声音带着哭腔,“我们当初骂阿萨德限制宗教活动,现在才知道,他只是想让我们活着祈祷。” 幼发拉底河的水依旧流淌,只是河上的桥梁换了好几种旗帜。土耳其的装甲车在桥上巡逻,车身上的星月旗在风中猎猎作响。 河对岸,HTS 的黑旗插在断墙上,旗下是拿着 AK47 的蒙面武装分子;远处的河湾处,以色列的快艇偶尔会驶过,溅起的水花打湿了岸边村民晾晒的衣服。 渔民阿布杜拉坐在破旧的木船上,看着河水倒映出的混乱景象,想起阿萨德时期,政府会组织渔民清理河道。 还会给渔船发柴油补贴,那时他一天能打十几斤鱼,足够养活全家。 现在,他得向三方势力分别缴纳 “过河费”,打到的鱼还不够交费用,只能靠挖河底的淤泥充饥。 难民营的帐篷里,长老的手机还在播放着他的认错视频。 评论区里,有人骂他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有人发来了自己所在地区的惨状照片,还有人问 “阿萨德还能回来吗”。 长老没有回复,只是把手机揣进怀里,走到帐篷外。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布满弹孔的地面上。远处传来爆炸声,不知道是哪一方的炮火。 他想起阿萨德时期的夜晚,虽然偶尔会有宵禁,但至少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而不是现在这样,只有哭喊声和枪声交织在一起。 “没有后悔药了。” 长老对着空旷的营地喃喃自语,风吹起他花白的胡须,“我们亲手打碎了能遮风挡雨的屋子,现在只能在废墟里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