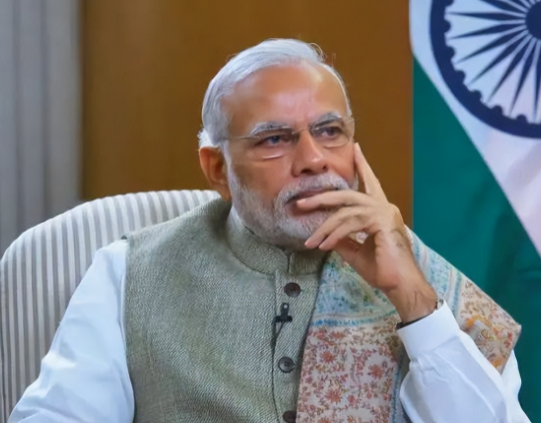1965年,空军飞行员高长吉面对越境挑衅的敌机,毅然违抗禁令将其击落。这一壮举令空军高层陷入两难境地,然而当伟人闻讯后,当即作出批示:若被条条框框束缚手脚,如何能赢得胜利? 【消息源自:《1965年东南沿海空战实录》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高长吉回忆录:我的歼击机生涯》1998年军事科学出版社;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1965年东亚空中行动报告》2001年版】 那天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汕头雷达站的荧光屏上突然跳出两个光点。李明哲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凑近屏幕确认——不是飞鸟,不是云团,是实实在在的金属反射信号。"报告!两点钟方向,高度一万二,速度九百!"他的声音在寂静的作战室里炸开,惊醒了正在打盹的赵参谋。 赵卫国一个箭步冲到雷达前,作战靴在地板上蹭出刺耳的声响。"又是'巫毒'!"他盯着那两条匀速移动的轨迹,后槽牙咬得咯咯响。这已经是本月第三次了,美军RF-101侦察机像逛自家后院似的在沿海晃悠,每次拍完照片就扬长而去。指挥部的电话直接打到塔台时,高长吉正在给新飞行员讲解如何用歼-6的机炮打提前量。 "高队长,双机紧急升空!"塔台指挥员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愤怒,"老规矩,只驱离,不首先开火。"高长吉把飞行图囊往座椅下一塞,扭头对僚机飞行员说了句:"小张,今天咱们给'客人'准备点新节目。"可谁都没想到,这场精心策划的"欢迎仪式"刚开始就出了岔子。小张的飞机刚离地就报警燃油泄漏,只能摇晃着机翼返航。 九点零八分,高长吉独自驾机爬升到八千米。耳机里传来地面引导:"敌机在你十点钟方向,距离三十公里。"他眯起眼睛望向舷窗外,碧蓝的天空干净得像刚擦过的玻璃。这很不对劲——RF-101的银灰色涂装在一万两千米高空几乎隐形。高长吉突然想起上周试飞的新战术,手指在操纵杆上轻轻敲打起来。 "汕头,请求实施'撑杆跳'。"无线电里短暂的静默后,赵参谋的声音有些发颤:"批准尝试,注意安全高度。"此刻指挥部的作战参谋们围在雷达屏幕前,看着代表高长吉的光点突然开始剧烈爬升。歼-6的设计升限是一万七千米,但手册上明明白白写着"超过一万五千米禁止剧烈机动"。 九点十五分,高度表指针颤巍巍停在了一万八千两百米。高长吉的视线开始出现黑边——这是缺氧的前兆。就在他准备下降高度时,右前方突然闪过两道金属反光。"逮到你了!"他猛地推杆俯冲,看着那架RF-101的轮廓在瞄准具里越来越大。美军飞行员显然没料到会在这个高度遭遇拦截,机翼一摆就要开溜。 接下来的三分钟像被按了快进键。高长吉第三次咬住敌机尾巴时,油量警报灯刺眼地亮了起来。"汕头,还剩多少返航油量?""最多二十五分钟。"地面回答得干脆。高长吉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拇指在导弹发射钮上摩挲——PL-2导弹的有效射程才八公里,而敌机正在十二公里外优哉游哉地巡航。 "拼了!"他猛地关闭无线电保持静默,推满油门追了上去。事后被捞起来的美军飞行员沃克在回忆录里写道:"那个中国疯子像是要把机头戳进我们的尾喷管。"在距离十公里处,高长吉突然拉起机头,趁着敌机被阳光晃眼的瞬间,两枚导弹拖着白烟扑向目标。第一枚炸断了RF-101的右水平尾翼,第二枚追着翻滚的残骸扎进了南海。 当高长吉的歼-6歪歪斜斜降落在跑道上时,地勤发现油箱里剩下的燃油还不够洗把脸。赵参谋冲过来捶着他的肩膀喊:"你小子把军委'不开第一枪'的命令当耳旁风啊?"高长吉摘下沉甸甸的飞行头盔,咧着嘴笑:"他们先开的加力燃烧室嘛。"这场持续十四分钟的空战,后来被写进各国空军教材——不仅因为创造了螺旋桨时代后首次纯导弹击落记录,更因为谁都没想到,用矮一头的歼-6居然能打下号称"不可拦截"的巫毒侦察机。 三个月后,高长吉在南京空军学院讲课,有学员问起那次著名的"撑杆跳"战术。他摸着下巴上的胡茬说:"其实哪有什么秘诀,就是算准了他们觉得我们不敢。"台下哄笑中,谁也没注意最后一排坐着几个穿便装的技术员,他们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数据——后来这些笔记成了歼-8高空截击机设计手册的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