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时任第67集团军参谋长的粟戎生(粟裕长子)率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在老山前线,他竟将训练用的航模飞机装上照相机监测老山前线,这也是我军首次将无人机照相侦察用于实战。 老山前线的丛林像密不透风的绿墙,把战场切割成无数个盲区,侦察兵背着电台钻进林子,往往几天几夜摸不到关键情报,偶尔带回的消息还可能因为视野受限出偏差。 时任第 67 集团军参谋长的粟戎生站在指挥部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标注着“敌情不明”的区域,眉头拧成了疙瘩。 这时候谁也没想到,改变僵局的会是一架不起眼的航模。 粟戎生见过美军在越南用无人机侦察的资料,那些能飞进危险地带的“铁鸟”让他动了心思。 老山这地形,人进不去的地方,机器或许能行,训练用的航模平时就是官兵们练手的玩具,他让人搬来几架,又找来民用相机拆了镜头。 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军人围着航模琢磨,怎么把相机固定稳当,怎么让飞机飞得更久,怎么确保拍出来的照片能看清敌方阵地的细节。 没现成的技术手册,就对着美军残骸的零星资料画图;设备不匹配,就用铁丝、胶带一点点凑。 折腾了半个多月,那架带着相机的航模第一次冲上老山上空时,地面上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航模飞回来的时候,胶片在暗房里冲洗出图像的瞬间,指挥部里爆发出低低的欢呼。 照片上,敌方藏在山坳里的炮兵阵地看得清清楚楚,炮管指向哪里、工事有几道掩体,连伪装网的褶皱都能辨认。 就靠这些照片,我军很快调整了火力部署,敌方部队连夜调动,等对方刚把炮架设好,我方炮弹就像长了眼睛似的砸了过去。 这架简易无人机成了战场上的“千里眼”,以前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摸到的敌情,现在飞一圈就有了答案。 粟戎生会上战场,没人觉得意外,他是粟裕大将的儿子,从小听的就是“军人不上战场算什么军人”。 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他没去机关坐办公室,揣着分配通知就去了云南前线,从基层战士干起,摸爬滚打十几年才走到指挥岗位。 老山轮战的时候,他照样跟士兵一起在猫耳洞蹲守,身上的迷彩服磨破了就补块补丁。 在他看来,粟裕的儿子这个身份,不是特权是责任,战场上子弹可不认谁是将门之后。 那架航模带来的不只是几张照片,它让部队第一次尝到“非接触侦察”的甜头,不用把人往枪口下送,照样能把敌情摸清楚。 有了准确的图像,指挥员在地图前指指点点的时候,心里就有了底,以前开会讨论半天还定不下来的部署,现在对着照片一说就明白。 更重要的是,它打开了一扇门,让大家看到技术创新能在战场上起到多大作用。 后来部队里开始有人专门研究怎么让这“空中侦察兵”更厉害,从胶片相机换成数码设备,从手动操控变成半自动化,一步步往前赶。 现在看中国无人机满天飞,从察打一体到民用航拍,好像是水到渠成的事,可当初要是没人在老山前线把航模绑上相机试那第一把,这条路说不定要绕个大弯。 粟戎生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在别人觉得“不可能”的地方找到了突破口。 他没指望一下子造出多先进的装备,先解决 “有没有” 的问题,再慢慢琢磨 “好不好”,这种从实战需求出发的创新,比任何实验室里的理论都管用。 粟裕大将当年在战场上靠灵活机动打胜仗,讲究的是“不拘一格”,粟戎生把航模改成无人机,和他的父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战场形势变了,老办法不管用,就得敢想新招,那架在老山前线嗡嗡作响的航模,飞过的不只是枪林弹雨,还有中国军人面对困境时那股子不服输的精神。 真正的创新从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往往藏在解决问题的实干里。

![YJ18C隐身亚音速巡航蛋[墨镜]注意是ZL方队,东大对隐身亚音速蛋不怎么感冒,](http://image.uczzd.cn/11662652948362677852.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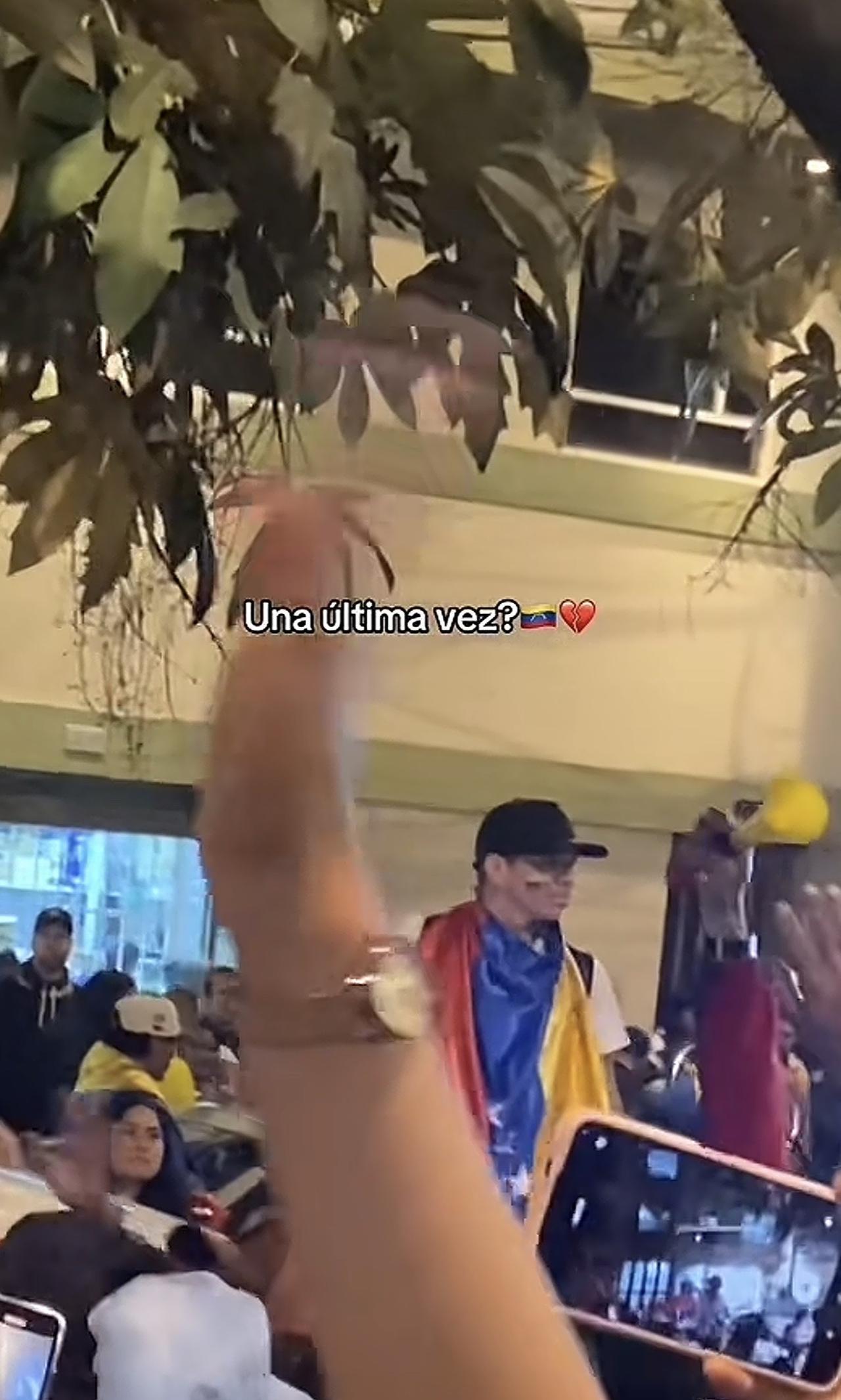

![四代坦克和99A的CG对比图[墨镜]四代坦克体积不小,去掉顶部武器站的车高相比9](http://image.uczzd.cn/15933197912130976114.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