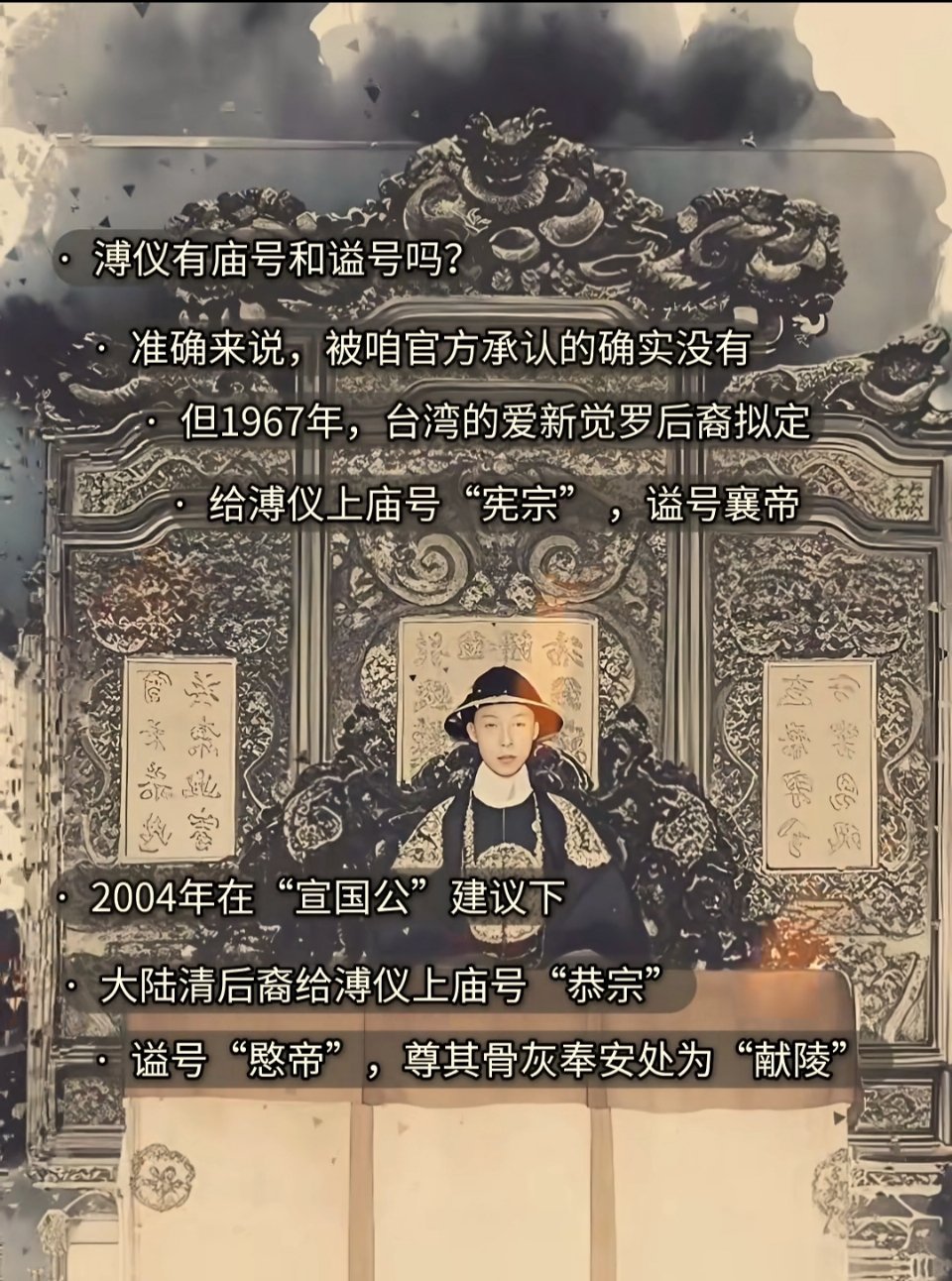孔二小姐孔德懋十分厌恶嫡母陶氏,并坚持是陶氏害死了自己的生母王氏,因此绝不愿意称她为“母亲”,只是称呼“陶氏”。根据她的说法,陶氏门第不高,父亲陶式鋆只是个大名府的知府,能进孔府当太太,完全是因为衍圣公是续弦+先纳了姨太太的缘故。
就连慈禧,对这门亲事都不太满意,因为在慈禧看来陶氏既不是名门闺秀,容貌和举止也不太入眼。陶氏后来去给慈禧磕头的时候,慈禧先问道:“这是那家的姑娘?”当知道了她娘家是房产主以后,就说:“唉!满朝文武官员,谁家姑娘不行,怎么单找这么一个?”不过因为历代衍圣公的妻子都是诰命一品夫人,出于惯例,慈禧还是封了她诰命一品夫人。
后来陶氏的丫头王宝翠被收房为姨太太后,每当宝翠临产,陶氏就盘腿坐在她自己房内的床上等着,孩子刚刚落生,立即就被抱到陶氏房中,由陶氏抚养。亲戚本家也只是向陶氏道喜,好像她才是生了孩子的那个,反而是刚生产完的宝翠无人问津,很多本家太太甚至从来没见过她。孩子们只能管陶氏叫“娘”,按照进门顺序管大姨太太丰氏叫“大妈”,管亲生母亲叫“二妈”,而宝翠也要管孩子们叫“少爷”“小姐”。
使女的故事?感觉嫡庶神教可以去他家取材~
陶氏一首把持了孔府的事务,任命自己从北京娘家带来的杜炳勋师爷为账房总管,甚至让三位小姐少爷认杜师爷为干爹。然而杜师爷把持账房后,贪污腐败的了不少,被陶氏发现,就把他赶走了。临走前杜师爷卷走了大量的钱,但半路被陶氏伏击,所有东西被没收。可见陶氏确实有手段有心计。
除了杜师爷,陶氏还带了很多人来,从师爷到裱糊匠都有。陶氏的几个兄弟也经常来,后来干脆住下帮忙管家。陶氏则每天上午坐在前上房书案前听“回事”,和皇帝一样批各种呈文。即便是孔德成诞生后,孔府的官员、执事、小甲的呈文里,抬头都要写“老太太、公爷恩准”。陶氏甚至打破了惯例,以妇女之身主持修家谱,只是后来突然去世,没修成。
衍圣公孔令贻去世后,陶氏立刻指示弟弟陶勋控制孔府事务,第一时间将孔府层层警戒。陶勋给陶氏的密信中说“府事弟已连日内外密布”,陶氏有什么吩咐“密示于弟”,“弟必竭死力以效劳”。孔令贻去世前,遗嘱命要嫡堂兄孔令誉(式如)暂时料理府事,但在孔式如去京料理棺柩回乡事时,陶勋给陶氏密信说:“不知式如……藏有私心否?务乞五姊时多留心,勿受其欺。”还说:“弟已……从中暗探消息。”
由于王宝翠已经怀孕,而此次分娩直接关系到陶氏能否继续独揽孔府大权,因此陶勋指派专人看管宝翠,防止发生意外。陶勋又在内宅后院单设小厨房,派去他的两名心腹专为宝翠做饭,三令五申明确规定除这两人送去的饭菜外,任何食物不得入口。陶勋还时时提防着有人花钱买通厨房下毒,可见当时孔府内部的暗流涌动。
根据孔德懋的说法,宝翠生下孔德成后,被陶氏伙同一位名叫孔心泉的医生毒死。根据女仆回忆,宝翠不怕死,因为活着也没有好日子,只是想死前见见自己的孩子,但是这个心愿也没有达成。所有人对于宝翠的死都有疑虑,只是无法宣之于口。
宝翠死后,陶氏放出话说,她是产后受风死去的,说她是在分娩后,由产房移到里间屋的床上时受的风。宝翠去世当晚,陶氏让几个当差的在夜里不声不响地将把棺材从内宅后门抬出去,在孔林的一个角落草草掩埋,连墓碑也没有。
但宝翠死了十多天后,一位听差突然跑到济南,击鼓鸣冤要求省政府来查明死因。更神奇的是,在那个年代,省政府居然答应派人来孔府调查,这可能是“五四”运动后,社会上掀起“打倒孔家店”的热潮,反孔派官员想利用此案扩大自己阵营的影响。
省里成立了“王氏死因案”专案组,派了两个办事人员来。陶氏大吃一惊,吓得瘫在床上浑身发抖。最后她将医生孔心泉推出去当了替死鬼。孔心泉没有办法,吃鸦片自尽了。孔心泉死后,陶氏还假惺惺地去他家吊丧,孔心泉老婆说了些很难听的话,陶氏这位“一品夫人”在众多客人面前狼狈而去。
孔心泉服毒自尽后,省政府以“一命抵一命”匆匆宣告结案。这里面,陶氏用了些什么手段?花了多少活动费?以及她那在济南当官的弟弟又怎样为她出力的?就不得而知了。
王氏死后,陶氏为了表现自己贤明,一力抬举没有生育的丰氏在各种活动上露面。但她只是当丰氏像丫鬟一样,指示她干这个拿那个,经常有人误会丰氏是新来的丫鬟。丰氏也就这样默默的忍受到去世。
孔德懋十三岁那年,陶氏病故,准备和丈夫合葬。此时终于有些好心的本家提出:
王氏为孔府生育了两女一子,尤其是生育了第七十七代公爷,为孔府立了大功,应当三人合葬。
虽然姨太太和衍圣公夫妇合葬,这是在孔府历代都没有过的事情,但十一岁的孔德成听到生母终于可以享受死后哀荣,激动的热泪盈眶,立刻向本家们跪下磕头,三人合葬的事情就算是定下来了。
直到此时,这位可怜的农家姑娘,她的存在才终于在死后十一年被昭告天下。她的儿女们也终于可以不必担心任何迫害,堂堂正正的承认她为自己的生身母亲。
谁能想得到,衍圣公府的姨太太,下一代“圣人”的生母,竟会过成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