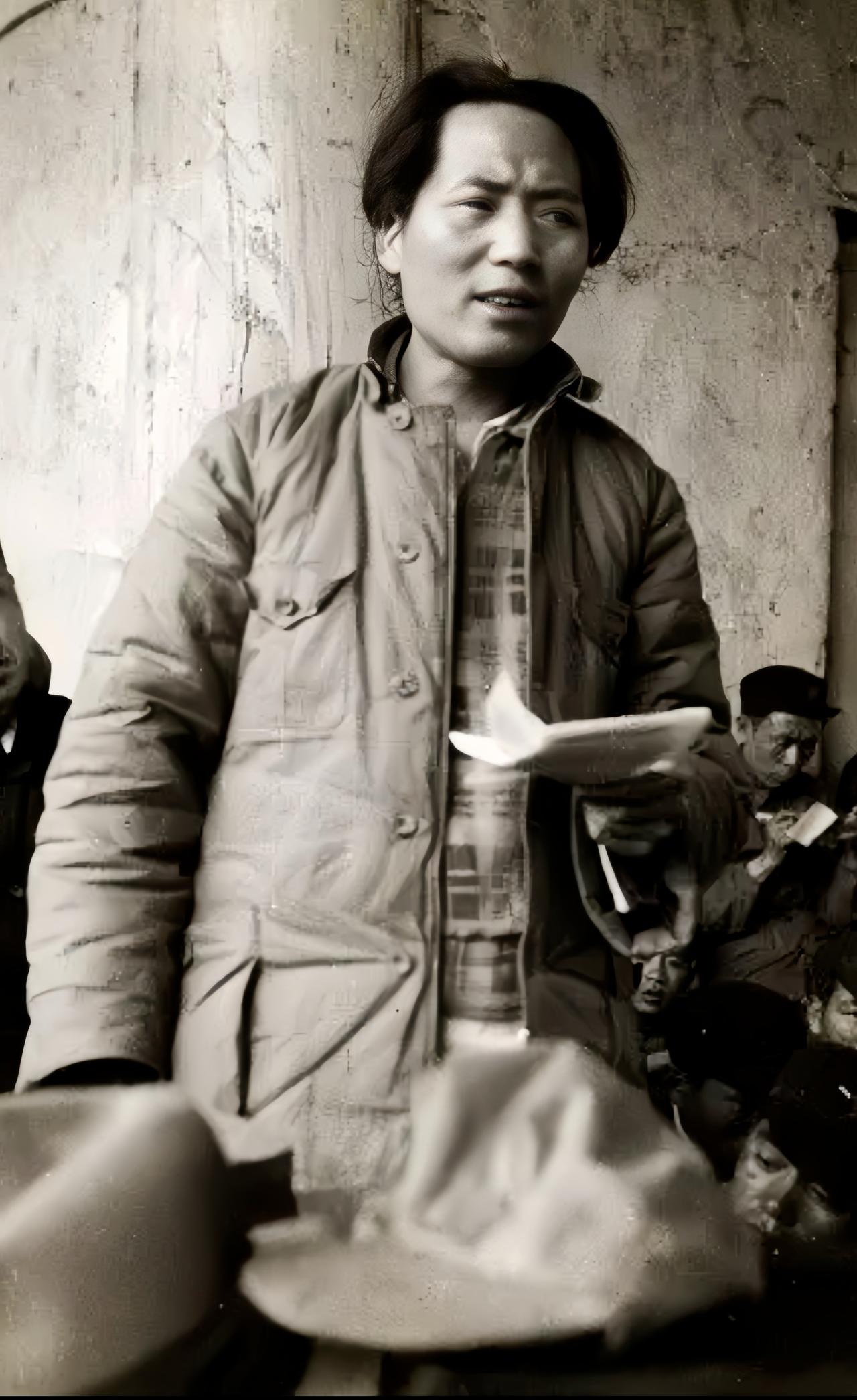“什么原因让你喜欢上了毛泽东?”一位刚刚退休不久的60后的答案,引发了我的思考。这位60后人称全叔,以前在机关单位上班,因为有点职权,所以在位时常常是门庭若市,走到哪里都前呼后拥。可退休后,“所有人好像突然就不认识自己了”。 深秋的午后,全叔正给社区里的孩子们讲述古田会议的历史。他布满皱纹的手掌抚过泛黄的书页,金桂的甜香从窗外飘进来,与书页间的油墨气息交融。 这样的场景若让两年前的他看见,定会觉得不可思议——那时他刚退休,整日对着空荡的客厅发呆,连泡茶时都会习惯性多拿几个茶杯。 那是2021年的冬天,供暖管道在楼道里嗡嗡作响。全叔蜷缩在褪色的皮沙发里,望着手机里再也不会亮起的微信头像发呆。 二十年的机关生涯戛然而止,曾经络绎不绝的访客仿佛被寒风卷走的落叶,连门口值班室的老张都不再殷勤地帮他提菜篮。 某天清晨,他在储物间翻找旧报纸时,一本深蓝色封皮的《毛泽东年谱》从箱底滑落,砸在积灰的水泥地上发出闷响。 书页间夹着的借书卡显示,这本1978年出版的传记,是他在县委党校进修时借阅的。 泛黄的纸张上,青年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场景跃然眼前:隆冬的北平,八人合住的通铺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翻身都要知会邻人。 但二十出头的毛润之仍坚持清晨五点起床,借着煤油灯抄录《伦理学原理》的德文注释,字迹工整得如同印刷体。 "这和我当年在机关值班室通宵写材料倒有几分相似。"全叔摩挲着书页喃喃自语。 窗外的梧桐叶沙沙作响,他忽然想起1974年插队时,生产队长总爱讲苏区往事:1933年的瑞金,被解除军权的毛泽东搬进云石山古寺,在青灯黄卷间研读《反杜林论》。 寺前石阶上,总能看到他披着旧棉袍与老农谈天的身影,膝盖上搁着写满批注的笔记本。 书柜里的台钟敲响三下,惊醒了沉浸在往事中的老人。他戴上老花镜,仔细辨认年谱里用红笔勾画的段落:1934年秋,毛泽东带着三大箱书籍踏上长征路。 湘江血战后,担架上的他仍在研读《国家与革命》,铅笔批注挤满了书页的每个空隙。这些细节让全叔想起自己初到县委报到时,挎包里总装着《矛盾论》单行本,下乡调研时在田埂上做笔记的样子。 当读到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要对此发表点意见",全叔突然笑出了声。 这让他想起1983年评先进工作者时,自己坚持要把荣誉让给同事的老黄历。窗外的夕阳给书桌镀上金边,老人惊觉已连续阅读了五个小时——这是退休后从未有过的专注时刻。 如今的全叔成了社区党史宣讲员,他总爱指着墙上的《沁园春·雪》手迹说:"看这字里行间的气魄,是陕北窑洞的油灯熬出来的。"偶尔有老同事在菜场遇见他拎着芹菜豆腐,打趣他"怎么不坐专车了",他会笑着扬扬手里的《毛泽东选集》:"主席说过,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嘛。" 暮色渐浓,全叔合上年谱,给盆栽里的君子兰浇了遍水。叶片上的水珠在夕阳下闪烁,恍若当年他在韶山冲看到的晨露——那个改变中国命运的农家少年,正是带着这般澄澈的目光,在逆境中走出了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