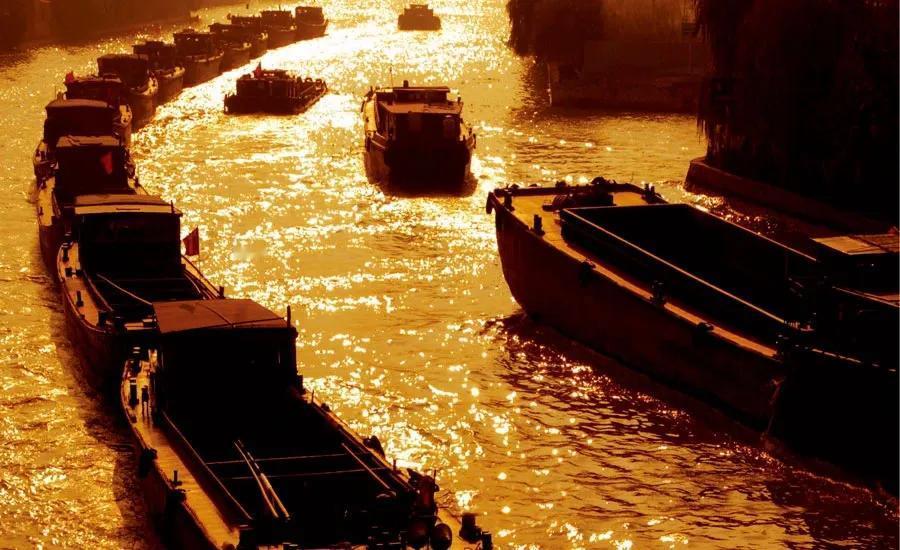1956年解放军在云南原始森林深处,发现了一群原始人,他们衣不蔽体、靠着捕猎和捡野果为生,如今他们过得怎样? 在云南哀牢山那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里,隐藏着一群与世隔绝的苦聪人。他们是古老氐羌人的后代,早在千年之前就背井离乡,只为逃避灾祸。 一代又一代,苦聪人在这片深山老林里过着原始而艰苦的生活。他们没有房子,就在树丛下搭个窝棚;没有锅碗,就用竹筒盛水煮食;没有衣服,就披兽皮蔽体。 生存,对于苦聪人来说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挣扎。每天,男人们拿起土制的弓箭上山打猎,女人们在林间采摘野果。但大山里食物有限,一顿饱餐都成了奢望。 苦聪人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与现代社会渐行渐远。他们没有农业,不懂耕种;没有文字,无法记录历史。外面的世界在飞速发展,而苦聪人的时间,似乎永远停留在原始时代。 1956年,一支解放军小分队执行任务时,偶然在哀牢山深处发现了这群原始居民。当时的苦聪人衣不蔽体,蓬头垢面,许多成年人连用火都不会。这一惊世发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人们很难想象,在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的新中国,竟然还存在着如此贫穷落后的"原始部落"。千百年来,苦聪人在大山深处艰难求生,他们不是被遗忘,而是从未被发现。直到这一天,他们才终于与新生的共和国"相遇"。 受困于闭塞落后环境的苦聪人虽然贫穷,但他们是勤劳善良的。政府和解放军决定伸出援手,帮助苦聪人改变命运,告别原始生活,奔向美好新生活。这注定是一场世纪跨越,需要付出巨大努力。 政府决定帮扶苦聪人,第一步就是派出一支民族工作队,深入哀牢山与苦聪人接触。要改变一个群体的生活方式谈何容易,工作队首先就是要取得苦聪人的信任。 工作队带着各种日用品和食物顺着蜿蜒的山路找到苦聪人。起初,苦聪人躲躲闪闪,用木棍石块驱赶工作队,生怕这些"外人"伤害他们。工作队就在山脚下点起篝火,一边煮饭做菜,一边唱歌跳舞。 苦聪人渐渐放下戒心,开始接受工作队的食物和衣物。双方在互动中建立了信任,苦聪人听说山外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竟然动了搬迁的念头。工作队抓住机会,游说苦聪人离开大山,到政府建的新村落里定居。 说服苦聪人"出山"花了整整6个月时间。苦聪人终于背着简陋的行囊告别故土,迈向新生活。政府为他们修建了漂亮的砖瓦房,发放崭新的锅碗瓢盆,送来猪羊鸡鸭。苦聪人睁大眼睛,没想到生活还能这般舒适。 新生活固然美好,但也带来诸多挑战。苦聪人不懂汉语,对农耕种植一窍不通,连日常生活用具都不会使用。为此,政府抽调大量干部常驻苦聪村,手把手教他们生活技能。 干部们教苦聪人开荒种地,引进水稻玉米等高产作物。村里建起了新学校,孩子们头一次坐进了教室。成年人学习识字算数,学习基本法律和卫生保健知识。 在干部的悉心帮助下,苦聪人一点一点适应着现代生活。他们学会用牛耕田,学会保存粮食,不再为温饱发愁。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起了新房子,一砖一瓦筑起了新生活。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政府的扶持还在继续。新修的公路连通了苦聪村与外界,村里通了水通了电。各种农业科技培训,让苦聪人掌握了脱贫致富的本领。 年复一年,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昔日的原始部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苦聪人从深山搬到新村,从茹毛饮血到吃穿不愁,从文盲到识字断字。他们就这样一步步告别贫穷,迈入现代文明。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苦聪"野人"已经今非昔比。现在,全国苦聪人口已达3万,分布在金平、绿春、镇沅等地。他们从原始森林走进社会,彻底告别了刀耕火种的生活。 2007年,随着最后一个苦聪村通电,所有村寨都用上了电灯电器。砖石木瓦房取代了简陋的草棚,人畜分离的新居让苦聪人逐渐远离了疾病的困扰。孩子们不再蓬头赤脚,而是穿上鞋子背上书包,走进学校接受教育。 昔日的苦聪人如今都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公民。他们不再是"无名氏",而是被正式归入拉祜族。领了结婚证,办了身份证,苦聪人终于在法律和制度上获得了平等的地位。 勤劳的苦聪人学会了种植水稻,发展畜牧,还开始尝试经商贸易。收入一年比一年高,脱贫致富奔小康。村里办起了幼儿园、卫生室,建起了文化中心,苦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多彩。 2020年,作为拉祜族一分子的苦聪人也迎来了全面小康。他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用上了洗衣机电冰箱。年轻人开上摩托车,用上智能手机,过上了与时代接轨的新生活。土里刨食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美好生活正在苦聪村绽放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