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曾国藩给朋友写信,第一次提起了赵烈文这个人,赞扬他:英迈有识。”曾国藩幕府人才济济,赵烈文靠什么频频在曾国藩这里“出圈”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准确预判了大清的时局和结局,其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曾国藩的高度认可。
此后的数年里,赵烈文深度参与了曾国藩筹划军务、奏折和日常事务处理工作,亲眼目睹了晚清诸多重大历史事件。
同治六年,是曾国藩一生之中少有的清闲的一段时间,因此处理完日常事务后,他最喜欢和他的秘书长赵烈文谈话,内容虽然广泛,却都是深度的着眼未来长远大局的话题,谈话甚至上升到自道光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上来。从而引发了对于周边各国未来全球化走势。在此之前,我们很有必要简要介绍一下赵烈文基本简历。

赵烈文墓志铭
赵烈文,字惠甫,江苏阳湖人。其父赵仁基,道光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赵烈文自幼扎实地系统地学习了传统教育,但此后三次试均名落孙山,于是绝意仕途,专心钻研务实之学。
大约在1856年被其姐夫周藤虎推荐给曾国藩做幕僚。1861年12月,由曾国藩专折向清廷请示奏调赴军营,称其“博览群书,留心时事,可堪造就。”从此他成了曾国藩研究关于大清内外的问题首席幕僚,赵烈文也向曾国藩提供了有关大清四个最为重要的预测。
第一个预测:准确预测未来将要实现全球一体化。
咸丰十一年,赵烈文向曾国藩递交了一份长篇谏言,这是在决战太平军的关键时刻,赵烈文却抛出了与作战无关的言论,即太平军不是最大威胁,平定时间指日可待,清朝真正的威胁会在西方。赵烈文写道:“外国夷人,国家治理,民力富强。人人奋勉,好胜心强而以不如别人为耻,这些西方人对中国的政务民情,乡土风俗,处处图谋,考虑事情唯恐不明确,观察事情唯恐不细微,搜集我们的文化经典,翻译传播,兢兢业业,从未有间断过。”
赵烈文不无担忧地说:“他们的志向不在小,国家的祸患,再没有比这个更危险的了。”接着赵烈文又说“大清之所以如此衰弱,主要原因就是崇尚虚文,使用无用的繁琐苛刻礼仪,而外国方面务求专精简一,讲究实用。未来天下大势要走向“开通六合”。这个“六合”就是孔夫子首先创造的“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六合”,也就是整个物质世界整个空间。按照赵烈文预测,就是日后东方和西方会实现全部联通,用如今的话就是“全球一体化”概念,这在当时绝对是前无古人的提法。
第二个准确预测科举要被废止。
曾国藩曾多次称赞他“博览群书” “洞达时务”。也就是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前瞻。早在1860年,他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的百年变迁后,认为八股的“变化升降”之道已经穷尽,并大胆预测:“后来取士之方,恐将易辙矣。”果然,1906年清廷下诏准停止科举,兴办学堂。

废除科举
第三个准确预测日本将成大清最大威胁。
赵烈文对时人所著的《日本外史》,粗略了解日本的历史和现状后,颇感慨日本近年来的变化说:“西方国家与之通商,炮火之精,舟楫之利,未来会成大清最可怕的祸患。”此时,日本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才刚刚开始改革,而大部分清廷官员对日本的认识还停留在“那么小的地方,不足为患”。直到30年多后,黄海上的隆隆舰炮声轰碎了他们的迷梦。
对于甲午战败和此后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李鸿章均参与其中,虽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称赞其“大清帝国中的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其“东方俾斯麦”,慈禧赞扬他“再造玄黄之人”,甚至后世学者如梁启超以高度同情基调给予历史地位,但是同时代的赵烈文认为李鸿章治下的大清军队走向全面滑坡有着清醒客观认识,对最终的所有战败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在光绪元年的时候赵烈文与军务之人闲谈说起李鸿章治下的军队呈现出战力弱化,兵士被剥削的问题:“统领营官朘削日甚,食米、旗械、号衣之外,下至包头、裹腿均制办发给,而扣应食之饷,每人月不得一金,士心嗟怨,逃者纷纷。”而李鸿章“自军务稍息,合肥公专务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而前后左右无一骨鲠之士,佞谀者进,朴勤者退,凡不急之务,如兴造土木、捐创善堂及官幕、游客或赡家或归榇,或引见或刻书,均勒令营中貲助。甚者嬉游宴饮,挟妓娶妾,无不于焉取之。”最后军队风气到了争夺军中职级,大肆买官卖官,而“办公薪水又仅足日用,不得不设法渔猎,将习巧宦,而士有离心。最后赵烈文感叹说:当此海江多事,隐忧甫切,奈之何哉!奈之何哉!《能静居日记》
在此,我也要说句公道话,李鸿章没少娶小妾,赵烈文辞职之后也没少娶,这种双标观点,也要和读者说一下,如果调换位置,我想赵烈文也未必比李鸿章操守更好。

中日甲午战争
第四个预测,大清不出五十年就要灭亡。
基于超前意识和独特眼光,赵烈文成为准确预见清朝崩溃的第一人。而且这是在赵烈文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闲谈对曾国藩抛出的预言。
此时曾国藩已经发现了京师有些现象不太对,他听说京师气象不太好,“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赵烈文想都没想就说:“大清治理已经二百多年,许多事情均已败坏,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我的判断,以后的大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恐怕不出五十年就会发生。”这种预测到时间之准和灭亡形式都说出来,确实是石破惊天之语。果然在此后的四十五年大清灭亡,并分崩离析被军阀割据。

清朝退位诏书
曾国藩听后非常震惊问:“能南迁吗”赵烈文的果断回答:“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清政府已不可能像东晋、南宋那样南迁偏安一隅。曾国藩听后绝望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
几天后,曾国藩依旧不愿相信赵烈文的论断,因为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他对于大清是有重大贡献的,特意找他再次引申这个话题,希望赵烈文收回这个观点。曾国藩说,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一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千古。又如大乱之后而议征减,饷竭之日而免报销,数者皆非亡国举动,足下以为何如?赵烈文还是坚持自己见解,并阐释说:“三代以后,论强弱,不论仁暴;论形势,不论德泽。”他还列举了诸葛亮辅佐后主殚心竭虑,鞠躬尽瘁依旧不能避免覆亡,南宋之后,求治颇切,而终究不是金人对手。听了这话,曾国藩还是不甘心,又提出了说出了新的想法,希望赵烈文能重视当朝的恭亲王的“聪明”和慈禧太后的“威断”,以此认为他们能够避免“抽心一烂”和“根本颠仆”的结局。

恭亲王照片
而赵则坚持己说:我曾见过恭亲王的小照片,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所谓不在行迹在实事,慈禧威断终究是外表,并不是真的能力。当时,曾国藩觉得清王朝还有一线生机。但两年后,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更加接近清廷的权力人物,才知国家颓败远超想象,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而他却也看到了:“京师水泉皆枯,御河断流,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
在曾国藩第一次看到慈禧后,认同了赵烈文的判断,回来对他说:“两宫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就是说,两宫太后没有什么才能,说话都没有太高水准,皇上太小,没法判断。我们可以想象被清王朝拯救的曾国藩是何等的失落。因为这关乎到他此前所有的努力终究是大梦一场。
此后的大清帝国确实早已江河日下,所谓“同治中兴”无非是并不耀眼的回光返照。对于曾国藩的人生后期他内心是相当孤独的,他自己感慨:“苦无同志之士,自文忠与江忠烈殁。而同事者鲜能一心。”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等门生故旧大多离他远去,巨大的孤独感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仔细算来通过他推荐重用提拔到巡抚位置的已经有几十位,更遑论一生用人数量。虽然以知人、用人为世称道,被曾国藩提拔的左宗棠也是骂了他半辈子,最后还是承认曾国藩确实有“知人之明,”,可是最终的结局在曾国藩看来还不是“苦无同志”、“鲜能一心”。看来他吸引人才的知人之明“啖之以厚利”只是互相利用罢了。
一系列的精神上的打击让晚年的曾国藩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
在日记书信中时常也会出现“寸心焦灼,了无生趣”也是这年,他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棺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入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杳无信息,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以为苦恼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身事外,亦唯有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而已。”
虽然为大清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曾国藩本质上来说做官并不成功,终其一生也未能进入大清决策层,只是短暂担任过地方督抚权位最大的直隶总督而已,反观他的学生李鸿章当了二十五年直隶总督后又兼任北洋大臣,掌管大清外交军事、经济大权,非曾国藩所能比肩。世人多言做官必学曾国藩,鄙人却以为还是学李鸿章更为见效。

曾国藩唯一照片
同治十一年,对于赵烈文来说无异于是最悲痛的日子,这天他得知恩师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在日记这样写到“惊悉涤师于二月初四日在江都官署薨逝之信,五内崩摧,顷刻迷闷,奋力一号,始能出声。”在给曾纪泽的信中曾这样深情地回忆与涤师最后分别的场景“忆前年送行,师尊于车马纵横之中,送烈至门,坚辞不可,怆然而别。情景犹在目前。每一念及,心如糜割。”曾国藩去世不久,对赵烈文从政的热情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不久他就要辞职,于向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打报告,李鸿章当时没同意,赵烈文打算第二天再提出。就在第二天发生了一件让赵烈文更震荡灰心的事情。同治皇帝因患天花去世,赵烈文的内心想法是“疏远小臣,无涕可挥,惟觉心中震荡不宁而已。”几天后赵烈文终于获准辞职,飘然回乡。但是他的观点却成了那个时代站的最高,走的最远的觉醒者。在浩浩荡荡的历史转折处留下清晰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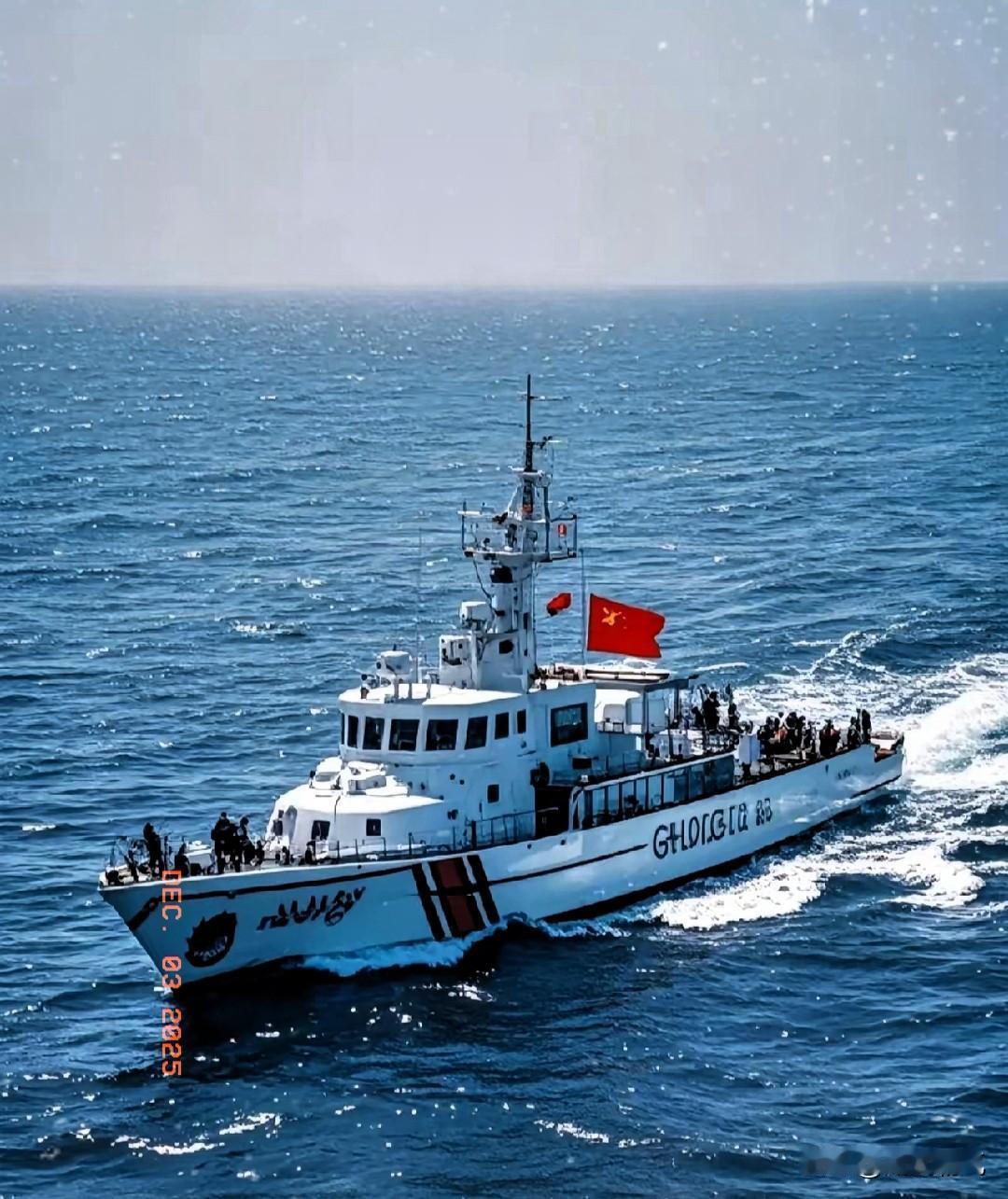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