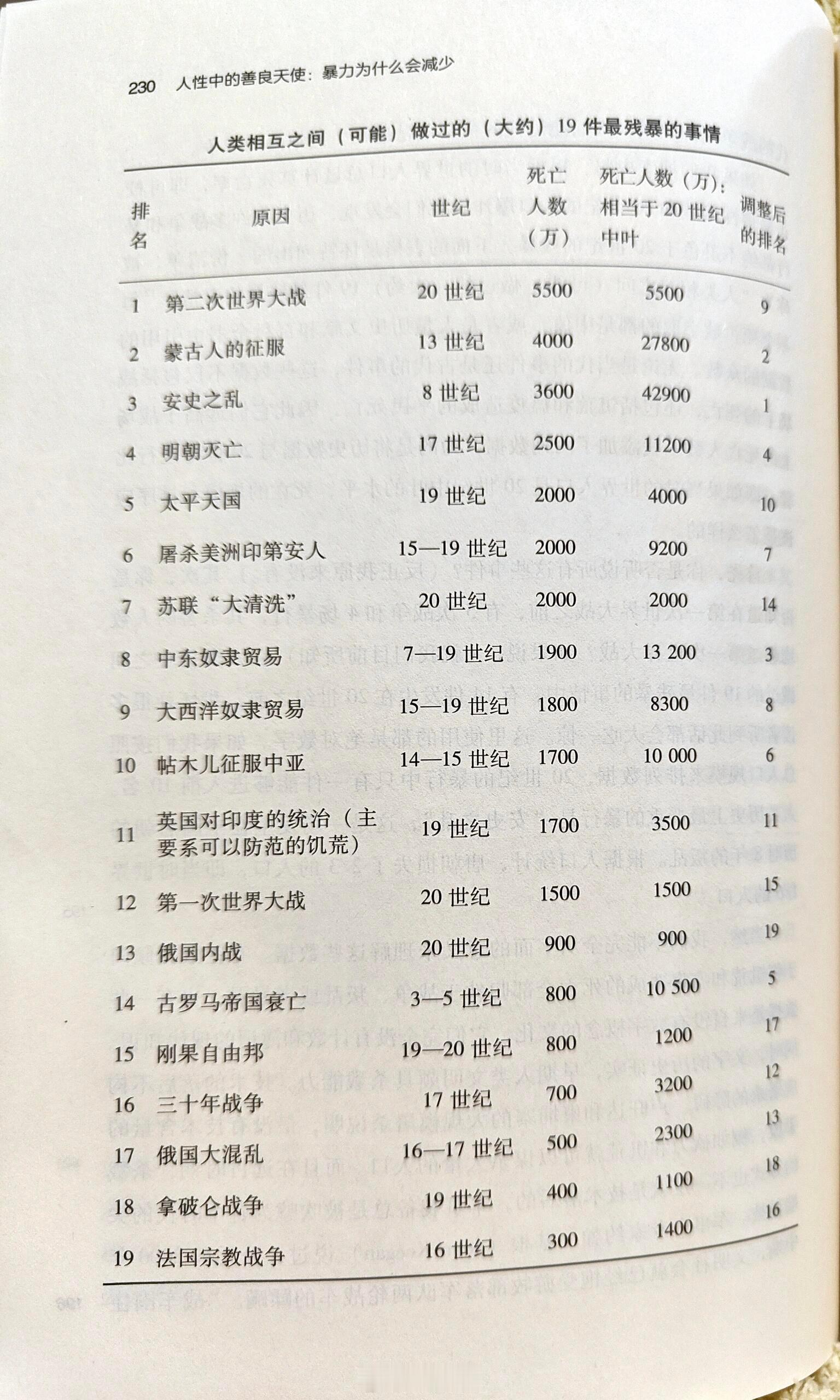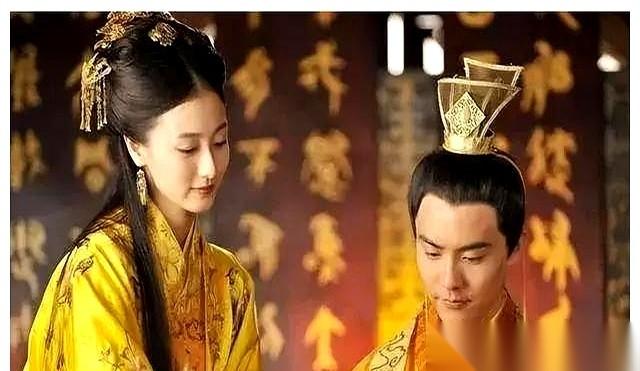为什么封建社会三五任皇帝之后,政权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李世民在《帝范》中谆谆告诫太子“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时,他或许已经预见到权力对人性的侵蚀力量;当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慨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时,他已然触及了中国历史中那个令人困惑的循环——为何那些曾经励精图治的王朝,总会在三五任皇帝后走向衰败的宿命?
这一历史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个别皇帝的道德缺陷或能力不足,而是源于一个更为深刻的结构性问题: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对人性的系统性腐蚀。
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犹如一种慢性毒药,它悄然改变着掌权者的认知结构、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最终导致整个统治系统的功能紊乱和崩溃。

汉武帝
一、权力的认知扭曲:从“兼听则明”到“独断专行”绝对权力的首要毒性在于它对统治者认知能力的侵蚀。
新王朝的开创者通常保持着相对清醒的认知能力,因为他们经历过创业的艰难,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
汉高祖刘邦出身平民,明太祖朱元璋起自布衣,他们了解民间疾苦,懂得集思广益的重要性。
这种基于经验的认知谦逊,是他们能够夺取天下并实现初期治理的重要保障。
然而,随着政权稳固,深宫高墙将皇帝与真实世界隔离开来。
汉武帝初登基时尚能广开言路,开创了“冠于百王”的盛世,但晚年却因长期独断专行,导致了巫蛊之祸,连自己的太子都不能幸免。
权力创造的认知茧房逐渐形成,皇帝被宦官、外戚、权臣所包围,他们各怀目的,精心筛选着流向皇帝的信息。
唐玄宗在位前期能够虚心纳谏,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开创开元盛世;但在位日久,逐渐被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佞包围,闭塞言路,终致安史之乱爆发。
这种认知扭曲的极致表现,是皇帝开始混淆“个人意志”与“客观规律”。
隋炀帝杨广执意三征高句丽、开凿大运河,不顾民力衰竭,正是因为在他的认知中,自己的欲望已然成为国家意志。
当权力达到顶峰,现实检验能力便会急剧下降,任何违背皇帝意愿的信息都会被自动过滤或否定。
这种认知机制的畸变,使得王朝中后期的统治者往往无法做出符合实际的决策,最终导致政权危机。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认知扭曲还具有代际强化效应。
开国皇帝至少还有民间生活的真实经验,而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继任者,从一出生就被权力的幻觉所包围。
他们从未接触过真实的民间生活,无从了解权力的边界和局限。
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著名疑问,正是这种认知扭曲的生动体现。
当他得知百姓因饥荒而饿死时,基于自身的生活经验提出了这一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解决方案,这并非单纯的愚蠢,而是长期与真实世界隔绝导致的认知畸变。

刘邦
二、权力与责任的失衡:从“忧患意识”到“权力幻觉”健康的政治系统需要权力与责任的平衡,但绝对皇权却系统地破坏这种平衡。
开国君主通常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们清楚自己的权力并非天授,而是在血与火的斗争中获得的。
这种创业经历使他们明白,权力伴随着责任,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有效治理的基础上。
但随着世代更替,继任的皇子皇孙们逐渐失去了这种忧患意识。
他们生于安乐,从未经历过祖父辈的艰难困苦,权力的获取对他们而言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非需要努力争取并小心维护的责任。
宋徽宗赵佶艺术天赋极高,却将国家大事视为儿戏,最终导致靖康之耻,正是权力与责任严重失衡的典型案例。
这种失衡催生了多种权力幻觉:
其一为“资源无限幻觉”。
皇帝逐渐相信国家资源取之不尽,可以任意挥霍。
隋炀帝为满足个人虚荣,命令将全国树木用丝绸包裹,以向外国使节展示富强。
明神宗为修建陵墓,耗费相当于全国两年财政收入的巨额资金。
他们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些资源来自民脂民膏,终有枯竭之日。
其二为“权力永恒幻觉”。
统治者开始相信自己的权力地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不会因统治失当而动摇。
这种幻觉使得他们忽视民意,践踏传统,破坏规则。
北齐后主高纬在国势危如累卵之际,仍大肆挥霍,甚至让宠妃冯小怜“玉体横陈”以供观赏,还毫不在意地说:“只要朕快乐一天就够了,何必考虑明天?”这种末日狂欢式的心态,正是权力永恒幻觉破灭前的最后疯狂。
其三为“个人神圣幻觉”。
皇帝逐渐相信自己是不同于常人的神圣存在,普通的道德规范和生理限制对自己不适用。
秦始皇寻求长生不老药,明世宗长期炼丹修道,雍正皇帝沉迷于丹药,这些都是权力神圣化的极端表现。
当统治者开始相信自己超越常人之时,也正是他失去常人情感和理智之日。

隋炀帝
三、欲望的合法化与制度化:从“节制欲望”到“放纵系统”绝对权力的另一重毒性,在于它将统治者的个人欲望合法化、制度化,甚至神圣化。
历代王朝都建立了一整套服务于皇帝个人欲望的庞大系统,从宫廷供应到地方进贡,从后宫充盈到修建离宫,这套系统将皇帝的私欲转化为国家事务,耗费大量社会资源。
唐玄宗在位后期,为满足杨贵妃喜食荔枝的爱好,建立了专门的驿传系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这看似浪漫的故事背后,是一整套为满足个人口腹之欲而建立的制度化浪费。
同样,宋徽宗为修建艮岳园林,命人从全国各地搜集奇花异石,通过漕运系统运至京师,这就是臭名昭著的“花石纲”。
这些行为不仅仅是个人奢侈,更是权力将私欲制度化的表现。
更可怕的是,这种欲望的合法化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
皇帝周围的利益集团会主动迎合甚至刺激皇帝的欲望,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
明武宗朱厚照即位初期尚有励精图治之心,但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为掌控朝政,专门修建豹房,搜罗珍玩美女,引导皇帝沉湎享乐,从而架空内阁权力。
在这种系统中,皇帝的欲望不再是个人弱点,而成为权力斗争的工具。
这种欲望制度化的极致,是形成了一套精密的“迎合机制”。
各级官员很快学会,满足皇帝的私欲比勤勉政绩更能获得提拔。
于是,本应用于治理国家的官僚系统,逐渐异化为服务皇帝个人欲望的工具。
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次沿途官员都极力逢迎,耗费巨额公款,这些支出最终都转嫁到百姓身上,加剧社会矛盾。
当欲望被制度化,节制和反思就变得异常困难。
即使有皇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改革,也往往难以对抗整个既得利益系统。
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铲除魏忠贤集团,力图革新朝政,但此时明朝的官僚系统已彻底腐化,他最终无力回天,只能在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最终覆灭。

唐玄宗
四、权力腐蚀的代际加速:从“创业艰辛”到“承平退化”历史学家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历代王朝的衰败过程往往呈现出代际加速的特征。
开国君主通常雄才大略,继任者尚能守成,但三五代之后,统治质量明显下降,直至王朝崩溃。
这种代际退化不能简单归因于基因劣化,而是权力腐蚀的代际累积效应。
第一代创业者亲身经历过夺取权力的艰辛,深知民心向背的重要性,他们通常保持简朴生活习惯和清醒头脑。
汉高祖刘邦即位后仍保持相对简朴的生活方式;明太祖朱元璋严惩贪官,亲自处理国事至深夜,这些行为源于他们对权力脆弱性的深刻认知。
第二代守成者虽未亲历创业艰难,但至少受过创业者的亲自教导,对权力的危险性尚有记忆。
汉文帝、唐高宗等尚能保持清醒,延续王朝的繁荣。
但到了第三代、第四代及以后的统治者,情况开始急剧变化。
他们生于深宫,长于妇人之手,从未接触过真实世界,对权力的认知完全来自书本和身边人的描述。
更关键的是,他们从一出生就被视为“天潢贵胄”,周围充满了阿谀奉承之辈,缺乏真实的反馈和必要的约束。
这种成长环境导致了一系列人格缺陷:极端自我中心、缺乏同理心、难以延迟满足、抗挫折能力低下。
西晋开国皇帝司马炎尚有一统三国的雄才大略,但其子晋惠帝司马衷却连基本治国能力都匮乏;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勤政爱民,而他的后代正德皇帝、天启皇帝却将国事视为儿戏,沉湎于个人爱好不能自拔。
尤为致命的是,皇室教育系统往往难以对抗权力环境的腐蚀力。
即使是最博学的太傅,面对身为储君的弟子,也难以进行严格管教。
当受教育者掌握着教育者的生杀大权,真正的教育便不可能实现。
这种结构性矛盾使得皇室子弟即使接受最好的教育,也难以形成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权力观。

明太祖
五、系统性解药与历史局限:制约机制的缺失与重构面对权力的腐蚀性,中国传统政治并非完全没有应对之策。
历代王朝都尝试建立各种机制来制约皇权,缓解其毒性。
儒家思想体系试图通过道德教化来约束皇帝行为,倡导“仁政”、“民本”理念。
史官制度通过记录皇帝言行寄望于“青史留名”的约束,言官体系赋予御史等官员批评皇帝的权力。
官僚系统依靠惯例和制度来限制皇帝任意妄为,甚至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等神秘主义思想也被用作制约皇权的工具。
然而,这些制约机制在绝对的皇权面前往往显得脆弱无力。
当皇帝决心突破这些约束时,很少有力量能够阻止。
明世宗为“大礼议”之争,杖毙十六位大臣,终如愿以偿。
万历皇帝为立储之事,二十多年不上朝,开创了皇帝怠政的恶劣先例。
在传统政治框架内,对皇权最有效的制约通常来自非常规力量——外戚、宦官、权臣甚至军事叛变。
但这些制约力量本身又常常成为新的问题源头,甚至从另一个通道直接导致王朝崩溃。
东汉的外戚与宦官交替专权,唐朝的藩镇割据,明朝的阉党乱政,无不是制约机制失衡的表现。
跳出传统框架的解决方案直到明清之际才被明确提出。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通过提高宰相权力、强化学校议政来分散皇权。
顾炎武主张“寓封建于郡县”,通过地方分权来制约中央集权。
这些思想在当时虽未实现,但确实指出了问题的关键——只有通过制度性分权,才能有效制约绝对权力。
历史周期律的背后,是权力对人性的系统性腐蚀。
那些“败家子皇帝”并非生来昏庸,而是在绝对权力的浸染下逐渐失去了作为健全个体的认知能力、情感反应和价值判断。
从唐玄宗的前明后暗,到宋徽宗的才艺误国;从万历皇帝的消极抵抗,到咸丰皇帝的犹豫不决,这些个体的悲剧背后,都说明了一个致命问题 ——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这一历史教训超越时空,对任何权力系统都具有警示意义。
权力本质上是必要的恶,它既能为社会提供秩序和公共服务,又不可避免地腐蚀掌权者的心灵。
健康的政治体制不在于幻想找到不会被腐蚀的圣人,而在于建立能够有效约束权力、防止其腐蚀作用的制度安排。
当我们今天回顾中国王朝更替的循环悲剧,不应简单地将之归咎于特定个人的道德缺陷,而应看到结构性因素的决定性作用。
唯有通过权力分立、制度约束、社会监督、透明运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抵抗权力的腐蚀性,避免重蹈“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覆辙。
杜牧的感叹犹在耳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记录过去,更在于为未来提供镜鉴。
认识权力的腐蚀性,建立防控这种腐蚀性的制度机制,或许是走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