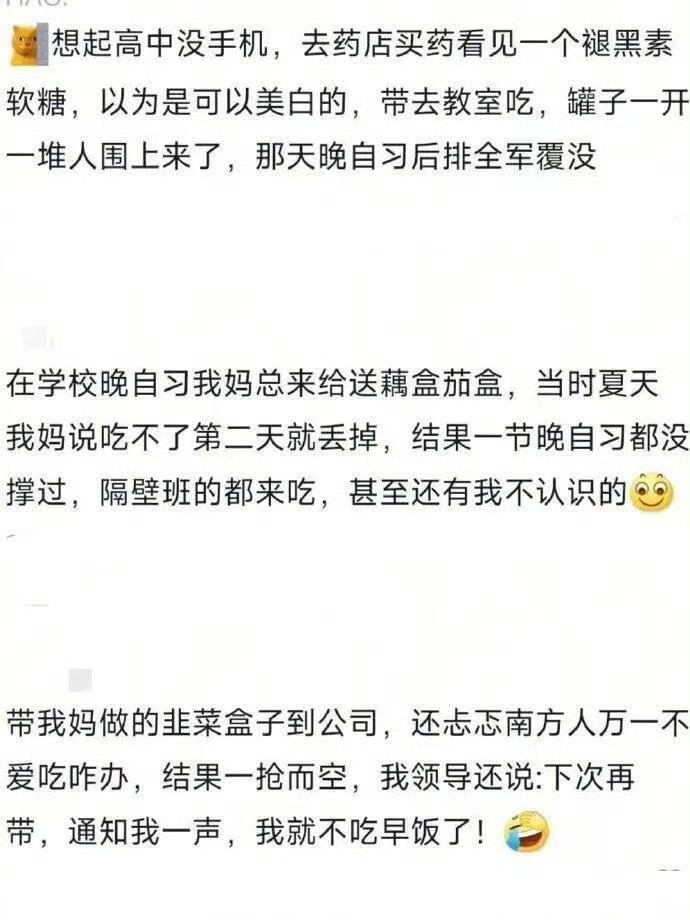白菜的根在新石器时代的土里就扎着了。
那会儿它还不叫白菜,是《诗经》里“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的葑,也就是蔓菁。
后来慢慢变,到魏晋成了“菘”,北魏《齐民要术》里写着种菘的法子,
说要“十月中,于畦中作坑”,埋着过冬,这便是最早的窖藏白菜。
它从不是什么金贵物,却跟着中国人的锅灶,熬了三千年。

北方的冬天,白菜是半个粮仓。
立冬前后,巷子里满是拉白菜的车,家家户户搬着、码着,窖里的白菜裹着干叶,像揣着过冬的命。
古谚云“百菜不如白菜”,不是说它多好吃,是它能炖能腌,能配肥肉也能就窝头。
南方人腌成酸菜,北方人渍成泡菜,一碗白菜豆腐汤,能暖透穷人家的寒夜。
如今超市里四季都有白菜,脆生生的,没了窖藏的土味。
可老辈人还记着,从前冬天掀开窖门,一股子凉湿气裹着白菜香涌出来,那是日子里最实在的盼头。
它从来没登过盛宴的主桌,却在亿万人的饭桌上,
把“活下去”的朴素,熬成了烟火里的安稳。
今天,跟诸位聊聊,中国最好吃的白菜……

河南新乡获嘉县特产,六百年前朱元璋驻扎太山天齐庙时,
士兵用清水煮出浑汤,汁浓鲜美,老朱拍腿定“贡品”,从此“浑汤大白菜”名扬天下。
这典故占半篇,可不止传说,
乾隆《获嘉县志》早载白菜为“蔬之首”,北纬35度蒙金土、黄河水哺育,
让大白菜结球紧实如叠抱,煮时自然出浑汤,
钙含量比普通白菜高,咬着脆生生,甜津津,像啃了口冬日暖阳。
如今获嘉大白菜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亩产过万斤。
科技团队让这口老味道更“得劲”,
煮烩菜汤浑如奶,炒着脆甜无丝,连拉肚子的都能吃,因为粗纤维低。

内蒙古乌兰察布化德县的“地理标志宝贝”,打小在阴山北麓的黄土地里扎根。
清末“招垦实边”时,山西河北的庄户人带着菜种跨山而来,
在旱地里试种,靠天吃饭也能长出脆生生的白菜。
明成祖北征时,士兵手脚生疮,老军医教他们用白菜板蓝根熬汤擦洗,
竟好了大半,这“白菜救兵”的典故,至今还在老辈人口中传。
这白菜模样俊,叶球弹头形,外叶浓绿内叶嫩黄,叶柄甜脆得能当水果吃。
含糖量、维生素C都高,粗纤维少,咬一口“咔嚓”响,清甜直往嗓子眼钻。
如今,远销京津冀,还漂洋过海到日韩。

明朝时官窑民夫在此垦荒种菜,广东白菜与洞庭湖气候碰撞,育出“棵大味甜、
纤维细少”的广兴洲大白菜,如今已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老辈人说:“广兴洲的白菜,越吃越爱,赛过肉!”这味儿,藏着六百年江湖气。
苏东坡曾赞“白菘类羔豚”,陆游更写“九月区区种晚菘”,
白居易诗里“浓霜打白菜”的鲜脆,齐白石画中“菜中之王”的霸气,都往这颗白菜里攒。
这白菜生得倒卵状,菜帮薄如纸,
咬一口“咔嚓”脆,甜津津的汁水直往喉里钻。
炒则鲜嫩,炖则浓香,连菜梆子都能腌成“麻辣菜梆”,下饭一绝。

甘肃榆中县的“高原甜心”,自明万历三十三年《临洮府志》记载起便扎根黄土高原。
秦时蒙恬北伐匈奴,“移民实边”将中原农耕技术带入榆中,
自此大白菜在海拔1480—3670米的冷凉气候中孕育出独特甜脆。
它叶球炮弹形,外叶翠绿如翡翠,内叶嫩黄赛蜜糖,菜帮薄脆无筋,
生食清甜似甘泉,熟食鲜浓胜肉汤,
当地人常说“这白菜,脆生生甜津津,赛过蜜糖罐儿”。
四百年间,它从农家菜园走向全国餐桌,2010年获国家地理标志认证,
更因高钙高维C被称为“菜中之王”。

是重庆武隆的“山珍”,2008年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它诞生于19世纪高海拔山区,
20世纪80年代后因引进新品种、扩大种植,成为重庆最大高山蔬菜基地。
武隆人常说“高山白菜甜过初恋”,
仙女山、白马山,海拔1200米以上的黄壤地,昼夜温差大,山泉水灌溉,
让白菜脆嫩甜爽,炒着香、煮着鲜、凉拌更巴适。
这白菜它承载着百年种植史,从山民自食到外销东南亚,成了“保秋淡”的硬通货。
当地老农说:“高山白菜不怕晒,越晒越甜!”
如今,它带着泥土香和山风味,成了餐桌上的“烟火气担当”,
咬一口,脆生生、甜津津,像把山野的清冽都裹进了菜里,让人直呼“安逸得遭不住”!

山东济南历城区唐王镇的特产,打唐朝李世民东征时就种下了根。
当年秦叔宝说“俺家乡最大叶子就是大白菜”,李世民听了直咂摸味儿,一拍大腿:“就种这大叶的!”从此唐王村多了片白菜地,沾着皇气长成了“济南四美蔬”之一。
苏轼被贬惠州时还念叨着这口儿,说“白菘类羔豚”,小火慢炖能香得人掉眼泪。
这白菜心里黄白,脆得能听见“咔嚓”声,甜得跟蘸了蜜似的,凉拌脆生生,炖汤浓得像奶。
500年传承的“唐王小根”品种,干物质多、水分少,越存越甜。
如今地标认证、非遗种植技艺加身,成了农民的“聚财菜”。

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的“冬日宝”,自民国起便扎根黑土地,2010年登国家地理标志榜。
相传康德元年(1934年)始种,金源文化里藏着它的魂,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时期,大白菜是冬季窖藏的“硬通货”,冻不着、坏不了,熬过零下三十度的寒冬,仍是餐桌上的“白月光”。
清代农学家丁宜曾在《农圃便览》里写:“小雪刨窝心白菜,竖排屋内,埋干润土,顶盖苫,雨雪不侵”,
这窖藏术让白菜越冬仍鲜嫩如初,成了北方人“百菜不如白菜”的底气。
它个头敦实,叶球紧实如石,单株重4公斤,
叶色深绿泛光,纤维少到“脆生”,咬一口甜津津的,炖酸菜、炒粉条、腌辣白菜,样样行。

河南商丘夏邑县的“百菜之王”,2019年摘得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金名片”。
这菜可不是普通货,
叶球筒形平头,外叶浅绿如春缎,内叶嫩黄似蜜蜡,咬一口“咔嚓”脆生,甜津津的汁水裹着95%的水分,直往喉咙里钻。
当地老辈人常说:“夏邑白菜,赛过‘玉白菜’!”
冬日里,农家人窖藏白菜过冬,取根“空壳篓儿”的白菜帮子,
配点粉条猪肉炖一锅,热气腾腾暖到“胳老瓣”(膝盖)。
它不挑做法,凉拌、醋溜、炖豆腐,样样行得通。
夏邑人还爱说:“白菜就是‘百财’,吃了财气旺!”
如今这菜年销25万吨,从东北到广东,餐桌上的“清白”滋味,早成了乡愁的代名词,
不掺假,不花哨,就图个实在劲儿。

根扎燕山南麓,喝着偏硅酸锶的矿泉水长大,
打清光绪年间就载入《玉田县志》,“甘脆甲他邑”,成了“玉菜”美名。
慈禧老佛爷尝过直咂摸嘴,赐名“御菜”要连年进贡,
这典故在玉田老辈人嘴里传得活泛:
封为“慈玉”白菜,漂洋过海到港澳,连翡翠雕的“玉白菜”都跟着沾光。
如今“玉田包尖”成了地理标志,
分大、二、小包尖三姐妹,二包尖最金贵,亩产万斤能存仨月,
菜心生吃甜脆赛水果,菜帮炒着不乱汤,硒含量超同类,是富硒白菜里的“扛把子”。
这白菜,叶球直筒拧抱,顶部尖得像锥,叶色深绿脉络细,
咬一口脆生生带着甜,汁水乳白不寡淡。
老辈人说“立冬不出菜,必定雪中盖”,
秋末冬初的白菜地,绿浪翻滚像盖了床厚被,瞅着就踏实。

山东胶州人的“命根子”,唐代起就是贡品,人称“唐菜”。
袁世凯复辟时惦记这口鲜,派官差抢收三里河七分地的“胶白”,
谁料极寒突袭,白菜冻成“铁疙瘩”,最终他到死都没吃上这口,成了“皇帝梦”里最憋屈的遗憾。
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写“红头绳系菜根倒挂”,说的就是它,
如今每棵都贴追溯码,从播种到上市全程可查,真赛了!
这白菜帮子薄得能透光,芯儿白得像刚挤的羊奶,
咬一口脆生生、甜津津,生吃赛过水果,炖虾、拌海蜇皮更鲜得掉眉毛。
胶州人冬天离不了它,风寒了煮白菜根水,馋了就整锅白菜豆腐汤,暖胃又暖心。
千年来,它从东京博览会金奖走到斯大林寿礼,
从“百财”玉雕到寻常百姓灶台,活成了山东人的烟火气。

天黑了,厨房的灯亮起来。
锅里炖着白菜,热气扑到窗上,结成了雾。三千年的风霜雨雪,都化在这口锅里了。
你夹一筷子,脆生生的响。
那声音,穿过多少朝代,还在百姓的碗里响着。
白菜还是那个白菜,人换了一茬又一茬。
它不说话,只在滚烫的锅里翻滚,把苦日子熬出甜味来。
尝尝吧,这熬了三千年的安稳。


![我国没有争议的南方12省过年吃饺子的就是北方这个最准[呲牙笑]南北方是以](http://image.uczzd.cn/2211055942514969960.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