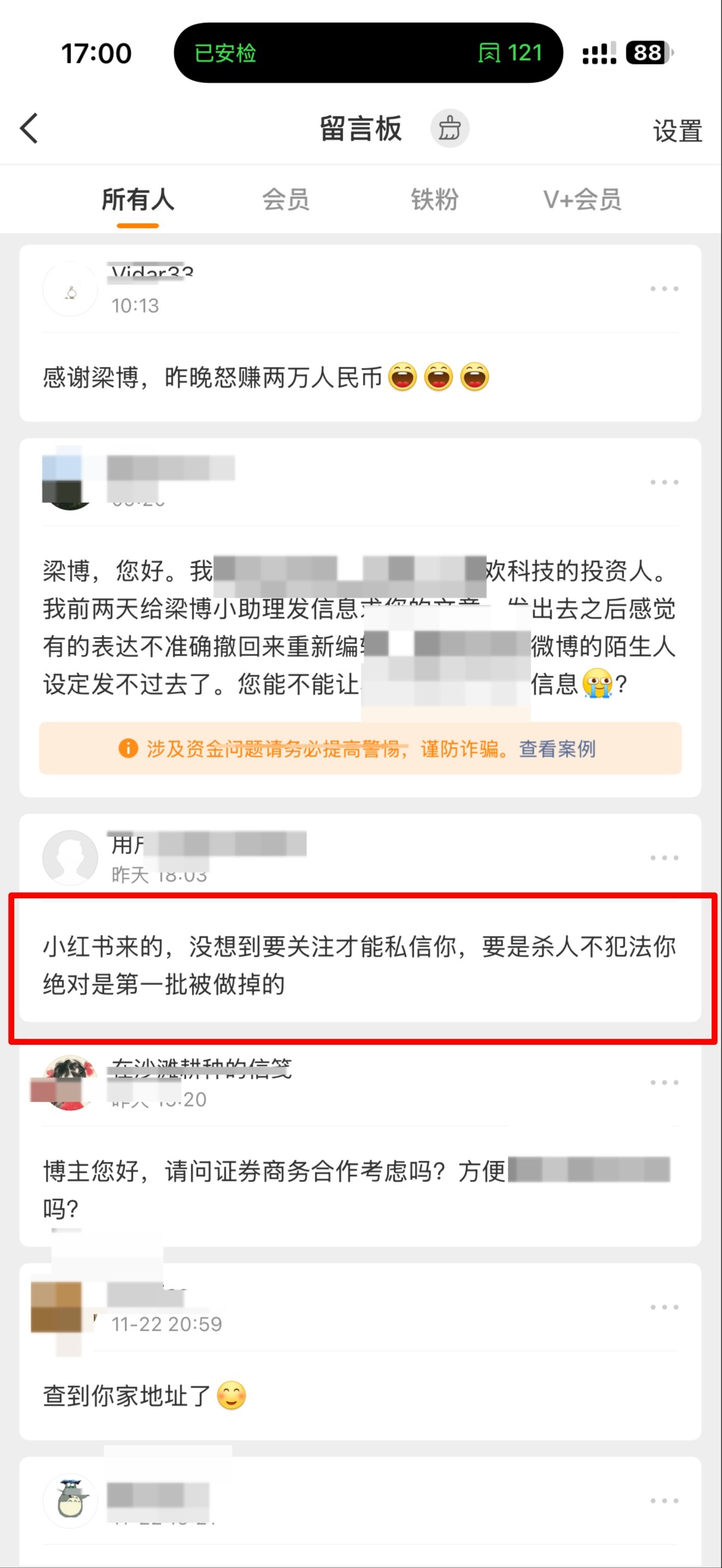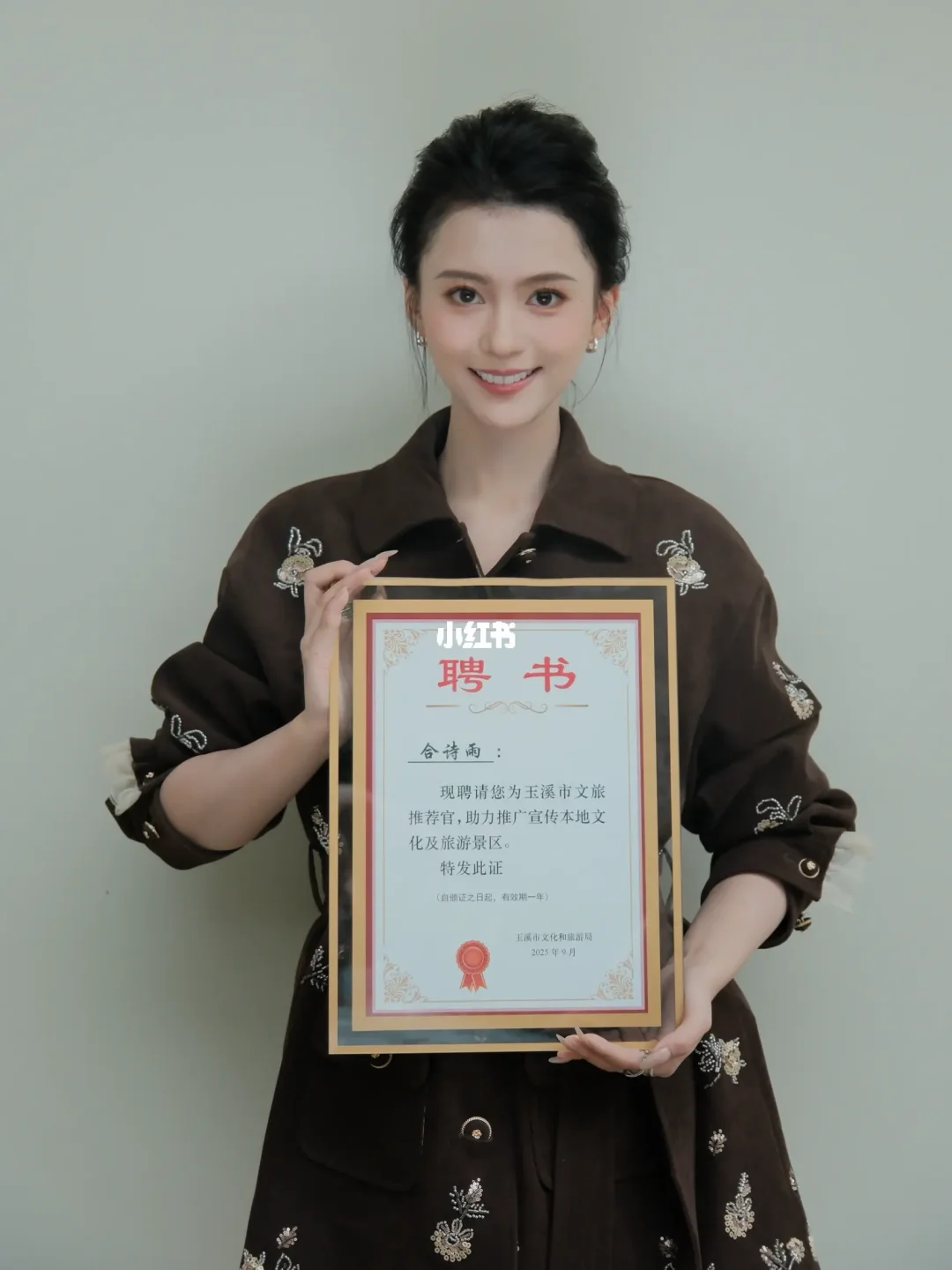沈玉笠把我从城南落魄户中捞出,纳为妾。
三年荣宠,羡煞旁人。
直到祭祖那日,萧婉婉指着我惊呼:
“玉笠哥哥,她怎生得与我这般相像!”
“粗鄙婢妾,东施效颦罢了。”
而后的日子里,情意不再,只有他护着郡主掘我父母坟茔。
还一脚踹向我孕腹。
我撞上爹娘残碑,胎儿的血浸透了散落一地的白骨!
后来烟雨江南,他蓬头垢面缩在石桥下,死死盯着我绣坊的窗:求您……再熬碗相思羹?
1.
我端着祭祀的果盘,手有点抖。
管家说今天许我站近些,是侯爷的恩典。
我心里又暖又怕,小心翼翼不敢出错。
突然,门外喧哗。
是长公主驾临,而她身边那位华光璀璨的郡主……
我下意识抬头,瞬间如遭雷击。
世上竟有如此相似之人?
不,是我竟与她如此相似!
郡主萧婉婉也看见了我,“玉笠哥哥!她是谁?怎生得……竟与我这般相像?”
满堂寂静,所有目光钉在我脸上。
那里面是毫不掩饰的鄙夷。

我浑身血液霎时冻僵,看向我的夫君,靖安侯沈玉笠。
他却已侧身护在郡主身前,“婉婉莫惊,不过一个粗鄙婢妾,东施效颦罢了,岂能与你真凰相较?”
粗鄙婢妾……东施效颦……
原来那些夜间的缱绻,病中的呵护,赞我“独一无二”的眉眼,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笑话。
我被他眼中的寒意钉在原地,屈辱和恐惧瞬间攫紧了我的喉咙。
“还愣着做什么?滚下去!”
他厉声呵斥,仿佛多看我一眼都嫌脏。
我几乎是踉跄着逃到宗祠最偏僻的角落,浑身抖得站不稳。
心脏疼得快要裂开,耳边却飘来老管事压低的唏嘘:“……唉,侯爷当初从城南破落户里把她捞出来,不就是图这张脸像极了那位没归京的主儿……如今正主回来了,这赝品啊,好日子到头喽……”
我死死捂住脸,眼泪烫得吓人。
原来我活着的价值,就是这张脸。
现在正主回来了,我这赝品,该扔了。
2.
宗祠那冰冷刺骨的寒意,仿佛已渗进了我的骨髓。
我缩在荷风院,对着模糊的铜镜。
镜中那张脸,曾经被沈玉笠温柔抚摸过无数次的脸,现在只觉得恶心。
什么独一无二,全是骗鬼的!
我就是个赝品,一个顶着别人脸的玩意儿。
深夜,门“哐”一声被踹开,冷风灌进来。
沈玉笠站在门口,眼神冻得死人。
“今日,你也见到了,昭阳郡主归京。”
我的心猛地一缩,“所以……侯爷,所以妾身这三年来……那些情意,在您眼中……当真……当真只是……”
后面的话哽在喉间,怎么也问不出口。
是替身?
是慰藉?
是填补萧婉婉空缺的玩意儿?
沈玉笠眉头微不可察地一蹙,“你与她有几分相似。当初将你从城南带出来,纳你入府,确有慰藉相思之意。”
“如今她回来了,你需认清自己的位置。我不希望你再出现在婉婉眼前。”
“看在三年你尽心伺候的份上,本侯会安排你去京郊别庄静养,”
“给你一笔足够丰厚的银钱,保你后半生衣食无忧。”
我怔怔地看着他,巨大的荒谬感几乎让我发笑。
衣食无忧?

静养?
“若妾身不愿去呢?”
他抬眸,目光冰冷,“那你告诉本侯,是你那点微不足道的倔强重要,还是让你父母在城西那处坟茔里……安安稳稳地长眠重要?”
我的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
城西杜家坟茔那是我双亲唯一的安息之所。
“听说那地方风水不错,本侯近来正想寻一处开阔地,修个跑马场。”
他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修马场!
平坟!
曝尸荒野!
恐惧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比任何羞辱和心碎都来得剧烈!
我浑身抖若筛糠,“侯爷!您不能……您怎么能……求您!那是妾身的爹娘啊!”
他静静地看着我崩溃,眼中没有丝毫动容。
“去,还是不去?”
所有的倔强、悲愤、不甘,在逝去至亲的威胁面前,被碾得粉碎。
父母在九泉之下都不得安宁……这比杀了我还要痛苦千万倍!
“……婢妾……遵命。”
3.
京郊的庄子,比荷风院更冷,更荒。
风从破窗户往里灌。
管家丢下那袋“丰厚”的银钱和几句不咸不淡的训诫后,便再无人问津。
只是没多久,庄门被粗暴地撞开,几个侯府家丁闯了进来,神色倨傲。
为首的管事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对着蜷在灶台边的我冷声宣令:“杜姨娘,收拾一下,即刻随我们回府!”
“回府?侯爷他……有何吩咐?”
管事嗤笑一声,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吩咐?是昭阳郡主想你了!郡主金尊玉贵,今儿不知怎的,忽然想起你做的什么‘相思豆羹’,点名要尝尝你这手艺呢!”
他将“相思”二字咬得极重,满是嘲弄。
相思豆羹……
那曾是沈玉笠缠绵病榻时,我守在小厨房熬煮几个时辰,只为他能舒服些的汤羹。
那时他握着我的手,说那羹里有“家的味道”,暖了他的胃,也暖了我的心。
如今,竟成了萧婉婉口中一个轻飘飘的“尝尝”,成了供她取乐的玩意儿。
我被半押半推地带回了靖安侯府。
直接推进了紧挨着主院大厨房的一个狭窄耳房,这里油烟弥漫,热得窒息。
“快着点!郡主等着呢!”
一个婆子不耐烦地催促,塞给我一小袋红豆和几样简单的材料。
我麻木地生火,淘米,洗豆。
冰冷的井水刺得冻疮钻心地疼。
红豆在锅中翻滚,氤氲的热气模糊了视线。
相思?

何其讽刺!
这羹里熬煮的,分明是我早已被践踏成泥的尊严和一颗千疮百孔的心。
羹终于熬好,我端着这碗滚烫的羹,走向笑语晏晏的花厅。
珠帘掀开,暖香扑面。
萧婉婉依偎在铺着白虎皮的软榻上。
沈玉笠就坐在她身侧,正低头与她说着什么,眉眼间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专注。
那画面,和谐得刺眼。
我垂首,将羹碗轻轻放在萧婉婉面前的小几上,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郡主,您的豆羹。”
萧婉婉漫不经心地抬起眼皮,用银匙舀起一点点,浅尝了一口。
随即,她秀眉一蹙,“啧”了一声,将银匙丢回碗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
“玉笠哥哥,这就是你以前病中常喝的?这也太甜腻了吧!红豆都煮烂了,豆腥气也没去干净……”
她转头,带着鄙夷的目光扫过我,“你以前就是喝这个养病的?也不嫌粗陋?”
我的脸瞬间烧得通红,每一句挑剔,都像鞭子抽在我心上。
这曾是我倾注心意、被他赞过的味道,如今在“真品”面前,成了不堪入口的“粗陋之物”。
我下意识地看向沈玉笠,哪怕是一丝一毫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