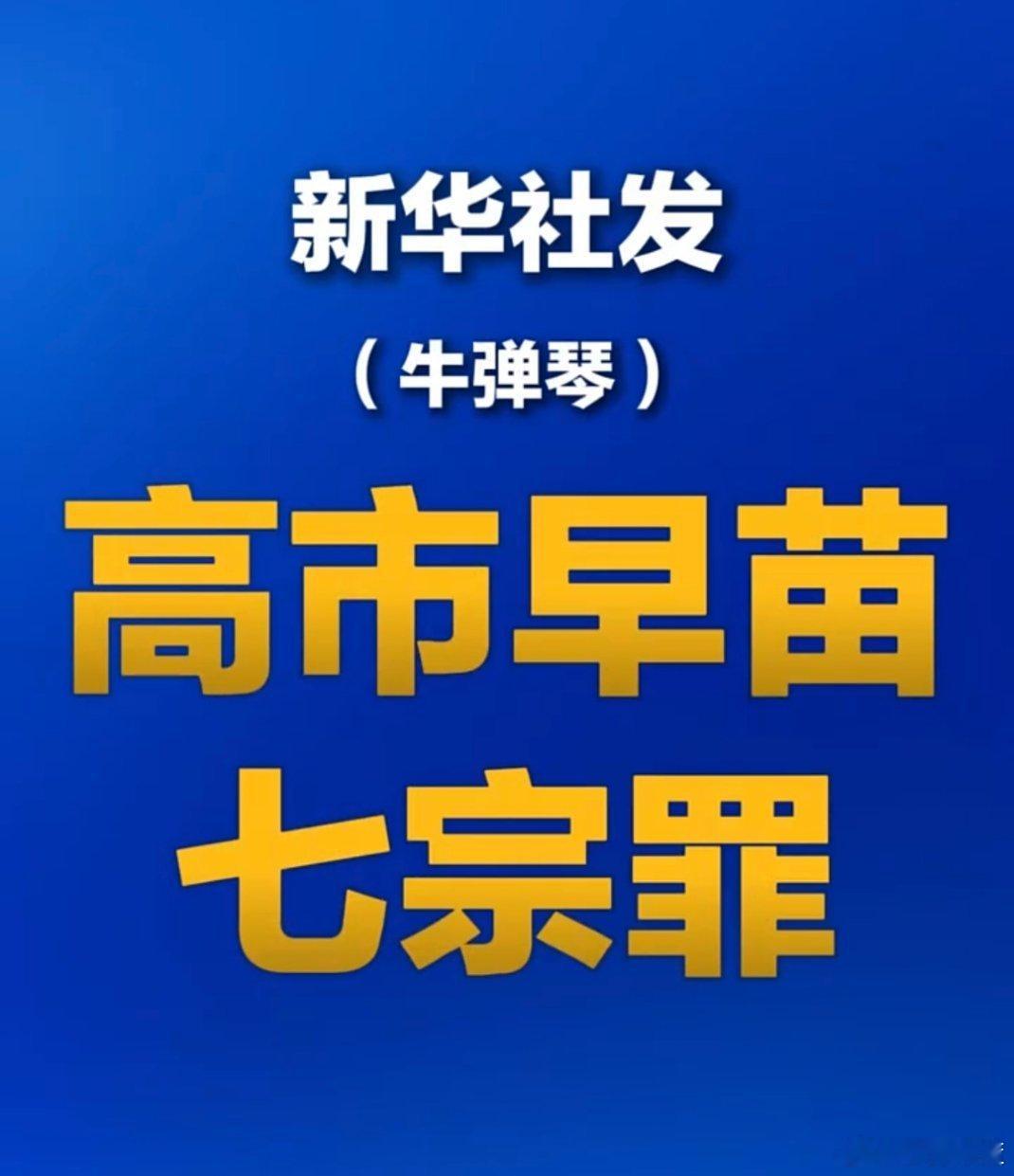中午小憩,一场光怪陆离却又无比真切的梦,醒来后让我愣神了足足五分钟,反复琢磨:我上辈子,会不会真是个漂亮姑娘?
梦的开篇,是带着浓郁年代感的乡村街道,约莫是2000年代的模样,没有平整的水泥柏油路,更不见鳞次栉比的二层小楼。脚下是夯实的土路,坑洼处偶尔垫着几块青灰色砖头,像是岁月留下的补丁。道路两旁清一色的平房,斑驳的土墙爬着暗绿色的青苔,屋顶露着参差不齐的木条,铺着老家特有的煤渣灰混合顶,连像样的砖房墙壁都少见,透着一股原始又质朴的烟火气。
我和媳妇并肩走在这条路上,晚风(或许是梦里的风)带着泥土的湿润气息,摸了摸口袋,烟盒空空如也。“去买两包烟吧?”我转头对她说,随后推着一辆半旧的自行车,载着她慢悠悠往村里的小卖店去。
小卖店的模样和周遭环境完美契合,简单到近乎简陋。进门就看见墙上挂着一台老式电视机,正播放着一首耳熟能详的港台粤语歌,旋律缠绵又怀旧。店里站着三四个年轻人,有的靠墙斜倚着,有的蹲在地上,手里夹着烟,眼神跟着电视屏幕走,嘴里断断续续哼着歌词,气氛闲散又热闹。正中间靠门的位置,摆着一个长长的玻璃柜台,里面零零散散躺着各种香烟,包装都不算精致;柜台后面是个木质柜子,分层摆着酱油醋、肥皂、糖果之类的生活用品,零食也只有寥寥几种,透着几分年代的匮乏感。

店主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头发微微谢顶,露出光洁的额头,五官轮廓分明,看着特别像某位电视剧里的老戏骨,越看越眼熟,却怎么也想不起名字。“老板,来两包南城。”我张口就说,心里对这个牌子无比笃定——那是种土黄色的硬盒香烟,包装带着几分粗糙,现实里我从未见过,梦里却记得清清楚楚。
刚说完,手机突然响了,我示意媳妇在店里等,转身走出小卖店接电话。几句寒暄过后挂了机,回到店里时,媳妇已经付了钱,手里拿着一包25块钱的七匹狼。“咱啥条件呀?”我接过烟,哭笑不得地说,“至于抽这么好的吗?”说着,我转身冲老板摆手:“老板,麻烦换成南城,刚才说的那个。”想了想,又补充道:“要不直接换五包吧,南城不是五块钱一包嘛,划算。”
老板闻言,脸上掠过一丝不情愿,眉头微蹙,但还是耐着性子,弯腰从柜子最底下的角落翻了半天,掏出五包南城递给我。接过烟的那一刻,心里莫名涌上一股亲切感,就像见到了许久未见的亲人,说不出的踏实。我迫不及待撕开包装,却发现这烟压根没有塑封,软乎乎的纸盒摸着粗糙得很,里面连常见的银色锡箔纸都没有,只用一层泛黄的草纸垫着。“可能是太便宜了,包装就这样吧。”我心里嘀咕着,抽出一支往嘴里塞,刚要摸打火机,却觉得烟的直径不对劲——低头一看,那竟然是支“双头烟”,两个烟头紧紧粘在一起,形状像极了缩小版的望远镜,又有点像双头蛇,透着几分诡异。
我把剩下的烟都倒了出来,更奇怪的事出现了:卷烟纸五花八门,有的带着浅浅的竖形条纹,有的是纯白色,还有几张微微发黄,粗细也不太均匀。“老板,你这造假也太明显了吧?”我把烟往柜台上一摊,语气带着几分不满,“双头烟、包装不统一,连锡箔纸都没有,这肯定是你自己做的吧?”
话没说完,老板打断我,语气硬邦邦的:“你想咋地?”“还能咋地,换回来呗。”我说道,“把七匹狼给我,再送我一包,要求不高吧?”老板头摇得像拨浪鼓:“换七匹狼可以,送烟不行。”我掏出手机,作势要拨号:“那我只能给烟草局打个电话,问问这烟合不合规了。”
旁边的年轻人还在跟着电视哼《吻别》,断断续续的歌词飘在空气里,却丝毫没影响我的气势。老板盯着我看了几秒,微微低头,浅浅摇了两下头,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等一下。”说完,他转身走进里屋的卧室,片刻后拿着一个盒子走了出来。
那是个精致的菱形盒子,六个角分别是六种不同的颜色,红、黄、蓝、绿、紫、橙,在昏暗的店里泛着柔和的光,一看就不是凡物。“这个盒子,我攒了好久,一直舍不得拿出来。”老板把盒子递给我,语气里带着几分不舍。我好奇地打开,发现是大盒套小盒的设计:第一层铺着一层块状烟丝,每一块都用红色丝带系着小巧的蝴蝶结,凑近了能闻到一股浓郁又纯粹的烟草香;第二层是五颜六色的糖果,形状各异,大小不一,包装上印着英文和可爱的图画,都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式;第三层则是一沓卷好的烟纸,色彩斑斓,红的、粉的、浅蓝的、鹅黄的,质感细腻。“这烟纸是我儿子去香港的时候给我带的,每种颜色都有不一样的味道。”老板解释道,“那糖果能消除口臭,抽再多烟也不怕。这个,送给你了。”
我又惊又喜,心里的不满瞬间烟消云散,甚至有点不好意思起来,连忙道谢。和媳妇走出小卖店,她突然从包里拿出一副耳坠递给我:“拿着吧。”那是一副纯银的耳坠,链条纤细,中间串联着两颗圆润的珍珠,末端坠着两颗菱形的水晶,灯光下闪着温润的光。我开过几年饰品店,还帮人打耳洞,为了证明不疼,自己的耳朵上打了好几个孔,对这些小物件格外敏感。接过耳坠,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就把它戴在了耳朵上。
神奇的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了。
眼前的世界仿佛被按下了“刷新”键,一切都变得鲜活又明亮。我低头看向自己,身上早已不是原来的衣服:下身是一条曳地的红色长裙,裙摆随着动作轻轻晃动,像一团燃烧的火焰;上身是一件洁白的衬衣,领口系着一个鲜红的蝴蝶结,外面套着一件修身的红色马甲,脖子上还搭着一条咖啡色的短围巾,胸前别着小巧的胸针和淡雅的胸花,整套打扮精致又俏皮。我转头看向小卖店的玻璃窗,里面映出的模样让我心头一颤——红色耳坠衬着白皙的皮肤,红色领结点缀着灵动的眉眼,竟有种公主般的惊艳。

作为一个男人,活了这么多年,我从未体会过这种感觉——那种因漂亮而生的、肆无忌惮的自信。我蹬上自行车,原本坑洼的土路仿佛变得无比平坦,车轮滚动得轻快又顺畅。眼角的余光里,能看到路边有人停下脚步,转头看向我,那目光里没有异样,只有欣赏。我挺直脊背,迎着风往前骑,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笃定,甚至一时忘了自己原本的性别,只想着沉浸在这份五彩缤纷、光芒四射的自信里,像美少女战士变身的瞬间,充满了无限的力量。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境拉回现实,醒来后,我坐在床上发呆了很久,梦里的场景清晰得仿佛就在刚才,尤其是戴上耳坠变身的那一刻,那种极致的自信和美好,让人回味无穷。
我忍不住想,上辈子,我会不会真的是那个村子里最漂亮的姑娘?不然怎么会在梦里,对那份属于女性的美丽和自信,有如此真切的感知?其实仔细想想,做女人也挺好的,除了生育的辛苦,其余的都无比美好。如今男女平等,女人能做的,男人也能做,而那些独立、自立的女性,活得通透又惬意,地位甚至比男人还要高。这场梦,或许是一场穿越时空的邂逅,让我短暂体验了另一种人生,也让我对性别、对自信,有了不一样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