晌午的日头毒得很,我把牛拴在树荫下,自己蹲在地头啃凉馍。
富贵这名字,是我爹请算命先生起的,说是命中带贵,将来能光宗耀祖。
谁知道这贵气来得这样迟,迟得我差点没等到。
要是那年春生没拉我去赌场,要是我没碰上龙二,要是我爹那天没给我那三块大洋——日子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

可我偏偏去了。龙二的骰子在我耳边哗啦啦响,像招魂的铃铛。
我把家产一百亩地输得干干净净,我爹气死在粪缸旁,我娘一病不起。家珍抱着凤霞站在当院里,眼睛红得滴血。
但……今儿个咱不说这个。
咱说说要是没输那场赌,日子会咋过。

我牵着牛往家走,夕阳把我和牛的影子拉得老长。这牛通人性,晓得我腿脚不利索,走得慢吞吞的。要是没输那场赌,我大概不会懂得一头牛的好。
“富贵啊,”我娘要是还活着,准会这么说,“咱家这一百亩地,你得好好经营。”
我会天不亮就下地,看着长工们锄草施肥。
家珍会给我送饭,凤霞跟在后头跌跌撞撞。有庆要是没死,该是个壮实小伙子了,能帮我扛半袋粮食。

可我知道,这都是瞎想。龙二赢了我们的宅子,第二年就被定为地主枪毙了。
枪毙那天我躲在人群里看,子弹从他后脑勺进去,从前额出来,带出一团红白的东西。要是没输那场赌,吃枪子儿的该是我。
所以你说,输那场赌是福是祸?

我把牛牵进棚里,添了把草料。这牛是公社分给我的,老得牙都快掉光了,跟我一个德行。我摸着它的脊背,骨头硌手。
“老伙计,咱俩谁先走还不一定呢。”牛甩甩尾巴,像是听懂了。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大概还是那个穿绸缎褂子的少爷,不会晓得一碗米粥的香甜,不会懂得一双布鞋的暖和。家珍死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下辈子还要做夫妻。”
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眼睛亮得吓人。我说好,下辈子我耕地你织布,咱吃糠咽菜也甘心。
风霞要是没死,该嫁人了。有庆要是没死,该娶媳妇了。苦根要是没死,我该抱重孙子了。
可他们都死了,就我还活着。

有时候我想,活着就是个圈套。你越想好,它越不让你好。你认命了,它反倒给你留条活路。
我把牛拴好,往家走。我的茅草屋在山坡上,孤零零的。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住的是青砖大瓦房,院里种着海棠树。春天开花的时候,家珍喜欢在树下做针线,凤霞围着树跑,花瓣落她一头一身。
可现在我就这茅草屋,下雨天漏水,刮风天透风。可我睡得踏实,一觉到天亮。要是还住大瓦房,我怕是要睡不着觉——怕土匪来抢,怕官府来征,怕败家子来骗。
共产党来了,斗地主分田地。我因为早败光了家产,倒落了个贫农成分。分了三亩地,一头牛。龙二要是知道,准气得在阴曹地府跳脚。
所以说啊,人算不如天算。

我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生火做饭。一碗稀粥,一碟咸菜,我吃得有滋有味。吃完坐在门槛上抽烟,看月亮从东边爬上来。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现在该是怎样的?大概还是那个不知饥饱的少爷,不晓得一粒米的珍贵,不晓得一文钱的难挣。
家珍还会是那个低眉顺眼的少奶奶,凤霞还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女儿——医生说凤霞的哑病是发烧烧坏的,跟穷不穷没关系。
有庆死得冤,给县长女人献血,活活被抽死了。我找县长理论,发现是春生——当年拉我去赌场的春生。你说这是不是命?
春生后来也挨批斗,上吊死了。死前来找过我,说对不起我。我说都过去了,咱们都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还计较啥。

要是没输那场赌,有庆会不会死?难说。这世道,该死的时候躲不过。
我磕磕烟袋,准备睡觉。明天还要早起耕地。公社解散了,地又分给个人了,我得好好种,不能饿死。
躺在床上,我想起爹死那天说的话:“鸡养大了变成鹅,鹅养大了变成羊,羊养大了变成牛。”
“牛养大了呢?”我问。
“牛养大了,”爹说,“共产主义就实现了。”
现在我有牛了,虽然老得快走不动了。共产主义实没实现我说不好,但我有牛了,有地了,能自己养活自己了。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大概不会懂得这些道理。人会一直糊涂下去,直到死都不明白为啥活着。

家珍说得对,人只要活得高兴,穷也不怕。我们这辈子经历了太多,打仗、土改、大跃进、文革,都挺过来了。现在日子好了,他们却不在了。
有时候我觉得他们都没死,就在我身边。
我耕地的时候,家珍坐在地头看我;我吃饭的时候,凤霞给我夹菜;我睡觉的时候,有庆给我盖被子;我抽烟的时候,苦根趴我腿上听故事。
真的,我不骗你。人活着,就得有点念想。
月亮从窗口照进来,明晃晃的。我睡不着,起身去看牛。牛趴在地上反刍,眼睛亮晶晶的。
“老伙计,你也睡不着?”我拍拍它的脑袋,“咱俩说说话。”
牛呼哧呼哧地喘气,像是在回应。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不会和一头牛说话。我会和账本说话,和骰子说话,和酒肉朋友说话。现在我和牛说话,牛比人实在,你给它草吃,它就给你耕地,不骗你,不坑你。

天快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梦见我没输那场赌,地主成分,被枪毙了。家珍带着凤霞有庆改嫁,受尽白眼。苦根根本没机会出生。
我吓醒了,一身冷汗。
牛在棚里叫,该耕地了。
我起身套牛,迎着朝阳往地里走。露水打湿了我的布鞋,凉丝丝的。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不会注意到露水是啥感觉,不会晓得晨风是啥味道,不会懂得一头老牛的好。
所以说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输了家产,赢了人生。虽然这人生苦得像黄连,但我嚼出甜味来了。
日头出来了,我和牛的影子越来越短。我扶犁,牛拉犁,配合得默契。

地头有棵槐树,开花的时候香得很。我要是干累了,就坐树下歇歇,抽袋烟,想想从前的事。
不想也好,活着就好。
牛突然不走了,扭头看我。我顺着它的目光看去,地头站着个人影,像是家珍。
我知道是眼花。家珍死二十年了。
可我还是喊了一声:“家珍,是你吗?”
没人回答。只有风吹过玉米地,沙沙地响。
牛又开始走,一步一步,稳稳当当。
我忽然明白了,不管输没输那场赌,该来的都会来,该走的都会走。活着就是看着来来走走,自己还得往前走。
就像这牛,拉着犁,一步一步,不管地头有多远,只管走。
走一步,少一步。
走一步,赚一步。
日头升高了,我汗流浃背。牛也喘着粗气。
“老伙计,歇歇吧。”我卸了套,牵牛到树荫下。
我们并排躺着,他反刍,我抽烟。

要是没输那场赌,我不会知道,和一头老牛并排躺着抽烟,竟是这天底下最自在的事。
抽完烟,我拍拍牛屁股:“干活吧,老伙计。干完了回家,我给你豆饼吃。”
牛叫了一声,像是答应了。
是啊,干活,回家,吃豆饼。这就是日子。
输没输那场赌,日子都得这么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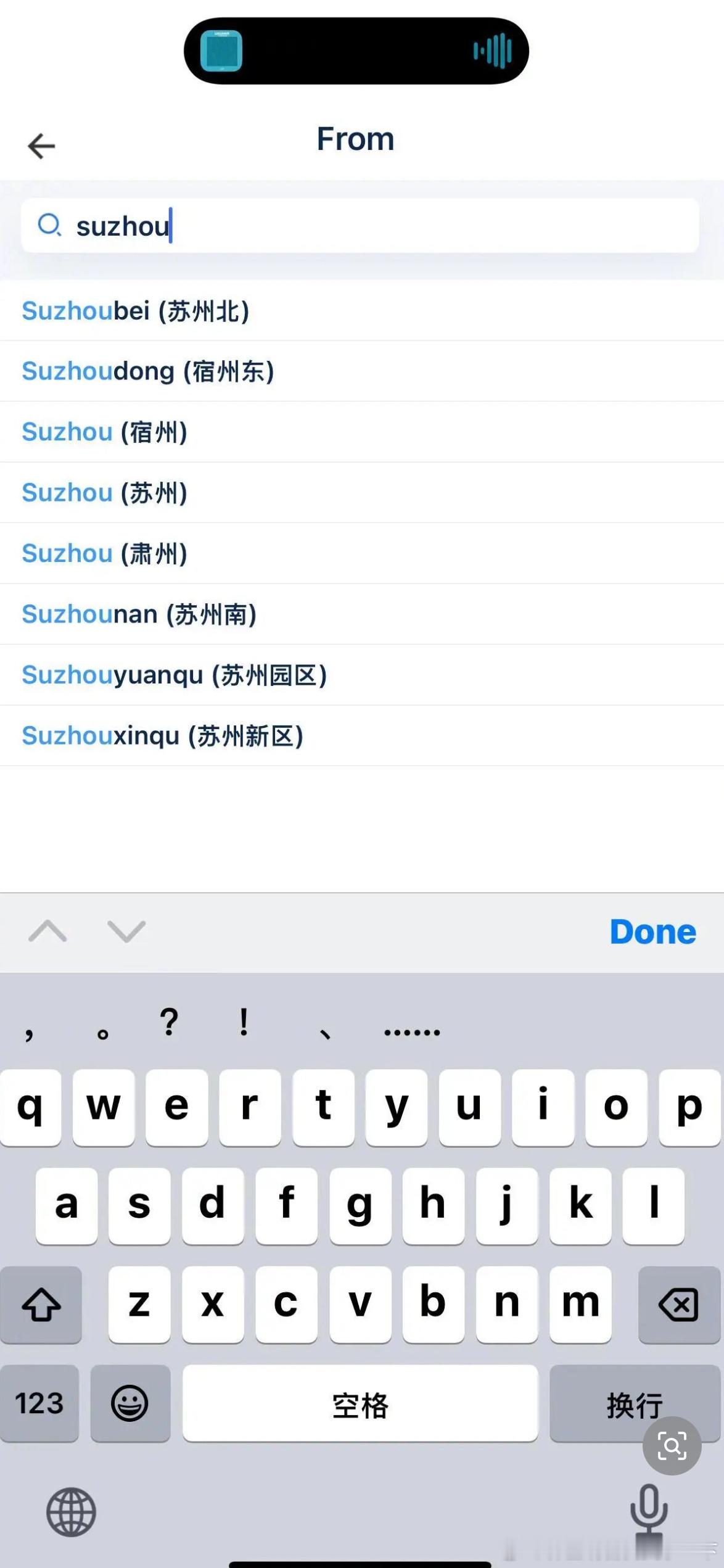
![她姐于歪超爱[doge]](http://image.uczzd.cn/7377986251097447503.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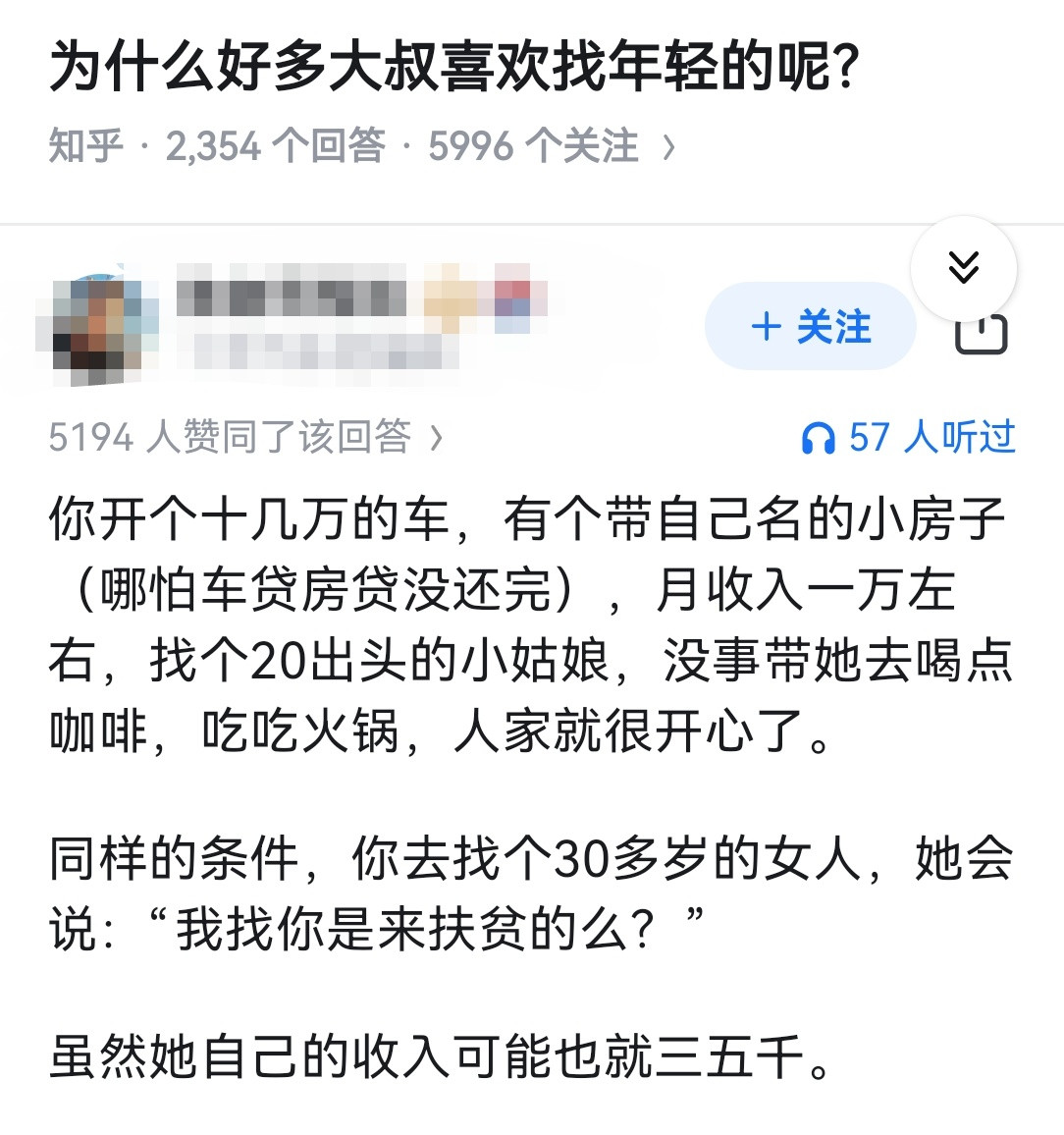
![这图谁做的[???][???][???]我这几天一直盯着这个榜单从来都不是这样[???]](http://image.uczzd.cn/6576684139151121982.jpg?id=0)

![蛋糕直播分享自己小时候的QQ空间,现在看是真羞耻啊[笑着哭],不过大家应该都经](http://image.uczzd.cn/1214658826239864651.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