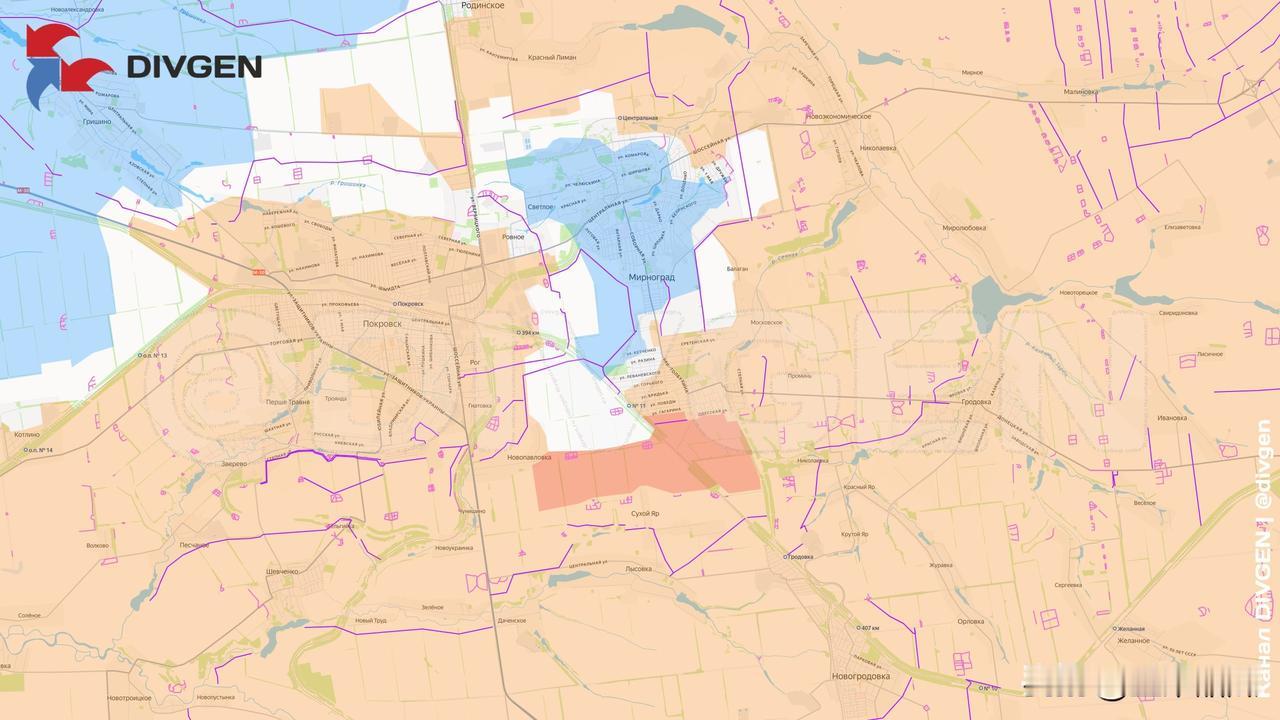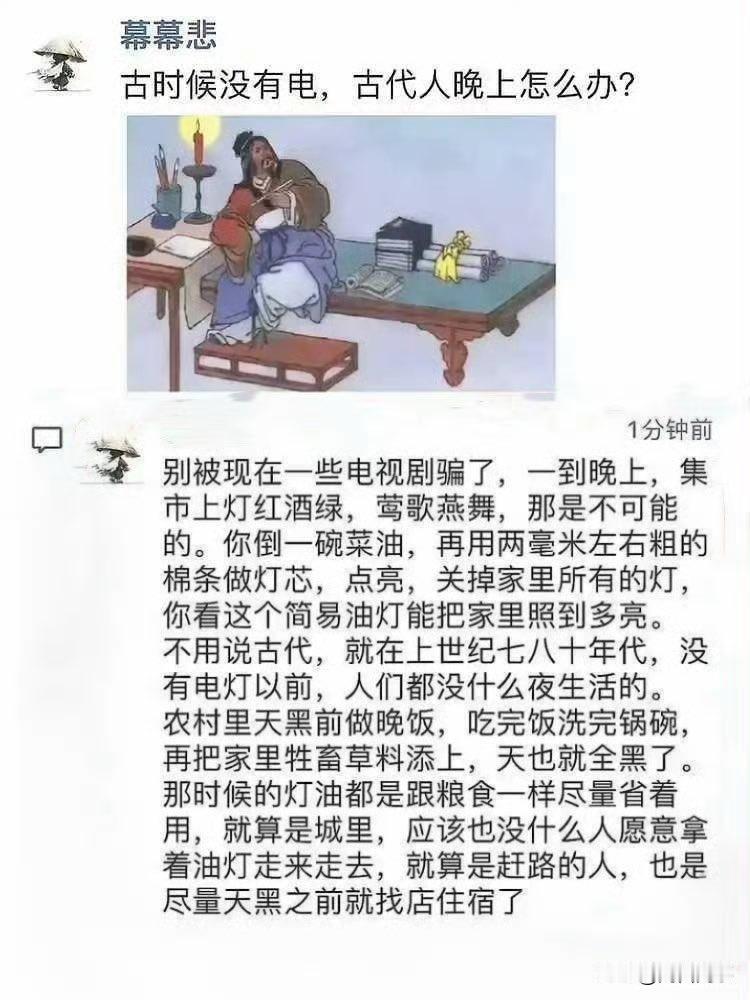一
杜甫的写作,地负海涵,千汇万状,风格多样到自成一个宇宙。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关于杜诗的“宇宙学”(cosmology)论域。元稹和叶燮的两段话,可以代表后人对杜诗生成面貌的总体描述:
至于子美,所谓上薄风雅,下赅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1]
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 [2]
就杜诗的集大成而言,历风雅、汉魏与六朝,这些影响要素并不是同时实现的。举凡苏、李、曹、刘、颜、谢、徐、庾、沈、宋,他们一个一个在杜甫的写作中,此一时或彼一时,这一处或那一处,投下了深浅不一的影子。关键在于杜甫的生活遭际常有所不同,致使其关注的焦点与语言的方式随之而转换。而说到杜甫的一生,岂不就等于汉魏与六朝诗人们的主要生活形态一个历时的浓缩?换句话说,他难道不正是把苏、李、曹、刘、颜、谢、徐、庾、沈、宋这么些人的生活又一一再活过一回?拿元稹形容建安之后与宋齐之间文章面貌的说法用在杜甫身上,则他关辅时期(长安及秦州、同谷)多“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而成都(及梓州、阆州)、夔州、荆湘时期多“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我的看法是,杜甫的写作明显呈现出一个从外在世界逐渐趋于内心的倾向,而这种内倾化,在夔州乃达到一个极点。也就在这一特定的时刻,杜甫写作了极具现代主义精神风貌的伟大诗作。
T.S.艾略特曾有《诗的三种声音》一文,其中说道:“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或不对任何人说话;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说话,不管人多人少;第三种是诗人试图创造一个戏剧性人物在诗中说话;这时他说着话,却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只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对另一个虚构的人物可能说的话。” [3] 如果与文类联系起来,想必可以这样理解:第三种声音自然属于戏剧;第二种声音是对特定的对象说话,以信息的传达为要务,近于一般的散文;第一种声音是独语,本质上就是抒情诗。
测听杜甫不同时期的诗,叩问这三种声音,我们将别有所见。
二
就杜甫关辅时期的第一阶段作品而言,大约“现实主义”一词总是一个很好的概括。金启华《杜诗技巧论》说:
我们知道诗体对一个诗人来说,只是他反映现实的一种手段,而现实中重大的事件常常也决定诗人用什么体裁来描写它。杜甫的长安十年所见所闻,以及在安史乱中,他的颠沛流离,感时伤乱,这样重大的题材,这样沉重的心情,非长篇大作是容纳不下的。杜甫是以五、七古诗来描写这些事件。五、七古诗是杜甫在安史之乱中写作较多的诗体。譬如他的《北征》、《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等,都是在这一阶段中写的。 [4]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引范温《诗眼》云:
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麦熟”、“人生不相见”、《新安》、《石壕》、《潼关吏》、《新昏》、《垂老》、《无家别》、《夏日》、《夏夜叹》,皆全体作建安语,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颇多。 [5]
“今所存集”即指北宋王洙分类编次的《杜工部集》,其第一第二卷为古体诗,名篇特多。范温说得比金启华更到位:“其言直致而少对偶”,直道其语言特质;“早年皆学建安”,又明示其影响来源。
从声音上分析,杜甫在这一阶段所写的名作,只有《前出塞》、《后出塞》和《新婚别》是“创造一个戏剧性人物在诗中说话”的第三种声音,所占分量最轻。第一种声音的“永夜”“悲自语”是有的,但是,压倒性胜出的是第二种声音,即对或多或少的听众说话。那些酬赠之作,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赠卫八处士》等自然用了这种声音,另外有很多未在题中明确听众身份的诗作,由语气也分明可辨其说话方式,如“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丽人行》)“花门剺面请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王孙》)“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潼关吏》)都是明证。
这种声音高频率的出现,乃是因为这一阶段的写作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当然,我们现在说是历史事件,可在当时却是不折不扣的时事。杜诗素称“诗史”,那是从后人的角度来看待的。以我们今天熟悉的眼光看,杜甫的那些具有历史纪实性的诗作,更接近于新闻报道或时事述评。长安十年的困顿,安史乱中的流离,杜甫置身于社会、政治现实的旋涡中,目之所击,耳之所闻,那些军政大事遂一一形诸笔端。《兵车行》和《丽人行》就像是咸阳桥头与曲江水边的两个实地采访,《秋雨叹》之二则是天宝十二年秋长安霖灾的纪实,《三吏》、《三别》均为新闻速写,《留花门》与《塞芦子》则属于典型的时局分析,《洗兵马》呢?一篇辞气凝重、意气昂扬的社论。诗人忧世而伤时,其肠热,故不能不惊呼;其眼明,遂不得不直指。被外在世界全然裹挟的情思与行为,直接导致了杜甫此期的写作“全体作建安语”。而建安的诗风,前人的描述不正是“慷慨悲凉”,也就是元稹所谓“遒壮抑扬、冤哀悲离”吗?
杜甫这时期的两篇大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以个人行迹为线索,糅合国事与家事且叙且议,不专主写时事,却能够折射出历史的面目和时代的精神,其写作类型最接近于今日常见的较具个性化而更显真切感的记者系列专访一类。胡小石论《北征》道:“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有,亦当时诸家所不及(元结同调而体制未弘),为后来古文运动家以‘笔’代‘文’者开其先声。” [6] 他又将这一“散文化”的特点扩展开去而论及整个杜诗:“以诗描写时事的受历史化,以诗输入议论的受散文化,善于描写时事而融化散文风格的,不能不推子美为第一人!” [7] 而我们知道,更具有实用性质的散文,既然以信息的交流为首要目的,正是标准的第二种声音。尽管杜甫这两个长篇,总还是被称为“抒情诗”——“咏怀”不就是“抒情”吗?但是正如顾随所说的,“说‘咏怀五百字’是抒情诗,只是为了方便。这一首长诗实不止于抒情而已” [8] 。艾略特早已提醒过,一首诗中虽然会有一种声音在主导,但也交织着其他的声音:“我怀疑在任何一首真正的诗中只能够听得到一种声音。” [9]
第二阶段,即杜甫到成都之后的五年半里,诗风起了变化。草堂岁月优游而安详,诗人得以从容地雕章琢句,敷色研声,所以他的近体诗数量多而质量高,古体诗及其名篇却大幅度减少。峥嵘剑阁挡住了远方战争的喧嚣,除因蜀中兵变不得不流亡梓州和阆州的二十个月,他一般不必直接面对翻澜的时局频繁而急迫地作出反应了,即便有所反应,他也可以用律诗了,如为边警而作的《警急》、《王命》、《征夫》、《西山三首》等,都是以五律写时事,但毕竟不再是深度报道和分析。因为律诗语意的断续性造成字词的静止的聚集,不便于叙述,而长于“吟写性灵、流连光景”的写景和抒情,所以,迎来了久违了的和平生活的诗人,被明媚的春光、秋色、山容、水态深深地吸引,他将大千世界的“物色兼生意”刻画得既微妙又精准。试看下面这些诗句:
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为农》)
远鸥浮水静,轻燕受风斜。(《春归》)
仰蜂粘落絮,行蚁上枯梨。(《独酌》)
芹泥随燕嘴,花蕊上粉须。(《徐步》)
寒鱼依密藻,宿鹭起圆沙。(《草堂即事》)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
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屏迹二首》)
如果说“诗史”二字前一阶段的杜诗最足以当之的话,这一时期的作品就堪称“图经”了。不仅仅是山川形胜的图卷,也是草木花鸟的图谱。诗人欣然观察那些草木、鸟兽、虫鱼,将众生可爱的形态与神理一一摄入笔端。本来,在秦州短暂的安定时光,他已经工笔细描过一些花草。朱弁《风月堂诗话》指出:“至唐杜甫咏《蒹葭》云:‘体弱春苗早,丛长夜露多。’则未始求故实也。他如咏《薤》云:‘束比青刍色,圆齐玉箸头。’《黄粱》云:‘味合同金菊,香宜配绿葵。’则于体物外又有影写之功矣。” [10] 最后一句话很好地说明杜甫咏物诗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成都诗中更发挥到极致。所谓“影写”,无非“实录”。张戒《岁寒堂诗话》就《江头五咏》评道:
物类虽同,格韵不等。同是花也,而梅花与桃李异观。同是鸟也,而鹰隼与燕雀殊科。咏物者要当高得其格致韵味,下得其形似,各相称耳。杜子美多大言,然咏丁香、丽春、栀子、㶉鶒 、花鸭,字字实录而已,盖此意也。 [11]
可是,就描摹物态的静止的画面而言,最难分辨诗人是在用哪一种声音说话。看似属于“不对任何人说话”的“第一种声音”,但是又仿佛介于自言自语和与眼前事物虚拟的对话之间。好多情况下,我们都能发现诗人与那些个生灵亲切对话的口吻。以《江头五咏》为证:
晚堕兰麝中,休怀粉身念。(《丁香》)
无情移得汝,贵在映江波。(《栀子》)
如何贵此重,却怕有人知。(《丽春》)
且无鹰隼虑,留滞莫辞劳。(《㶉鶒 》)
不觉群心妒,体牵众眼惊。(《花鸭》)
若非你我对称,便是询问和告诫,见得出作者与对象的交流。同样例子还有:“今秋天地在,吾亦离殊方”(《双燕》);“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百舌》)。诗人真是尔汝群物,友于花鸟。不过这也说明草堂时期他并非绝对的孤独,也未尝感受到那孤独的力量。何况在成都和梓阆三地,杜甫的奉和酬赠之作格外多些。应该说,这一阶段杜甫的情思犹在外在的事物上,而未尝收视返听,沉潜入自己的内心。
在夔州,一个“林中才有地,峡外绝无天”的所在,海内交游零落,峡中宾从罕至,“巴蜀愁谁语”的状况到此乃臻于极点,他孤独到甚至写诗“示獠奴阿段”了。两年的大寂寞中,乡关何处?澄清何日?一种混合着喜悦与忧伤、回忆与期盼的情感,日复一日地百转千回于心头,杜甫于是写出了平生最辉煌的诗篇。饶宗颐说:
大凡诗思之源泉有二,非生于至动,即生于至静。至动者流离转徙之际,如秦州之作,此得于外界动荡之助力者也;至静者,独居深念之中,如夔州之作,此得于内在自我之体会者也。杜公对诗之见解,至五十一岁已臻成熟,自信力既增加,于诗益视为一生之事业,造次既于是,颠沛亦于是。
“不废江河万古流”,乾坤可毁,而诗永不可毁。宇宙一切气象,应由诗担当之,视诗为己分内事。诗,充塞于宇宙之间,舍诗之外别无趋向,别无行业,别无商量。此时此际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充心而发,充塞宇宙者,无非诗材。故老杜在夔州,几乎无物不可入诗,无题不可为诗,此其所以开千古未有之诗境也。 [12]
叶嘉莹说:
杜甫入夔,在大历元年,那是杜甫死前的四年。当时杜甫已经有五十五岁,既已阅尽世间一切盛衰之变,也已历尽人生一切艰苦之情,而且其所经历的种种世变与人情,又都已在内心中经过了长时期的涵容酝酿,在这些诗中,杜甫所表现的,已不再是像从前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质拙真率的呼号,也不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毫无假借的暴露,乃是把一切事物都加以综合酝酿后的一种艺术化了的情意。 [13]
二人的赞词,一说“得于内在自我之体会”,一说“在内心中经过了长时期的涵容酝酿”,都突出了一个“心”字。莫砺锋也一再强调,已经步入老年的杜甫,此时展开了全方位的回忆。他说:
诗为心声。夔州诗正是杜甫晚年的内心独白,由于这种独白融入了深广的历史意识和社会内容,所以它深沉、博大,余响不绝,千载以下的读者仍能从这些诗中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强烈震颤。 [14]
当然,诗人的心声,并不是社会思考与历史回忆的抽象说明,也不是外在于自身的客观物象的单纯摹写,而是心与境遇,物我相契,“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然后发而为诗。因为此时此际“峡束沧江起”的绝胜山水,尤其助成了文字的奇崛不凡。“穷老真无事,江山已定居”,在夔州的岁月,杜甫直可谓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15] 。与此前几个阶段的诗相比,我想可以说,昔者之诗为人,今者之诗为己;昔之作者“为生民立命”,今之作者“为天地立心”:
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上白帝城二首》)
谷虚云气薄,波乱日华迟。(《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
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晚登瀼上堂》)
鱼龙回夜水,星月动秋山。(《草阁》)
遗庙丹青落,空山草木长。(《武侯庙》)
天意存倾覆,神功接混茫。(《滟滪堆》)
楼光去日远,峡影入江深。(《白帝楼》)
水色含群动,朝光切太虚。(《瀼西寒望》)
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即事》)
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返照》)
江天漠漠鸟双去,风雨时时龙一吟。(《滟滪》)
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白帝》)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这是写实,同时更是写意。至此,合森罗之物象与郁勃之心境为一,已浑然不辨究竟是“雷雨蔚含蓄”还是胸中磅礴的意气,是“满峡重江水”还是心中澎湃的思潮了。
但是,对杜甫夔州时期的诗加以贬抑的,也颇有人在。贬抑者各有针对性,意见并不一致。比如,朱熹是很不满于杜甫的夔州之作的,他说:
人都说杜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鲁直一时固自有所见,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却说好,如矮人看戏耳。
杜子美晚年诗都不可晓。吕居仁尝言:诗字字要响。其晚年都哑了。不知是如何以为好否? [16]
我们会觉得奇怪,杜甫夔州诗最有代表性的七律,格高而声弘,怎么会附和说“都哑了”呢?朱熹没有明说都指哪些诗篇,但是据“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这一说法,和另一处提到的“杜诗初年诗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只意当处便押一个韵”,我们可以推测,原来他是偏指古体的那部分,具体想必是指《园人送瓜》、《园官送菜》、《课伐木》、《种莴苣》、《催宗文树鸡栅》、《驱竖子摘苍耳》一类作品,它们记述的都是一些家庭事务,实在不必那么郑重(意即频繁)地说,烦絮地说,所以朱熹才会深致不满。不止他一个,历代还有不少人都这么想。仇兆鳌就说过:“公夔州后诗,间有伤于繁絮者。” [17] 饶宗颐认为,诸篇乃杜甫“以诗垂训”,“以家常之琐事,寓庙谟之深算,非细心读之,不能见其真恳之意” [18] 。但“以诗垂训”,非说教而何?第一时期在安史乱前和乱中,诗人那么多论事名篇,着眼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及其插曲,其情则“沉郁”,其法则“顿挫”,其文字则“直致”而动人,不像夔州时期这些叙事之作,用了平缓的笔法,讲了平凡的事情,简直由“诗史”而沦为“起居注”之类,即使说它们能得《风》《骚》遗意,也已经用非所长了。
问题是声音的“烦絮”和“哑”。在夔州的两年,杜甫“形神寂寞甘辛苦”,他已然从动荡的外在世界返回到内心深处,远方的战声总是在他宛如一枚螺壳的心里激发出回响,但诗人自己已不再吹响这枚螺壳了。他沉浸在自己的冥思与独语中。朱熹所不满的那些诗为什么“都哑了”?因为它们的假想的听者(如行信、宗文等)其实并不具备听者的资格,结果第二种声音的诗到头来变成了一个孤独老人絮絮叨叨的说教。只有当他被回忆和思念摄去了魂魄而进入内心的世界,只有当他成为自己的声音最中意最体己的聆听者,这时,有一种音乐的东西起来了,时复低沉,偶尔喑哑,往往高昂,终至吞咽,以同一的形式,在不同的音域,回翔万状。
三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寒衣处处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画省香炉违伏枕,山楼粉堞隐悲笳。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
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马自轻肥。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迟。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蓬莱宫阙对南山,承露金茎霄汉间。西望瑶池降王母,东来紫气满函关。云移雉尾开宫扇,日绕龙鳞识圣颜。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
瞿唐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朱帘绣柱围黄鹄,锦缆牙樯起白鸥。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月夜,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阁峰阴入渼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佳人拾翠春相问,仙侣同舟晚更移。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
一千多年来,对于《秋兴》八首,读者几乎是一致的极口称赞,少有不满。明人王世贞和近人胡适,是极少数不满者的代表。“王元美谓其藻绣太过,肌肤太肥,造语牵率而情不接,结响凑合而意未调,如此诸篇,往往有之。” [19] 胡适则认为:“《秋兴八首》传诵后世,其实也都是一些难懂的诗谜。这种诗全无文学的价值,只是一些失败的诗顽艺儿而已。” [20] 胡适的意见影响很大,现代学者颇有人附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指《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为“直堕魔道”,“简直不通”。冯至在《杜甫传》里也说,《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等诗里,“宝贵的内容被铿锵的音节与华丽的词藻给蒙盖住了,使后来杜诗的读者不知有多少人只受到音节与词藻的迷惑与陶醉,翻来覆去地诵读,而不去追问:里边到底说了些什么?因此在解释上也发生分歧。” [21]
说《秋兴》八首“难懂”,“不通”,“在解释上发生分歧”,都有充分的理由。可是这些理由一旦遇上新的诗的现实,就立不住脚了。这一新的现实,完全不是胡适《白话文学史》始终提倡的“白话”诗。胡适心目中的“白话”,照他自己的解释是:“‘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 [22] 问题是,杜甫的《秋兴》八首,第一,不是戏台上的说白,也就是说,不是戏剧化的第三种声音,而是一种内倾的独语;第二,不是不加粉饰的话,而是如王世贞说得有些道理的,“藻绣太过”;第三,也不是明白晓畅的话,因为诗人现在并非在进行人际交流,也就不以自己“说得出”、旁人“听得懂”为务,他正在倾听自己的心声。艾略特在《诗的三种声音》中说道:
在一首既非说教,亦非叙述,而且也不由任何社会目的激活的诗中,诗人唯一关注的也许只是用诗——用他所有的文字的资源,包括其历史、内涵和音乐——来表达这一模糊的冲动。在他说出来之前,他不知道该如何去说;在他努力去说的过程之中,他不关心别人能不能理解。在这个阶段,他压根儿就不考虑其他人:他一心只想找到最恰当的字眼,或者说,错得最少的字眼。他不在乎别人听还是不听,也不在乎别人懂还是不懂。他怀着沉重的负担,不得解脱,除非把它生下来。或者,换个说法,他被鬼魅魇住了,却无能为力,因为那鬼魅一开始来的时候,就没有面目,没有名姓,什么都没有。他写的那些字眼,那首诗篇,就是他祛除鬼魅的形式。再换句话说,他烦了那么多神,不是为了与什么人交流,而是要从极度的难受中摆脱出来;而当他最终以恰当的方式将那些文字安排妥帖——或者他认为那是自己能够找到的最佳安排—他会感到有那么一阵,精疲力竭舒畅,如获大赦,以及说不出来的虚脱。 [23]
在胡适看来,“说得出,听得懂”是作诗的天经地义,可是他不知道,偏偏有人写诗“不在乎别人听还是不听,也不在乎别人懂还是不懂”。而且,可以更进一解的是,“难懂”与“不通”对于这类极具现代主义精神气质的诗来说,一点都不值得奇怪。胡适分明是拿对于古典诗语注重关系、秩序与目的的一般要求,来衡量《秋兴》这类其语言充满了断裂、褶皱与阴影(“造语牵率而情不接”)的作品,当然方枘圆凿,格格不入了。
《秋兴》八首,不是叙述,不是议论,甚至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抒情。那么它究竟是什么类型的诗呢?用艾略特的说法,“与其说是‘抒情诗’(lyric poetry),还不如说是‘冥想诗’(meditative verse)” [24] 。他是针对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的《杜伊诺哀歌》(Duino Elegies)和瓦雷里(Paul Valéry)的《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一类诗作而言的。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如瓦雷里的《海滨墓园》(Le Cimetière marin)、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的《在学童中间》(Among School Children),以及艾略特自己的《四首四重奏》(Four Quartets)。这些西方现代诗的经典作品,无不采用内省的视角,独语的姿态,在复活的记忆中再现过去的经验,混合着梦幻、印象、欲望、情思,以及瞬间的感觉。总之,全都是耽于冥想之作,是对于存在、死亡、自然、失去的时间等等的冥想。
现代主义的冥想诗,从根本上说,都属于自我中心的内在声音。正如艾略特所提醒的,那些第一种声音的诗“总的说来是我们这时代发展起来的”。格雷厄姆·霍夫(Graham Hough)说:
诗歌最充分的表现不是在宏伟的、而是在优雅的、狭窄的形式之中;不是在公开的言谈、而是在内心的交流之中;或许根本就不在交流之中。在给抒情诗所下的许多定义里,T.S.艾略特所下的定义是最有名的:抒情诗是诗人同自己谈话或不同任何人谈话的声音。它是内心的沉思,或是出自空中的声音,并不考虑任何可能的说话者或听话者。近一百年来,我们对诗的感觉,其核心正是这种观念。 [25]
瓦雷里《海滨墓园》写道:“多好的酬劳啊,经过了一番深思,/终得以放眼远眺神明的宁静。”而“宁静”与“深思”必沉潜入内心,以第一种声音说话:
瓦雷里的《海滨墓园》通篇源自一种内在声音,既不是作者的被叙述的独白,也不是说话者的意识,而是来自既在二者之外又被二者所包含的一个中介地带。正如用腹语法发出的声音一样,该诗并非出自特定说话者之口,却又属于诗本身的声音。它作为一种积淀而来,然而又是特殊化了的,远远超越冥想者的一种冥想。 [26]
这种深寂的冥想,内倾的独语,最易于造成旋律的音乐。无怪乎现代主义的冥想诗往往借助了音乐的手段。汤永宽论艾略特说:“诗人在四首四重奏中追溯一生经历,沉思并求索时间与永恒的关系,抒发他对现世的失望和来世的渺不可期,感叹信仰的需要和坚守的不易,语言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困难,甚而怀疑诗歌艺术在世间的意义等等。这些,作为中心主题,在各篇中反复呈现、交织、展开和深化,像贝多芬晚年创作的一组四重奏乐曲一样,‘以暗示和掠影,低回反复交织于一曲美丽动听、时而忧郁终而变为恬静的音乐之中’。” [27] 瓦雷里在谈及《海滨墓园》时也说:“我将尝试使诗人们投身于创造,以音乐家的形式,创造出对于同一主题的姿态万千的文本和丰富多彩的演义。”“诗歌要求或暗示出一个迥然不同的境界,一个类似于音乐的世界,一种各种声音的彼此关系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产生和流动着音乐的思维。” [28]
而与音乐的构造相联系的是,现代主义的冥想诗经常采取组诗的形式。如格雷厄姆·霍夫所指出的,大多数规模较宏大的现代诗作都是由各种抒情片段连缀的组诗构成,《杜伊诺哀歌》和《四首四重奏》这类作品,都是沿着个人经验的曲线,通过一种缓慢的、隐秘的心理发展过程而展开的,所以写一系列抒情诗,仿佛在记着灵魂的日记 [29] 。
艾略特关于现代主义的“冥想诗”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前提,使我们得以重新打量《秋兴》八首,辨析其文本特质,了解其生产过程,衡量其诗学价值。下面,我就从冥想的气质、内倾的声音、音乐的思维、心理的逻辑等四个方面,对《秋兴》八首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以阐发其与西方现代主义相通相应的诸多特色。
(一)冥想的气质。饶宗颐说杜甫夔州诗为“独居深念”之作,叶嘉莹说杜甫晚期七律表现出“触引深思默想的意象化”,皆把握到《秋兴》八首一类诗的独特的冥想气质。从题面上看,杜甫身在夔府,心系京华,因“老去才难尽”,遂“秋来兴甚长”(语出《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全篇几个关节点,就是第一首的“故园心”,第二首的“望京华”,与第四首的“有所思”。杜甫暮年“心”、“思”所在,小则为自身之出处,如“画省香炉”与“山楼粉堞”,“功名薄”、“心事违”与“多不贱”、“自轻肥”,“沧江岁晚”与“青琐朝班”,“彩笔气象”与“白头低垂”,处处形成今昔、人我的对比;大则为国家之盛衰,从第四首到第八首,无不极力渲染长安的富丽堂皇,而又收拾以衰飒残败的景象,总而言之,是“百年世事不胜悲”。当思绪的游丝偶触时,有“奉使虚随八月槎”之追怀严武,有“仙侣同舟晚更移”之忆念岑参,也有“匡衡抗疏功名薄”之感慨于疏救房琯获罪等;在意识的深层聚态里,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的,杜甫的思想有一反复出现的模式,如《秋兴》所展示的,可以宽泛地定义为文明与野蛮、秩序与混乱的对立,以及前者受后者侵陵而衰颓崩解的过程,最终归入中国宇宙观的永恒与变动之中 [30] 。事实上,《秋兴》八首宏大、规整而又精巧的写作本身也是这一思想模式的体现。借用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中论但丁的话说:
他善于从语言中提取出全部潜在的声韵、情感和感觉,在诗歌的不同层面中,全部的形式和属性中把握世界,以传达出这样一种感觉:世界是被组织起来的一个系统,一种秩序,一个各得其所的等级体系。 [31]
然而,将《秋兴》八首坐实为冥想型的诗,绝不意味着杜甫是在做抽象思考。由于西方诗人普遍具有的宗教情怀与哲学情结,我们前面提到的现代主义名家名篇,多少都会陷入对时间、信仰、自然、艺术等主题的思辨中,而杜甫的《秋兴》八首则完全是一种思想的感觉化,凡诸念想,皆托饱满可感的意象以进行,思考的抽象内容都寄于言外。这种意象不仅仅是诉诸视觉,也诉诸听觉,以及种种生理与心理感觉。于是,诗人的思想不唯有声音,有色彩,也有温度,有质感。《秋兴》八首,前四首有声,如波声、砧声(之一),猿声、笳声(之二),金鼓声、车马声(之四),而以静(之三)与寂寞(之四)为基调;后四首有色,如金茎、紫气、沧江、青琐(之五),素秋、朱帘、锦缆、黄鹄(之六),云黑、粉红(之七),紫阁、碧梧、拾翠、彩笔(之八),而以白头(之八)做收束 [32] 。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是那些切肤而钻心的内在感觉,举凡凋伤、萧森、阴、寒(之一),孤、虚、悲(之二),悲、寂寞、冷(之四),惊、晚(之五),愁、可怜(之六),虚、冷(之七),苦(之八)等等,都给现实或记忆中的事物染上浓重的主观色彩,并赋予诗人的冥想以鲜活的可感性。
(二)内倾的声音。我们总是将《秋兴》八首与《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相提并论,但是,首先是《诸将》五首,从本质上说乃是散文化的议论,属于标准的第二种声音。“将军且莫破愁颜!”“诸君何以答升平?”祈使句与疑问句的语气表明,这都是诗人对某些听众说话,不管这些听众是否真的能够听到。而《秋兴》八首则完全沉潜入自己的内心,是以第一种声音说话。这是一种从孤独开始的、迫于旁人无由窥测的心理压力的写作活动,与旨在传达思想、交流情感的一般书写差别很大,所以,诗中尽可以有那么多结构反常的句式(如“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与意义纷歧的表达(如“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因为诗人此刻是在内心的交流之中,甚至根本就不在交流之中。
然而,在喃喃吐露心声的八首诗中,似乎有一个颇觉突兀的语气偶尔介入了,这就是第二首末联的“请看石上藤萝月,已映洲前芦荻花”。“请看”二字,相当于乐府诗中的“君不见”,在一般情况下,一定是对某个在场的听者的提醒。但是,一如“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乃“独宿”者的“自语”,“请看”这一祈使语气,也是在一无“谁看”的条件下发出的。这又做何解释呢?对此,钱谦益注曰:“细思‘请看’二字,又更是不觉乍见、讶而叹之之词。” [33] 金圣叹则解曰:“请看’二字妙,意不在月色也。‘已’字妙,月上山头,已穿过藤萝照此洲前久矣,我适才得见也。” [34] 两人的注解都很到位,把握到了诗人当时的真实情状:他沉浸在回忆与思念中,神思恍惚,已浑然不觉——却突然感到——时光已悄然流逝。“请看”二字,非对他人而发,实是诗人在提醒自己。这是典型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
在第一种声音的冥想诗中,并非不可能出现别的人称,但这第二或第三人称并非是一个他者,而是自我声音的分裂。如艾略特《四首四重奏》之四《小吉丁》(Little Gidding),第一章与最后第五章都是“你”怎样怎样或没有怎样,但显然是指的诗人自己;第二章更出现一个“他”并与之相互问答,但诗人特别点明“我担负了一个双重角色”,“我还是我,但我知道我自己已经成了另一个人”。里尔克《杜伊诺哀歌》里的超验世界,瓦雷里《海滨墓园》中的绝对本质,都被诗人虚拟为“你”而展开了一系列对话,但绝不改变整首诗乃孤独的自语的实质。现代主义的冥想诗中,经常发生诗人扮演另一自我的情况。钱锺书曾用《西游记》中“以心问心,自家商量”这句话,来概括“一人独白而宛如两人对语”的主体声音分化现象 [35] 。这种分化往往表现为对话化,如米哈伊尔·巴赫金所说的:“对话性的冲突深入到内心,语言结构的各种细微成分中,相应地又深入到意识的各种成分中。” [36] 杜甫此刻的“请看石上藤萝月”,也许还加上“闻道长安似弈棋”,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了这种内心声音的分化与对话化。而杜甫同时的七律《白帝城最高楼》之末联“杖藜叹世者谁子?泣血迸空回白头”,更是这一自我问答的独语体具体而微的写照。
(三)音乐的思维。王夫之《唐诗评选》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章。” [37] 他已然视组诗为组曲、组乐。清高宗《唐宋诗醇》也说:“如此八首,根源二《雅》,继迹《骚》《辩》,思极深而不晦,情极哀而不伤,九曲回肠,三迭怨调,讽之足以感荡心灵,直使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 [38] “思极深”与“情极哀”,说明了其冥想气质,“九曲回肠,三迭怨调”,也揭示出其音乐构造。的确,如果将这组诗视为一部交响乐作品,是非常合式的。《秋兴》主旨其实平平,如毛奇龄所谓“八首意极浅,不过抚今追昔四字而已”,但四字还可以再分下去,即身在夔府之“抚今”,与心系长安之“追昔”。“追昔”好似乐曲的“正主题”(principal theme),“抚今”则是“副主题”(subordinate theme),两个主题在地位上几乎平等,性质上适成对比,而在八首诗即八个乐章(movement)中穿插回旋,交织而发展。沈德潜的《唐诗别裁》总评此诗:“曰巫峡,曰夔府,曰瞿塘,曰江楼、沧江、关塞,皆言身之所处;曰故国、故园,曰京华、长安、蓬莱、曲江、昆明、紫阁,皆言心之所思,此八诗中线索也。” [39] 这段话非常清晰地揭示了组诗中一正一副两个主题的发展。前三首身值夔府,分别是巫山巫峡(之一)、夔府孤城(之二)、山郭江楼(之三)的悲秋以自伤的副主题,却又时时逗出故园(之一)、京华(之二)、五陵(之三)的正主题;后五首中心移入长安,贯穿着怀乡恋阙的正主题,但是,关于故国长安(之四)、蓬莱宫(之五)、曲江头(之六)、昆明池(之七)、昆吾、御宿、渼陂(之八)的辉煌追忆,也处处有意再现了寂寞秋江(之四)、沧江岁晚(之五)、瞿塘峡口(之六)、关塞江湖(之七)的副主题。无论旋律是苍凉忧伤,还是高亢激越,都若断还续,无往不复,最后以“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今望苦低垂”一联,收缴“抚今”、“追昔”两个主题,给全部的乐曲画上休止符。
就像构成音乐作品的“乐段”(section)一样,《秋兴》八首以联为单位的细部,也经常充满音韵的重复、对比与呼应。高友工、梅祖麟曾用现代语言学的批评方法,对《秋兴》八首“通过音型的密度变化造成节奏上的抑扬顿挫”做了精细的分析,为瓦雷里所谓“文字的响度重于因果性”这一音乐型自我独白体诗的存在提供了一个经典范例。他们对这样的“乐段”分析很多,比如,“信宿渔人还泛泛,清秋燕子故飞飞”,两句音型完全一样,“信宿”、“清秋”都含齿音,且都是双声;“泛泛”、“飞飞”都是唇音,又都是叠字,而且互为双声,并加上前一句中的“日日”,三次重复一个结构,造成单调乏味之感。但紧接着的“匡衡抗疏功名薄”,“匡”、“抗”、“功”是一连三个kong音节的后腭音密集排列,有效地传达了一种激动不安的情绪。类似的例子还很多,而他俩也倾向于将这组诗看作“一部音乐作品” [40] 。捎带提一下:与这种音乐的有机构造不一样,《咏怀古迹》五首只是相似题材聚集在一起的“诗组”,而不是单一主题逐渐发展出来的“组诗”(Sequence),若论音乐思维,是不能与《秋兴》八首同样看待的。
(四)心理的逻辑。《秋兴》八首的文字繁复而多歧,充满了“因果与文法之颠倒与破坏”,这就造成胡适等人大不以为然的“不通”。问题是,一首七律的文字组织,先得受制于其固有的声音与词义的规定性;而一种内倾化的写作,还得受制于不以客观秩序为准则的心理逻辑。因为要顾及音义对仗,就有了“听猿实下三声泪,奉使虚随八月槎”式的“不通”,要讲“通”,就该写作“听猿三声实下泪”。因为要反映心理真实,也就有了“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式的“不通”,这是历来最遭人诟病的一联,但它们所复制或唤起的感觉和印象,却不是文从字顺的表达如“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所能比拟。叶嘉莹说:“这种句法,其安排组织全以感受之重点为主,而并不以文法之通顺为主,因此,其所予人者全属意象之感受,而并非理性之说明。” [41] 这也就是顾随所说的:“老杜的诗有时没讲儿,他就堆上这些字来让你自己生一个感觉。” [42] 所谓找一个“讲儿”,也就是用文法通顺的语言给予理性的说明,把一句看似不通的诗讲通了。
我想通过一个类似的变形实验来证明文字的错置造成的特殊效果。温庭筠《溪上行》诗曰:“雨湿蓼花千穗红。”这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而已,虽通顺而不免呆板。如果不考虑韵脚,我们不妨变动一下词序,成为“雨红千穗湿蓼花”,这样,感觉的层次一下子就出来了:先是雨水中朦胧的红色,然后是红色中隐约的千穗,最后是湿漉漉的蓼花。理性的整合之后会先因后果,但是真实的心理过程却是先果后因。杜甫类似的表达很多,如“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船》),“碧知湖外草,红见海东云”(《晴》),语法上的确讲不通,但它们依循的是别一种语法。瓦雷里在《诗与抽象思维》中说:
那些不同于普通话语的话语,即诗句,它们以奇怪的方式排列起来,除了符合它们将为自己制造的需要之外不符合任何需要;它们永远只谈论不在场的事物,或者内心深刻感受到的事物;它们是奇怪的话语,似乎不是由说出它们的人,而是由另一个人写成的,似乎不是对聆听它们的人,而是对另一个人说的。总之,这是语言中的语言。 [43]
可见,这种对语言正常秩序的破坏,为的正是满足一首诗本身“为自己制造的需要”。现代主义诗语往往晦涩难懂,因为诗人遵守的是感觉逻辑,反映的是心理真实,倒未必是刻意地要在表层语言上去追求震惊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正如艾略特在《玄学派诗人》中说的,由于我们的文明变得极其多样和复杂,作用于诗人精细的感受力上,也产生多样和复杂的结果,“诗人必须变得越来越全面,越来越隐曲,越来越间接,以图挤迫语言,必要时搅乱语言,去就他的意思” [44] 。这个解释很有道理,只不过他没有想到,在一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已经有形态那么复杂的文明生活,有感受那么精细的诗。
四
以《秋兴》八首为范例,我主要从冥想的气质、内倾的声音、音乐的思维、心理的逻辑等各个方面,探讨了杜甫晚年的诗与西方现代主义诗相通相应的特点。抛开语言上的表面差异,我们难道不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一千多年前的杜甫早已为里尔克、瓦雷里、艾略特等现代主义诗人导夫先路了吗?
为了方便论述,我只举出《秋兴》八首以与西方现代诗大师的名作相较,在梳理杜甫各阶段诗的逐渐内倾化过程时,也是从总体上把握的。在研读杜甫的场合,每当我们想从具体的现象归纳而上升为普遍的结论,就会有相龃龉的例证浮现出来加以反驳。比如,杜甫为追求感觉的真实,不理会正常的句法而错置字词的做法,早在长安的时候就已有过成功的尝试了。如七古《醉时歌》中“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两句诗,“檐雨”、“灯花”的通常表达,被诗人神乎其技地对调了两个字眼,就绝妙地反映了醉眼蒙眬之际镜头魔幻般的重叠与移位 [45] 。又比如,一般论者总是将《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和《诸将》五首相提并论,但真正与《秋兴》八首内省的气质接近的,是《曲江》、《登楼》、《登高》、《宿府》等七律,和《春望》、《旅夜书怀》、《江汉》等五律,它们都属于并非组诗形式和音乐规模的冥想之作。怎么来论杜甫都不可能完全,因为他多样而复杂到匪夷所思:最口语也最典故,最浅白也最晦涩,最朴素也最精工。
显然,杜诗的宇宙学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丰富、复杂、新颖、奇妙。宇文所安评价杜甫说:“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 [46] 这个标准大概等于钱锺书所指出的,体现了理性万殊的原则,从而主要表现为“繁复”、“深挚”、“实”的风格 [47] 。艾略特曾经盛赞维吉尔一劳永逸地穷竭了拉丁语的全部可能性,这既值得骄傲,也并非全然值得庆幸:
去打量一下维吉尔之后的拉丁诗,考虑一下后来的诗人在何种程度上生活与工作在他的伟大的阴影里:于是我们只照维吉尔设定的标准,对这些诗人褒或者贬——有时我们赞赏他们,为的是他们发现了某种新的变化,或者仅仅将文字来一番新的搭配,使得我们不无愉快地、模模糊糊地回想起那个久远的来头。 [48]
这个评价,完全适用于古汉语中的杜甫。如果不是胡适们的白话文运动,我们还得像晚清同光体诗人那样,在杜甫的阴影里讨生活。然而我们却又发现,杜甫的巨大影子竟然投射到了现代主义的帷幕上,以其冥想的音乐、精微的感受力和眩目的语言实验。古汉语中伟大的杜甫竟然是一位现代主义者?这个事实着实令我们惊讶。《孟子·万章下》曰: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找到其间的逻辑之必然:作为“诗圣”的杜甫,可谓兼“巧”与“力”于一身。他既然是“集大成者”,当然也一定是“圣之时者”。
【注释】
[1]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见《元稹集》(下册),卷五十六,第600页。
[2] 叶燮:《原诗》内篇上,见丁福保辑《清诗话》(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八年新一版,第569—570页。
[3] T.S.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p.4.
[4] 金启华:《杜甫诗论丛》,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68页。
[5]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版,第4页。
[6] 胡小石:《杜甫〈北征〉小笺》,见《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115页。
[7] 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见《胡小石论文集》,第113页。
[8] 顾随:《朗诵了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后写给中文系三年级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见《顾随全集》第二卷“著述卷”,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版,第128页。
[9] T.S.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p.23.
[10]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上,见《风月堂诗话 藏海诗话 巩溪诗话》,中华书局一九九○年版,第2页。
[11]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下,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上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第471页。
[12]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63、64页。
[13] 叶嘉莹:《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见所著《杜甫秋兴八首集说》,河北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46页。
[14]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第193页。
[15] 吴汝纶《十八家诗钞评注》于《驱竖子摘苍耳》诗后曰:“张云:峡中诸五言诗萧瑟暗淡,兼往往有入道语,大抵子美所至之地,精神意思能与其山川元气冥合,所以造极渊微,诸诗乃适与夔、巫萧瑟之境相副耳。”引自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上册),浙江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第1048页。当然不仅仅是古诗,宇文所安说:“夔州律诗中,有较多吟咏气候和一日的组成部分(黄昏,半夜)的诗,这些都被处理成宇宙力量交互作用的体现,融合了杜甫对阴阳象征、宇宙要素及代表造化的大江的兴趣。”见所著《盛唐诗》,贾晋华译,三联书店二○○四年版,第241页。
[1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八册),卷一百四十,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3326页。
[17] 仇兆鳖:《杜诗详注》(第三册),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1437页。
[18] 饶宗颐:《澄心论萃》,第66页。
[19]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四册),第1499页。
[20]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第212页。
[21] 冯至:《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年版,第124页。
[22]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7页。求之于杜甫夔州时期的诗,最符合胡适这三项标准的七律应该是《又呈吴郎》,通篇是语重心长的教导,然而王慎中认为“不成诗”,王闿运认为“叫花腔”。
[23] T.S.Eliot,The Three Voices of Poetry,p.18.
[24] 同上,p.17。
[25] 格雷厄姆·霍夫:《现代主义抒情诗》,见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第286页。
[26] 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陈永国、傅景用译,第364页。
[27] 艾略特:《情歌·荒原·四重奏》,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57 58页。
[28] 瓦雷里:《关于〈海滨墓园〉的创作》,见《瓦雷里诗歌全集》,葛雷、梁栋译,中国文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第287、288页。
[29] 格雷厄姆·霍夫:《现代主义抒情诗》,见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编《现代主义》,第293页。
[30] 宇文所安:《盛唐诗》,第251页。
[31] Italo Calvino,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16.
[32] 参见舒芜《谈〈秋兴八首〉》,见《舒芜文学评论选》,安徽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第37—38页。
[33] 钱谦益:《钱注杜诗》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一版,第506页。
[34] 金圣叹:《杜诗解》卷三,上海占籍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第179页。
[35] 钱锺书:《管锥编》(第一册),第338页。
[36] 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亚铃译,三联书店一九八八年版,第287页。
[37] 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王学太点校,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版,第179页。
[38]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诗醇》卷十七,光绪七年(一八八一)浙江巡抚谭钟麟重刊本第九册,第18b页。
[39]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版,第192页。
[40] 高友工、梅祖麟:《杜甫的〈秋兴〉——语言学批评的实践》,见所著《唐诗的魅力》,李世耀译,第31页。
[41]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第50页。
[42] 顾随:《驼庵诗话》,见《顾随全集》第三卷“讲录卷”,河北教育出社版二○○一年版,第97页。
[43] 瓦雷里:《诗与抽象思维》,见《文艺杂谈》,段映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二○○二年版第287页。
[44] T.S.Eliot,“The Metaphysical Poets”,in Selected Essays,1917—1932(London:Faber &Faber,1932),p.275
[45] 南朝人常用“檐花”一词,但杨慎《词品》卷二所说的更有道理:“杜诗‘灯前细雨檐花落’,注谓檐下之花,恐非。盖谓檐前雨映灯花如花尔。后人不知,或改作‘檐前细雨灯花落’,则直致无味矣。”见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一册),中华书局一九八六年版,第458页。
[46] 宇文所安:《盛唐诗》,第209页。
[47] 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见《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第8—25页。
[48] T.S Eliot,What isa Classic(London:Faber & Faber,1944),p.23.
文/江弱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