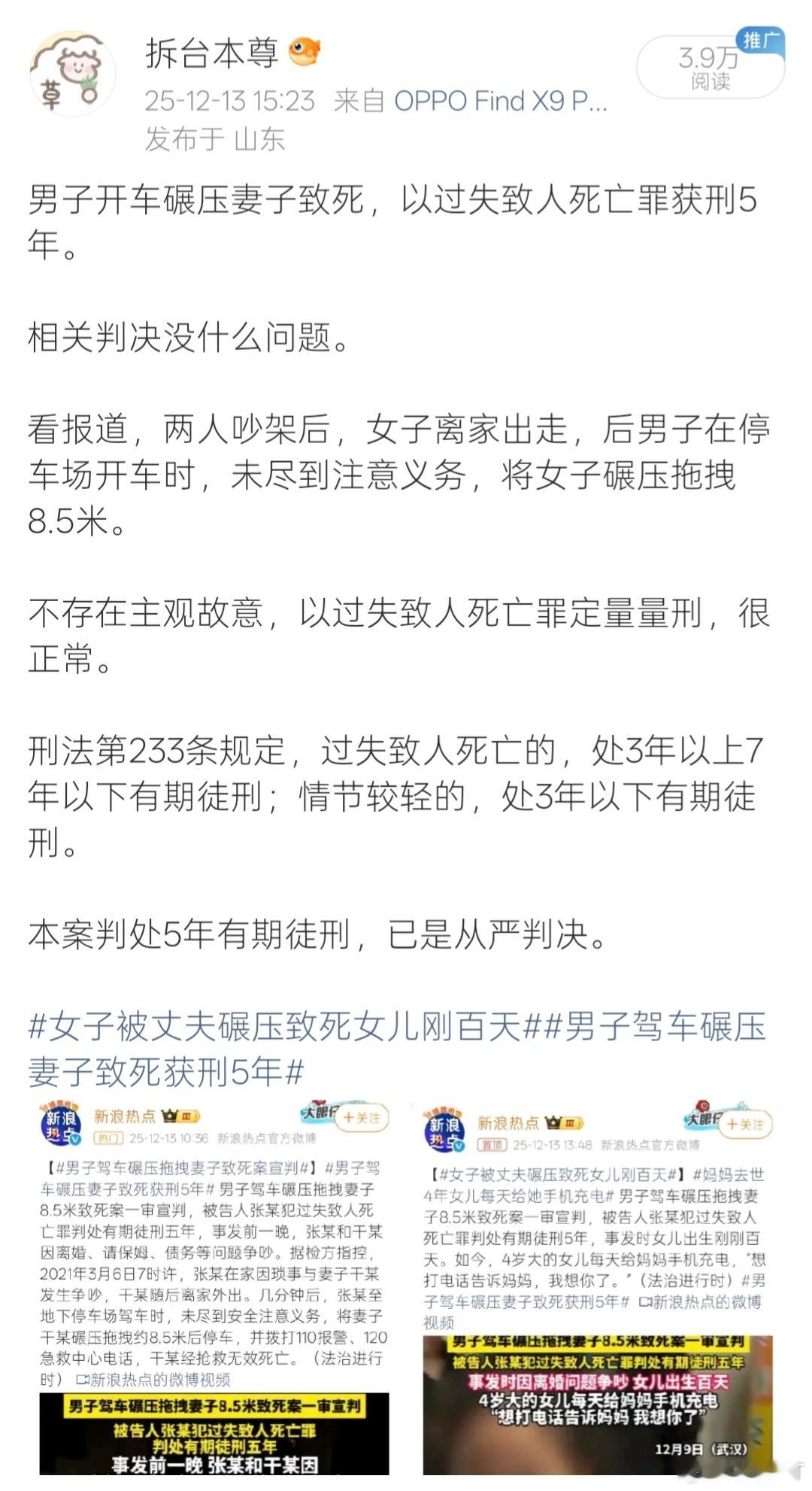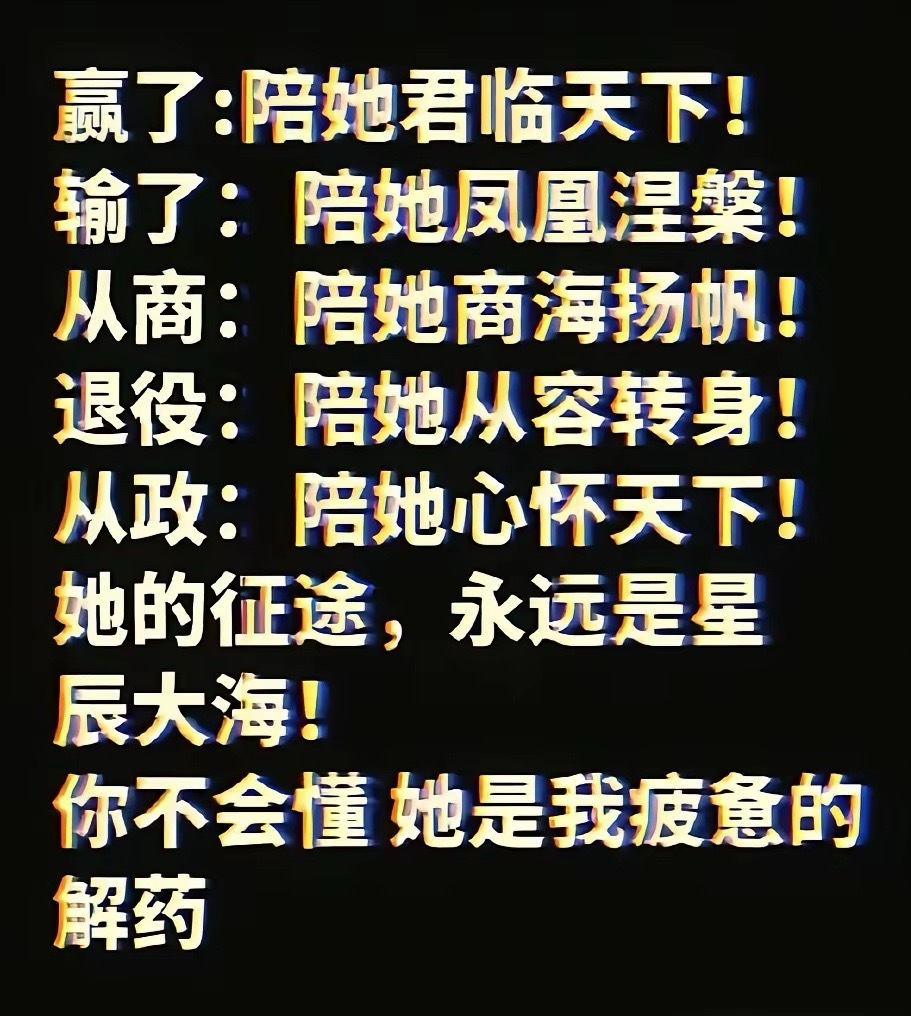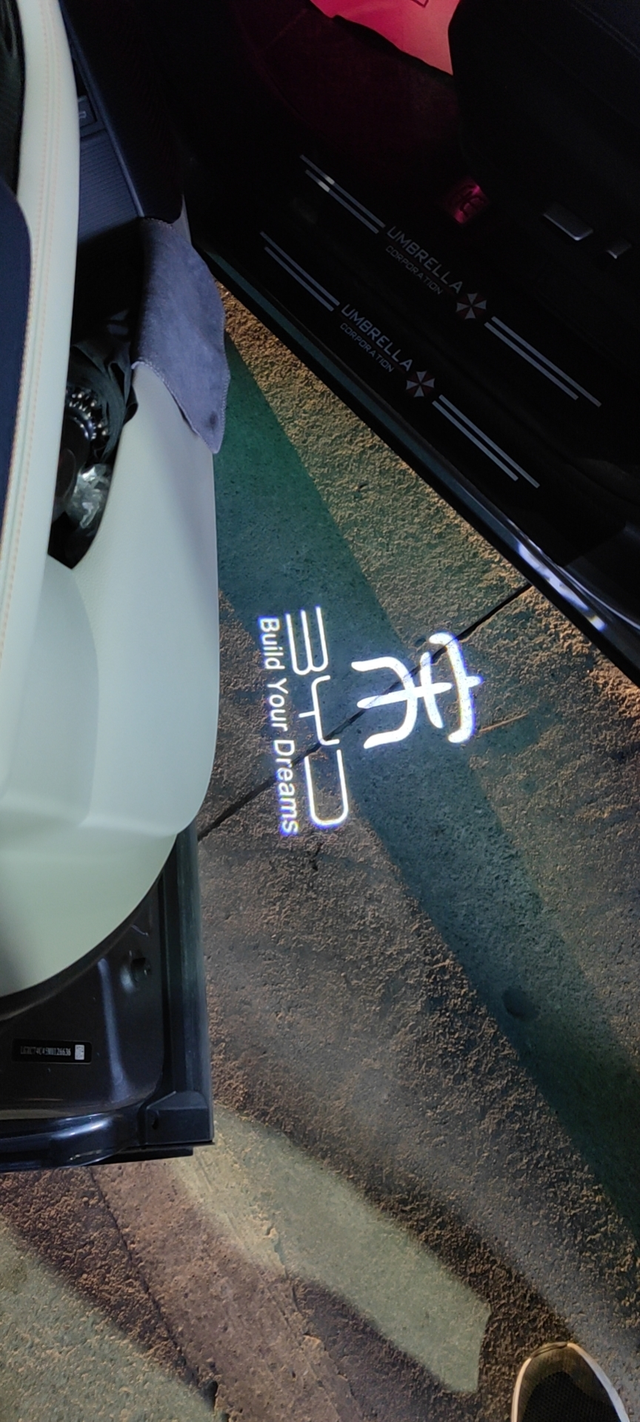亲戚过了三代,情分确实淡了。我妈这边,姨妈还在,逢年过节会送些东西、给点钱。表哥基本不联系,表姐因为热情投缘,常发微信走得近,可总觉得姨妈不在了,关系怕是也要远了。去世那天,表姐抱着我哭:“以后回娘家,再也没人在门口等我了。”出殡时,表哥扶着表姐,动作生涩却很稳,像小时候姨妈不在家,他笨拙地给发烧的表姐喂药。送葬的路上,表姐忽然说:“还记得那年暴雨,咱家屋顶漏了,你哥爬上去修,摔下来蹭掉块皮,却举着修好的瓦片笑‘看,不漏了’。”表哥没说话,眼圈却红了。 亲戚过三代,情分是会淡的。我妈总说“姨妈在,这门亲戚就还热乎”,她没骗人——姨妈在世时,逢年过节的礼盒堆在门口,表姐的微信消息总带着笑脸,表哥虽不常说话,也会托姨妈捎来他种的香椿。可我心里藏着个小疙瘩:要是姨妈不在了,这层热乎气,会不会就散了? 散的那天来得比想的早。殡仪馆的冷气裹着消毒水味,表姐扑进我怀里,肩膀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以后回娘家,再也没人坐在门口藤椅上,看见我电动车灯就喊‘囡囡回来啦’。”藤椅是姨妈的老伙计,竹篾磨得发亮,夏天总搭着块蓝布巾,她就坐在那儿等表姐,一等就是二十年。 出殡的队伍慢慢挪,表哥走在表姐左边,手虚虚扶着她胳膊。动作生涩得像初学走路的孩子,却稳——没让表姐晃一下。我忽然想起小时候,姨妈去邻村喝喜酒,表姐半夜发烧,表哥蹲在床边,用凉毛巾擦她额头,药片子掰成小块,混着糖水喂,洒了半勺子,急得脸通红,却还是固执地说“再吃一口,吃完就不难受了”。 送葬的路太长,表姐盯着车窗外掠过的白杨树,忽然开口:“你还记得十七岁那年暴雨吗?”雨点子砸在瓦片上像擂鼓,屋顶漏得像筛子,表哥踩着摇摇晃晃的木梯爬上去,脚下一滑,整个人摔在房檐上,胳膊肘蹭掉块皮,血珠珠渗出来,他却举着补好的青瓦片冲屋里喊“看,不漏了”——声音亮得像没摔过似的。 表哥一直没说话,直到表姐说到“摔下来蹭掉块皮”,他忽然偏过头,盯着车窗上的雨痕。那双眼平时总没什么表情,此刻红得像浸了水的樱桃,喉结滚了滚,还是没出声。 血缘这东西,真的会随着长辈的离开就淡了吗?我从前总怕,怕姨妈不在,表姐的微信会慢慢沉默,表哥的香椿再也送不到门口。可看着表哥扶着表姐的手,看着他红透的眼圈,忽然明白:有些情分不是系在长辈身上的线,是埋在岁月里的根——是藤椅上的蓝布巾,是漏雨的屋顶,是摔破胳膊还举着瓦片笑的少年,是那些没说出口却刻在骨头上的“我记得”。 车快到墓地时,表姐轻轻挣开表哥的手,从包里摸出块糖,剥开糖纸递过去。是姨妈生前最爱买的水果糖,甜得发腻。表哥接过来,含进嘴里,腮帮微微鼓着,像个被喂糖的孩子。 风吹过,墓地里的松柏沙沙响。我忽然想起姨妈常说的那句话:“亲戚亲戚,亲的不是‘戚’字,是‘亲’字里藏着的那些年——你扶我一把,我记你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