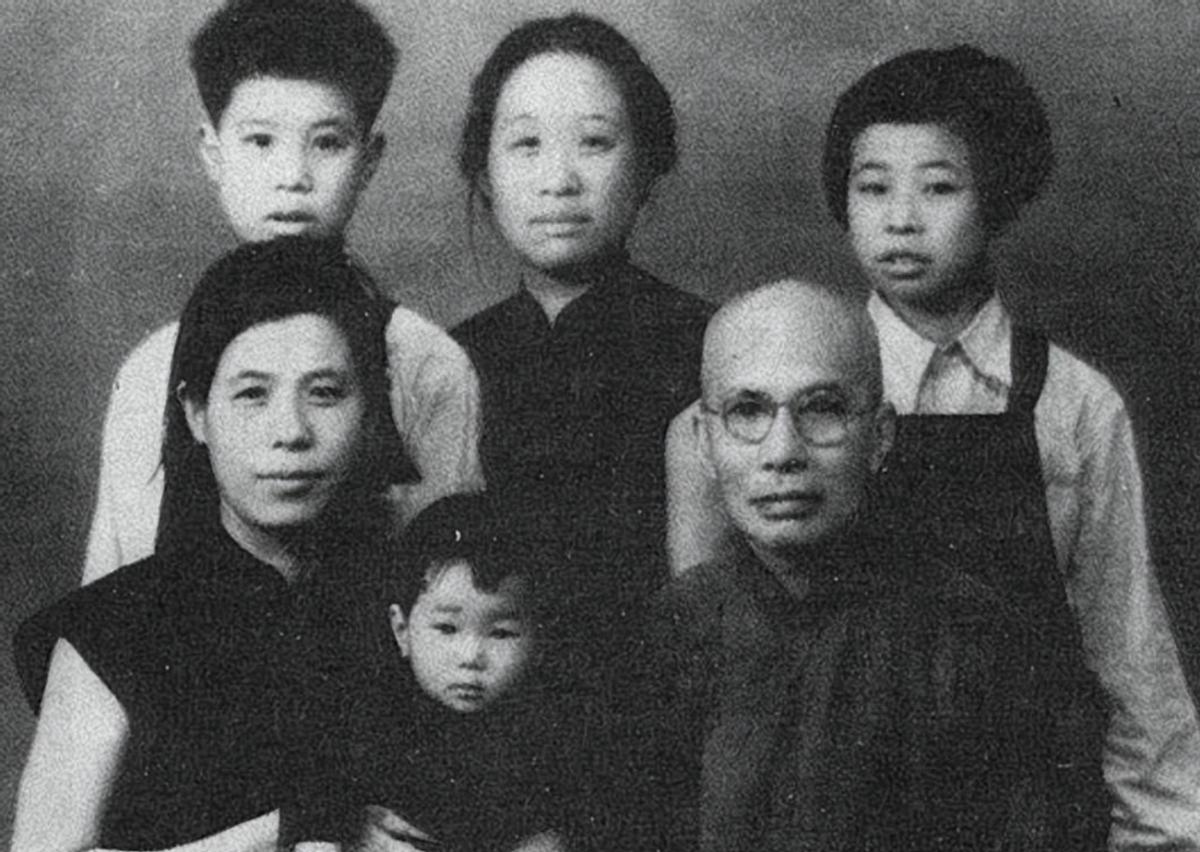新中国的八次国葬: 第一次,1976年,周总理,享年78岁! 第二次,1976年,朱德总司令,享年90岁! 第三次,1976年,毛主席,享年83岁! 第四次,1981年,宋庆龄先生,享年88岁! 第五次,1997年,小平同志,享年93岁! 第六次,2006年,霍英东先生,享年84岁! 第七次,2007年,庄世平先生,享年97岁。 第八次,2022年,江泽民同志,享年96岁! 八次国葬,七位男性,只有这一场,是为一位女性而鸣钟。宋庆龄的国葬,注定不一样。 宋庆龄的一生,到这一刻被压缩成这样两样东西,被送回她出生的城市,也送回宋家早年买下的那块墓地。 墓穴不大,几平方米,安静得很,没有什么排场,却成了整片陵园里最让人绕不开的一处。 那年春天还在北京。 五月八日下午,她还是去了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人坐在轮椅上,博士服披在肩头,脸色发白,眼神却亮。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要授她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持。 医生建议只做录音,她摇头,坚持亲临。轮椅推到麦克风前,她用外语讲了将近二十分钟,声音不高,节奏却稳。台下掌声响过好几次。 那天留下的照片,后来再看,大家都懂,那其实已经是她最后一次站在公众视野里。 回到驻地后,她再没有离开过二楼。 北京医院把监护仪、输液架、各种设备一件件搬上去,原本陈设简单的房间被机械和药瓶围满。 外头的大客厅却比从前更热闹,中央、人大、国务院派来的联络员轮值而来,记者、警卫交替守着,长沙发坐满了人,地毯上也坐着。 那段日子里,一件看似细碎却很关键的事情被提了出来,她的确切出生日期始终说法不一,没有她亲手确认的版本。英文秘书只记得,她说过和毛主席年纪相近,再细问就笑而不答。 最后托人查到美国学校的学生档案,一八九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这个日子才正式定下。 病情走得很急。北京医院的专家、老中医轮番会诊,一位解放军军医专程来献血。 五月十四日晚她高烧不退,第二天早上稍微退下一点,王光美来到床前。 话绕到几十年前的一桩旧事。 一九五七年,她曾在上海提出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因各种考虑搁了下来。病床前再问,她轻轻点头。 值班电话被打到胡耀邦那边,当天下午,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了接收她为中共党员的决定。傍晚,中组部与全国人大负责人到床前宣布结果。明白规矩的人都清楚,这一步走完,许多事情便有了分量和依据。 第二天,她又多了一个身份。 五月十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从一九四九年前留在上海面对险境,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国家副主席,再到晚年几十年投身和平与儿童福利,这个称号像是在历史上补齐了最后一行落款。 随之而来的,是连续不断的病情公告。电台每天播报,报纸醒目刊出。 慰问信、补品、中药、各种偏方不断寄到驻地。六一临近,许多孩子寄来红领巾和画满太阳的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祝愿。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病情通报中出现了“病危”二字。 晚上,小会客厅的电视还亮着,楼上的警铃突然响起,那是床头按钮直接连着的。 冲上二楼时,医生已经围在床前。 主管治疗的吴蔚然站在床脚,看完仪器,又看了一眼病人,缓缓说不必再抢救了,问床头闹钟准不准。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让人把指针拨停在二十点十八分,这个时间被记录下来,也被写进之后所有正式文件。 遗体被移到一楼小会客厅,布置成告别的场所。 中央领导陆续到来,鞠躬、停步、离开。最初的秩序有些杂乱,电视工作者提出按顺序重走一遍,大家便照做了。 灯光、花圈、白布与快门声交织在一起,构成那几年少有的一次公开送别。 六月三日,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下半旗,娱乐活动一律暂停。 主席台正中悬挂着宋庆龄的遗像,前方摆放着覆盖党旗的骨灰盒。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说她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战士,也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又提到一九四一年她到重庆,与马海德、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一起为中国抗战奔走。 会场里不少老人听到这些名字,轻轻点头,像是勾起了很远的记忆。 六月四日,国葬转到上海。 北京西郊机场,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站在跑道边送行,护送骨灰返沪的,是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还有从上海赶来迎灵的胡立教。 专机落在虹桥后,车队径直驶向西郊万国公墓。 宋家早年买下八穴墓地,本就为一家人留好了归宿。宋庆龄生前说过,上海是出生地,是她从事事业时间最长的地方,孙中山的故居也在那里,父母也在那里,总归要回来。 车子缓缓驶进陵园时,战士抱着骨灰盒走上石阶,石缝中冒出细小青草。 礼毕,骨灰和那袋金属残件一同安放入穴,大理石板合上,红旗收起,风从树隙间吹过,掠过新刻的名字,也掠过旁边被岁月磨淡的旧碑。 送行的人陆续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半旗缓缓升起又落下,绳索还在微微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