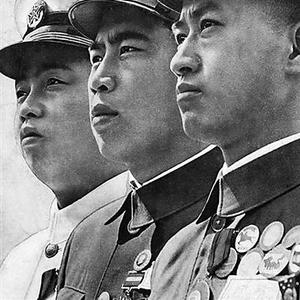[太阳]1949年12月,国民党上将孙震带着五百两黄金飞逃台湾,临走时将部队指挥权交给了侄子孙元良。孙元良召见手下开会,叫嚣说:“打,必须打下去。”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孙元良) 1949年12月,川鄂边区成了国民党残余势力负隅顽抗的最后几个据点之一,可时任川鄂边区绥靖主任的国民党上将孙震,心里打的根本不是“死守”的主意,而是怎么给自己留条后路。 眼看着解放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孙震心里跟明镜似的,败局已定,再留在大陆就是死路一条。他决定把这个快要散架的烂摊子甩给侄子,自己拍拍屁股准备跑路。 临走前,他表面上把川鄂边区绥靖署的事务交给副主任董宋珩打理,暗地里却把实际军事指挥权塞给了孙元良,还特意把蒋介石划拨来的“国防部”警卫部队划到孙元良的十六兵团麾下。 孙震逃到台湾后,孙元良以十六兵团司令官的身份正式接管了川鄂边区的残余部队,野心勃勃的他甚至想把名义上的上级董宋珩挤走,自己一人独揽军政大权。 那年12月19日,退守成都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胡宗南发来急电,命令孙元良带着部队赶往成都集结,和其他残余部队一起“固守川西”。 接到命令后,孙元良立马召集手下将领们开军事会议,可会议室里满是悲观情绪,不少将领都打心底里抵触这个命令。孙元良见状猛地一拍桌子,态度强硬地喊着:“打,必须打下去!” 孙元良非要执行胡宗南的命令,把部队往毫无胜算的战场上推。可他的强硬根本没人买账,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曾甦元看得明白,这时候往成都集结,就是去当胡宗南的“炮灰”,纯粹是自投罗网。他提议把部队撤到广汉一带,靠着当地的地形先休整一阵子。 41军军长张宣武则提出了个折中办法,建议去什邡——这里既能靠着周边的据点布防,真要是局势再坏下去,也能往西南方向突围,算是进可攻退可守。 孙元良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但看着将领们一个个面露难色,也清楚要是强行下令,搞不好部队就哗变了,没办法,只能不甘心地同意了去什邡的方案。 就在孙元良带着部队慢悠悠地往什邡移动的时候,一场秘密的起义计划正在悄悄酝酿。 董宋珩早就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溃败感到失望透顶,之前就通过秘密渠道联系上了中共地下党,表达了想要起义投诚的想法。 而和董宋珩关系要好的曾甦元,在41军、47军里根基深、威望高,两个人一拍即合,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带着部队脱离国民党的控制,投向人民的怀抱。 那年12月21日,曾甦元带着先头部队率先赶到什邡,一进城就立刻和城里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飞快地控制了城区的关键据点,还下令把城门紧紧关上,布置好了防御工事。 等孙元良带着60师等主力部队赶到什邡城下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傻了眼:城门紧闭,守城的部队严阵以待,城楼上的士兵甚至架起了机枪,一副随时要开战的样子。 孙元良气得火冒三丈,正想问为什么不开城门,一封董宋珩的亲笔信从城楼上射了下来。 信里说得明明白白,董宋珩已经决定带着川鄂边区绥靖署和十六兵团的部分部队通电起义,还劝孙元良认清形势,赶紧带着部队撤走,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手里攥着这封劝降信,孙元良瞬间陷入了两难境地。思来想去,他只能忍下这口气,带着部队灰溜溜地撤了回去。 回到驻地后,他还是不死心,琢磨着带着60师往懋功方向突围,要么就一路往南逃到云南,甚至想过穿越边境跑到缅甸,继续负隅顽抗。 可他的逃跑计划刚一提出来,就遭到了60师官兵们的一致反对。打了这么久的仗,士兵们早就厌倦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谁也不想再为国民党政权卖命了。 这下子,孙元良彻底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成了孤家寡人。没办法,他只能乔装打扮一番,孤身一人逃到成都郊区的农户家里躲了起来。 直到1950年1月,在旧部的暗中帮助下,他才辗转逃到香港,后来又从香港去了台湾,和叔父孙震汇合。 1949年12月25日,在董宋珩、曾甦元的带领下,川鄂边区绥靖署以及十六兵团的41军、47军等部队在什邡正式通电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彻底瓦解了国民党在川鄂边区的残余势力,为西南地区的解放扫除了一大障碍。起义后的部队很快被编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投入到地方建设和清剿残余土匪的工作中。 随着十六兵团的起义,成都周边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彻底没了主心骨,乱作一团,再也没法组织起有效的抵抗。那年12月30日,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成都市区,受到当地群众热烈欢迎。 成都的解放,标志着西南地区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基本被肃清,中国大陆的解放战争也就此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其中,什邡起义的正义选择,为这段动荡的历史增添了一抹温暖的光明色彩,也让人们看到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