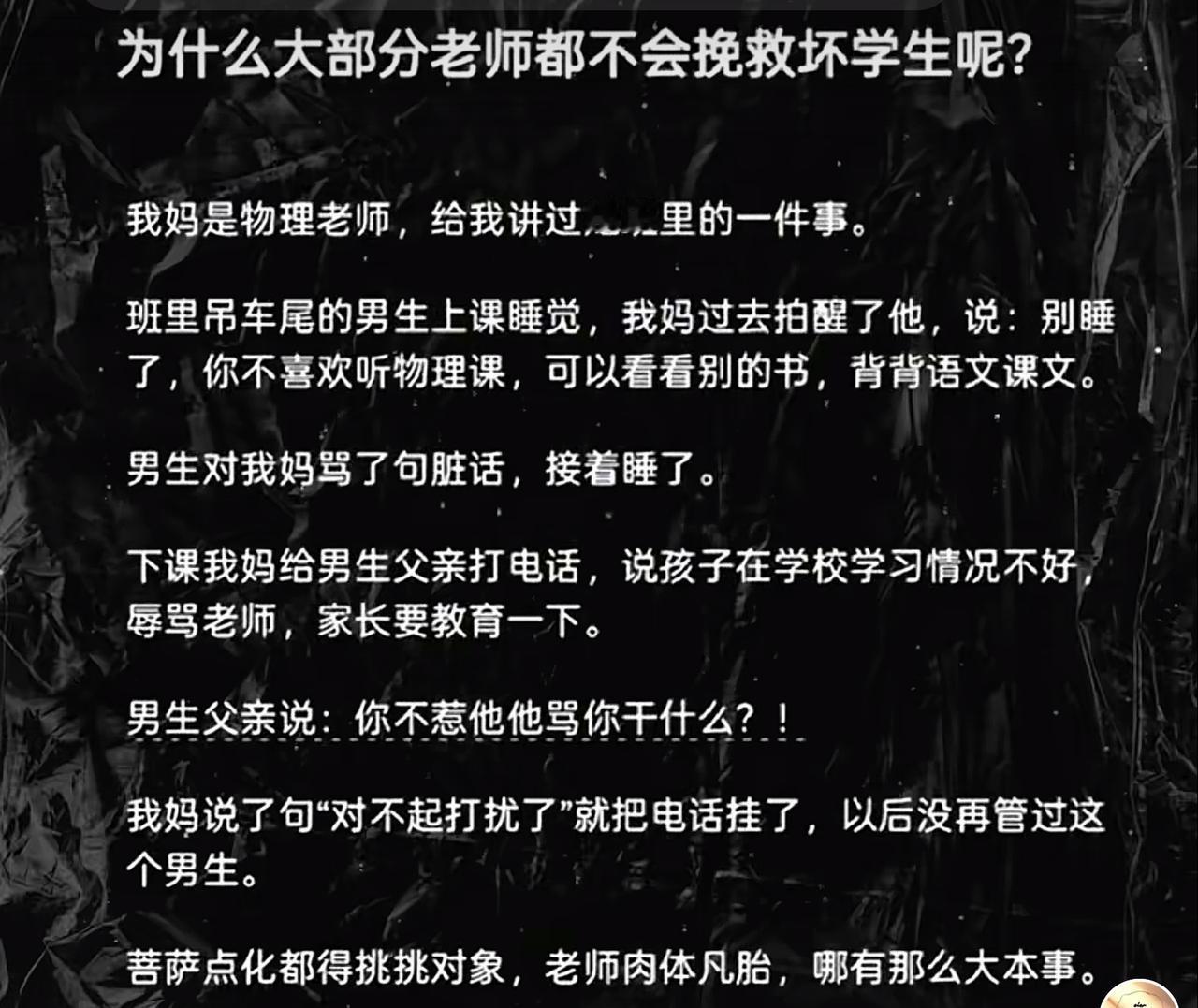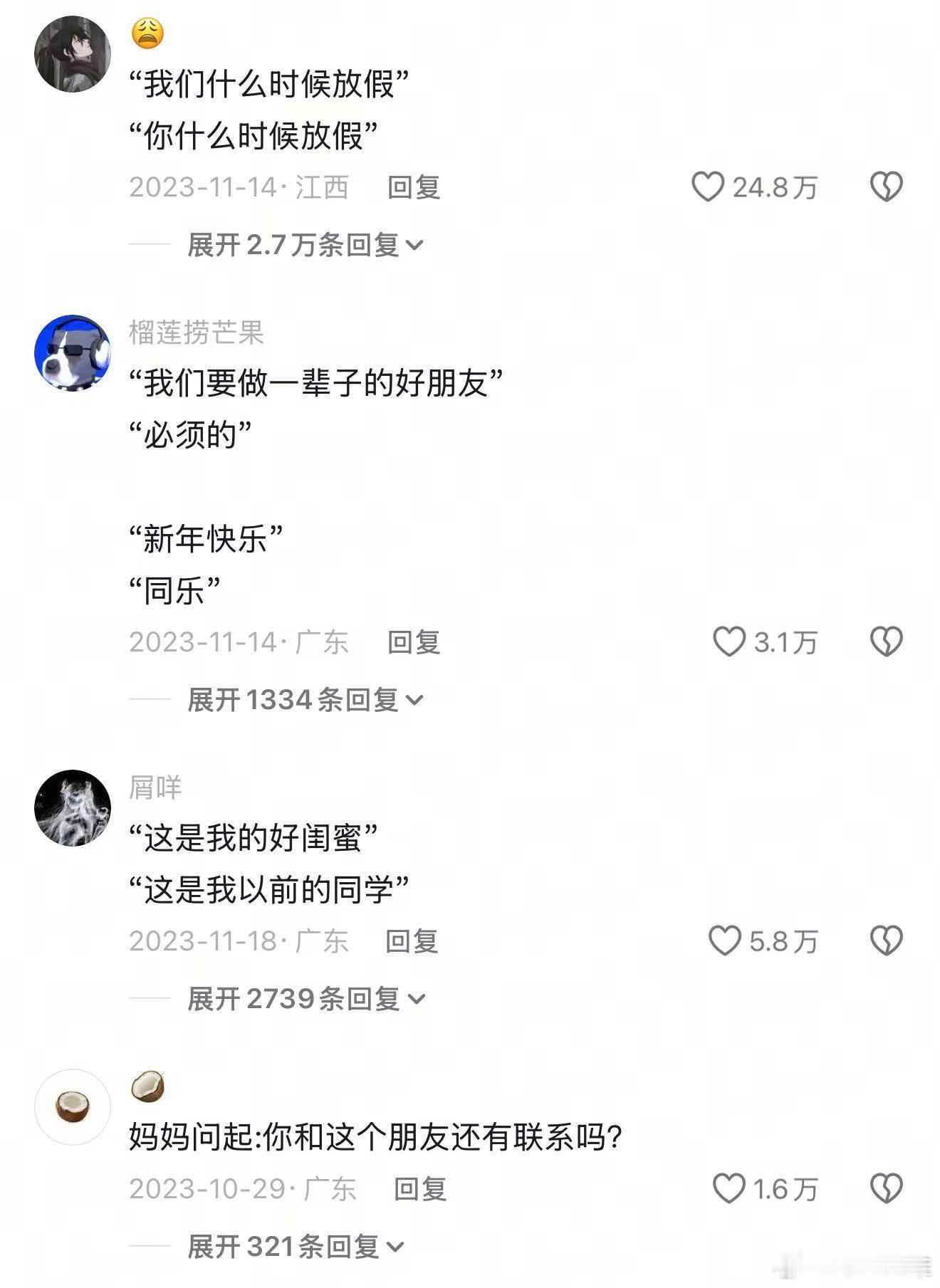时间如梭,我已过“耳顺”的年华了,按孔夫子所说,此时应进一步懂得在道德以上的价值了。

幼时我很孤单,脾气暴躁,幸好有外祖父轼公徐诵明,他是一位儒者、教育家,懂得疏比堵好、无为而治、自由发展。在他的疼爱与鼓励下,我执笔从艺,一晃五十年了,其间,无一日虚度,勤耕墨海,惜墨如金,思想归朴,返本求新,深得笔墨“厚爱”。在艺术人生的旅途中虽无万般坎坷,也颇跌宕起伏,但我始终未改变自己的初衷。
人生是有境界的,艺术亦如此。几十年的笔墨生涯,我就像一只不断线的风筝飞翔在天空,那里有四时朝暮、日月星辰,也有雷电交加、暴风骤雨,但它有时低飞,有时却冲破云雾不知飞向何方。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说得好:“在于墨海中立定精神,笔锋下决出生活,尺幅上换去毛骨,混沌里放出光明。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这里的“我”就是指那只自由飞翔的风筝,它的一端牢牢地系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上。在那里,“虚与实”“阴与阳”“有与无”得到了升华的结晶。如《中庸》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这是一种天地的和谐,它不仅指人类社会,也渗透全宇宙,形成太和之势。天地乾坤浩瀚博大,它保有至高的和谐,这就是中国人追求的大吉大利。我正是在此间获得灵感,顿悟命运。

友人们感叹社会世俗功利,我倒不以为然,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华古老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论将再次屹立于世界东方,宣扬和合文化的责任将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中华文化赋予的智慧,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贤就站在宇宙观的高度着眼于世界的治理与和平,关注天下苍生的命运,使其具有一种普遍价值。不分古今、不分中外,内外两忘,“至大无外,谓之大一”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人生境界中得到升华。身修一己,非最终之目的,能关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得到宇宙世界的文明,才是根本。我在二十多年前创作《阳光与和谐的梦想》行为艺术,致力建立中国抽象绘画流派,探索中国式抽象逻辑思维语言,都是在古老的“六艺”之学的感召下走向世界,并以中国人谦和、包容、仁义的态度,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文明对话的基点,以文会友。至今回味起来仿佛仍未结束,它们已超越所谓作品的概念,成为我生活和人生态度的一部分。

象山公顿悟后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真不知还有谁会对宇宙世界有如此深刻的理解。“剥极必复,否极泰来。”纵观世事,笔在砚中。“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人往往需要更多的表白,才能归入潜默,不知此时我的人生画境是否正在其中……

让二十四节气成为启发理解传统文化的钥匙
蔡涛
看徐冬冬先生的二十四节气系列作品,宛如置身于诗意与东方哲思的秘境,游弋于色彩与肌理构筑的空间,“构建自我意象”的闸门被轻易地打开。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对传统文化人云亦云的复刻,而是全新视角的解析、心灵独白式的吟诵。
二十四节气对每个中国人来说,从来不是日历上冰冷的符号——它是小时候老人们念叨的“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是故乡田埂上随“春分”回暖的新绿,是“霜降”时节树林中的红叶落霞,是刻在中国人基因里对自然的敬畏与共情。然而正是这种熟悉,让那些“春芽、夏荷、秋月、冬雪”之类的具体形象不能轻易打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南方人的青团、北方人的烙饼……华夏文化的博大,非凡物俗景所能象征,平常艺术家也难绘其精髓。徐冬冬独树一帜,开辟抽象艺术的新路,从宏观的视角,用多彩的语言呈现中国人骨血里的“顺时而为”的智慧,把我们引向文脉传承与创新、古老风俗与文化融合的思考。
对徐冬冬作品的解读应该是个人化的。对我而言,从他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滋润与干涸、生长与枯萎的轮回,昼夜均分、冷暖平衡的辩证。画中自然铺陈的颜料,就像山河风景中自由生长的生物,干枯的色块象征着沧海桑田的变迁,笔触的颤动演绎出生命更迭的节奏……我个人认为这些概念很难以具象形式去表达。
徐冬冬在抽象绘画的框架中融入东方水墨氤氲的精神,空灵中不失光影交织的细腻丰满。我意识到,他笔下的节气,早已跳出了“东方独有的风景”,而是一种“跨文明的交融”。他没将二十四节气作为“东方文化的专享符号”,而是人类观察自然、对话生命的“共同语言”。而徐冬冬的作品,正是把这种“语言”翻译成了可视的、抽象的艺术形式,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能读懂“江花红胜火”的诗意,理解“春种秋收,从容成熟,终点即起点”的东方哲理。
其实,中国文化中向来不缺少抽象。我们崇敬“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气度,向往不见项背之鲲鹏的逍遥;我们欣赏柳永“有画难描雅态,无花可比芳容”的意境,因为他没写出具体的眉目,却能调出每个人心中的美人。虽说中国美术史中没有专门的抽象流派,但从半坡陶器上的几何纹,到青铜器上的回纹饰,再到写实中走出的写意,以及后来的泼墨,都闪现着中华艺术家的抽象灵光。今天,我们终于看到徐冬冬用纯粹的抽象语言,去表达他对传统文化的个性化诠释,着实令人欣慰。
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艺术家最珍贵的品质就是创新。徐冬冬用丙烯、装置之类现代语言讲述二十四节气的故事,就像小提琴演奏的《梁祝》,让人感受到时空穿越般的愉悦。如果说徐冬冬的作品是音乐,我想应该特别适合恩雅、马友友去演奏,那种和谐与空灵的风格,荡气回肠的气韵,最能打动心灵。
当前,我们总在讨论“如何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徐冬冬用作品告诉我们:真正的文化传播,不是把“我们的东西”推给别人,而是找到“人类共通的情感”,再用自己的文化语言去表达。徐冬冬没有去解释“小满为什么是‘小得盈满’”,而是用肌理和色彩,让人去体会“知足常乐”的智慧;他没有去科普“白露为什么要‘收清露’”,而是用光与影的交错,让人能感受“对自然馈赠的珍视”。这种“只意会不言传的表达”,比任何理论都更有力量。
感谢徐冬冬,用抽象语言道出了我的心声,感谢他找到了一种超脱凡俗的、用现代语言呈现传统文化之美的形式,没让二十四节气成为一种俗气的“文化标本”,而是让它成为“启示文化理解的钥匙”;观看他的作品,如同身处一个能“与文明对话、与自己对话”的平台。我相信,徐冬冬的作品带给观众的不仅仅是感官刺激,更是对“不同文明如何相处”“人类如何与自然共生”的启示——期待这场展览给我们带来最珍贵的“生命答案”。愿每一位朋友,都能在这场“节气之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明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