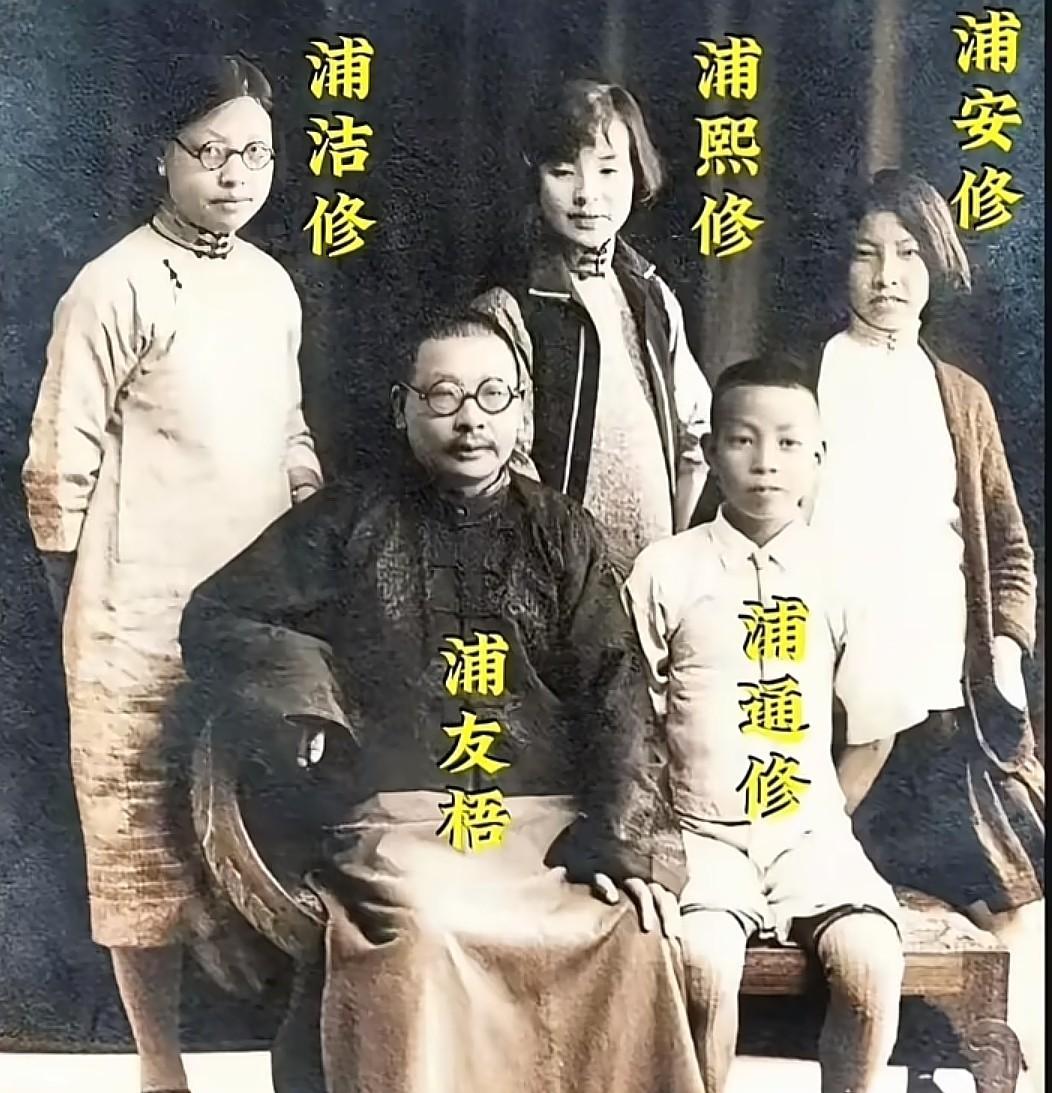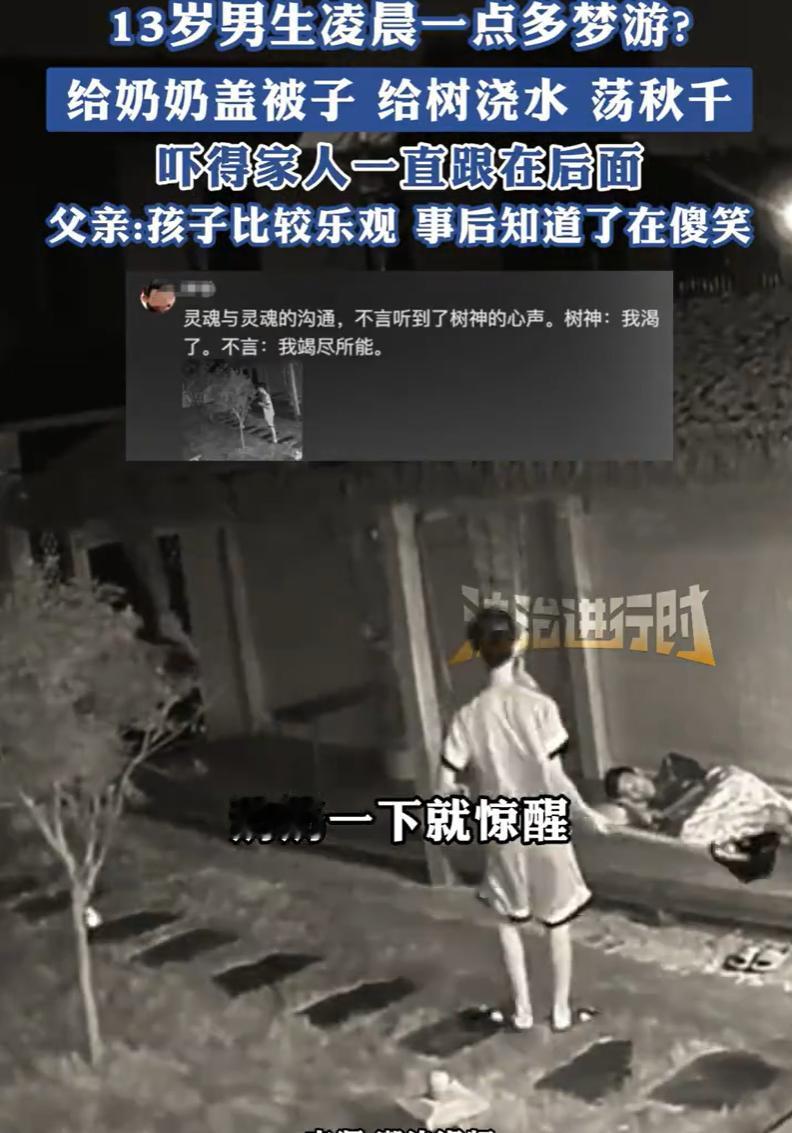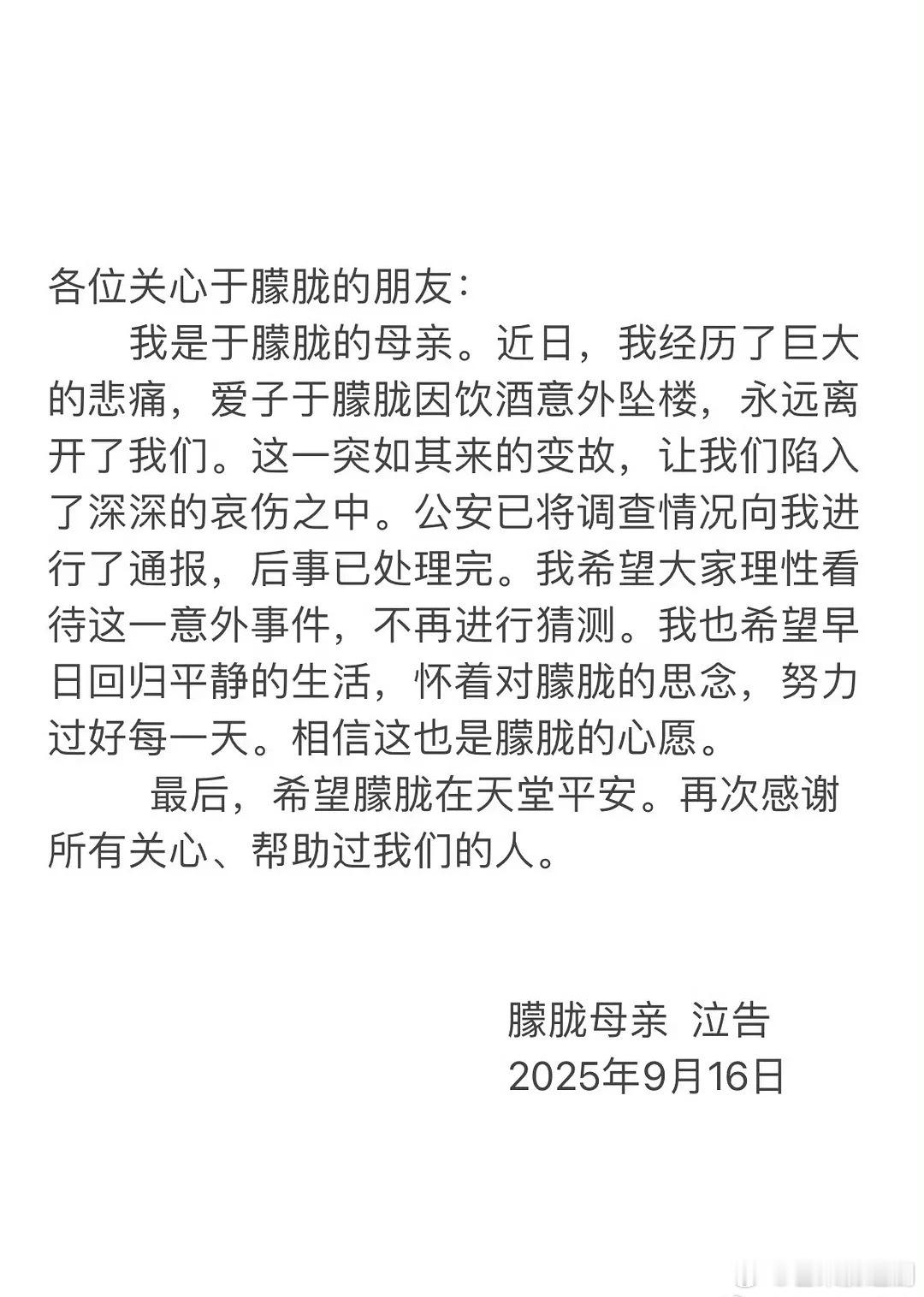1936年,裹小脚的她竟然在长征途中诞下了一个女婴,产后的恢复只能寄希望于草地上的嫩芽,谁能想到,这位历经磨难的母亲,最终竟活到了102岁。 陈琮英晚年整理旧物时,总会在木箱底层摸到一小包干枯的草芽。 草叶早已失去绿意,一捏就碎,却被她用油纸包了三层——这是1936年长征途中,她产后唯一能找到的“补养”,也是她从四川阿坝草原带到陕北,又从陕北带到北京的念想。 谁能想到,当年靠这捧草芽撑过产后难关的裹脚女人,后来竟能走过一个世纪,活到102岁。 1936年的阿坝草原,九月就冷得能哈出白气。 陈琮英跟着红二方面军走在烂泥地里,裹脚布被汗水浸得发硬,脚趾在里面蜷成一团,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 更难的是,她的肚子已经挺得老高,怀里还抱着个装机要密码的木箱子,箱子边角磨得她肋骨生疼。 那天傍晚,队伍借住在藏民的两层阁楼,一楼圈着牛羊,膻味儿顺着木缝往上飘。 她想爬木梯上二楼歇脚,刚踩稳第三步,脚下一滑就摔了下去,肚子里突然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疼。 战友们慌了神,七手八脚把她扶到二楼,在地上铺了块油布——这就是临时的“产房”。 没有热水,没有剪刀,只有战友递来的一块干净布条。 随着一声微弱的啼哭,女儿降生了,任弼时蹲在旁边,用自己的军装外套裹住孩子,声音有些发颤:“就叫远征吧,纪念这段路。” 产后第二天,陈琮英连一口热粥都没喝上,孩子饿得直哭,她却没奶。 看着身边战友挖来的嫩草芽,她闭着眼塞进嘴里,涩味顺着喉咙往下滑,胃里一阵翻腾,却还是硬咽了下去——她知道,只有自己有力气,孩子才能活下去。 后来朱德总司令听说了这事,特意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半条鱼,让炊事员熬成汤送过来。 汤里飘着几粒米,任弼时没舍得喝一口,全端给了她。 任弼时还学着用缝衣针弯成小鱼钩,每天行军结束就去河边钓鱼,哪怕只钓上两条指节大的小鱼,也会熬成汤给她和孩子喝。 陈琮英总说,那碗鱼汤的鲜,她记了一辈子,不是因为味道多好,是在那样的绝境里,一点热乎气就足以撑着人往前走。 其实陈琮英的韧性,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磨出来了。 12岁那年,她按“指腹为婚”的约定,成了任弼时家的童养媳。 看着任弼时总盯着学堂的方向发呆,13岁的她偷偷揣了娘留下的半块银圆,走了两天路到长沙,进了家织袜厂。 机器从早响到晚,震得她耳朵嗡嗡的,手指被棉线勒出红印,破了就用厂里的粗布条缠上,渗出血珠也不敢停。 每个月发工钱,她只留够买两个窝头的钱,剩下的全托人寄回任家,专门给任弼时交学费。 任弼时后来跟人说“没有琮英,我走不进学堂的门”,这话她听了没多说什么,只是把织袜的速度又加快了些——她知道,只有任弼时读了书,他们的日子才能有盼头。 革命路上的苦,比织袜厂的日子更难熬。 1928年10月,任弼时在安徽巡视时被国民党抓走,陈琮英抱着刚出生的女儿苏明,连夜爬上一辆敞篷拉煤车往长沙赶。 车斗里的煤渣被风吹得打在脸上,又黑又疼,她把苏明裹在棉袄最里层,手紧紧护着孩子的头,一路没敢合眼。 任弼时是被组织救出来了,可苏明在路上受了风寒,烧得浑身滚烫,转成肺炎没几天就没了。 她抱着孩子冰冷的小身体,躲在客栈的角落里哭,不敢让刚出狱的任弼时看见——他的后背还留着监狱里的鞭伤,她怕这事儿再压垮他。 1934年部队西征时,她刚生下儿子“湘赣”,因为要跟着队伍走,只能把孩子留给当地老乡。 她把孩子裹在自己织的小毛衣里,反复跟老乡说“等打胜仗就来接”,转身时眼泪砸在地上,却没敢回头。 后来她才知道,湘赣苏区被敌人烧了,孩子再也没了消息。 任弼时临终前还攥着她的手说“湘赣的消息,再找找”,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她跑遍了当年的苏区,逢人就问“有没有见过一个裹着红毛衣的小男孩”,直到找到当年的老乡,才知道孩子早就没了,只留下那件她织的毛衣。 1950年任弼时突发脑溢血离世,48岁的陈琮英带着四个没长大的孩子,拒绝了组织安排的轻松工作,说“弼时一辈子没占公家便宜,我也不能”。 晚年的她,每天都会把长征胜利50周年时发的八角帽拿出来擦,帽檐上的红五星被她擦得发亮,晚上睡觉就放在枕头边。 2003年5月,她在睡梦中走了,享年102岁。 整理遗物时,孩子们在她的木箱里发现了那包草芽、那件小毛衣,还有那顶八角帽。 这些物件,串联起她从裹脚童养媳到长征母亲,再到百岁老人的一生,也藏着她扛过所有苦难的秘密:只要心里有盼头,再难的日子也能走下去。 如果各位看官老爷们已经选择阅读了此文,麻烦您点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各位看官老爷们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