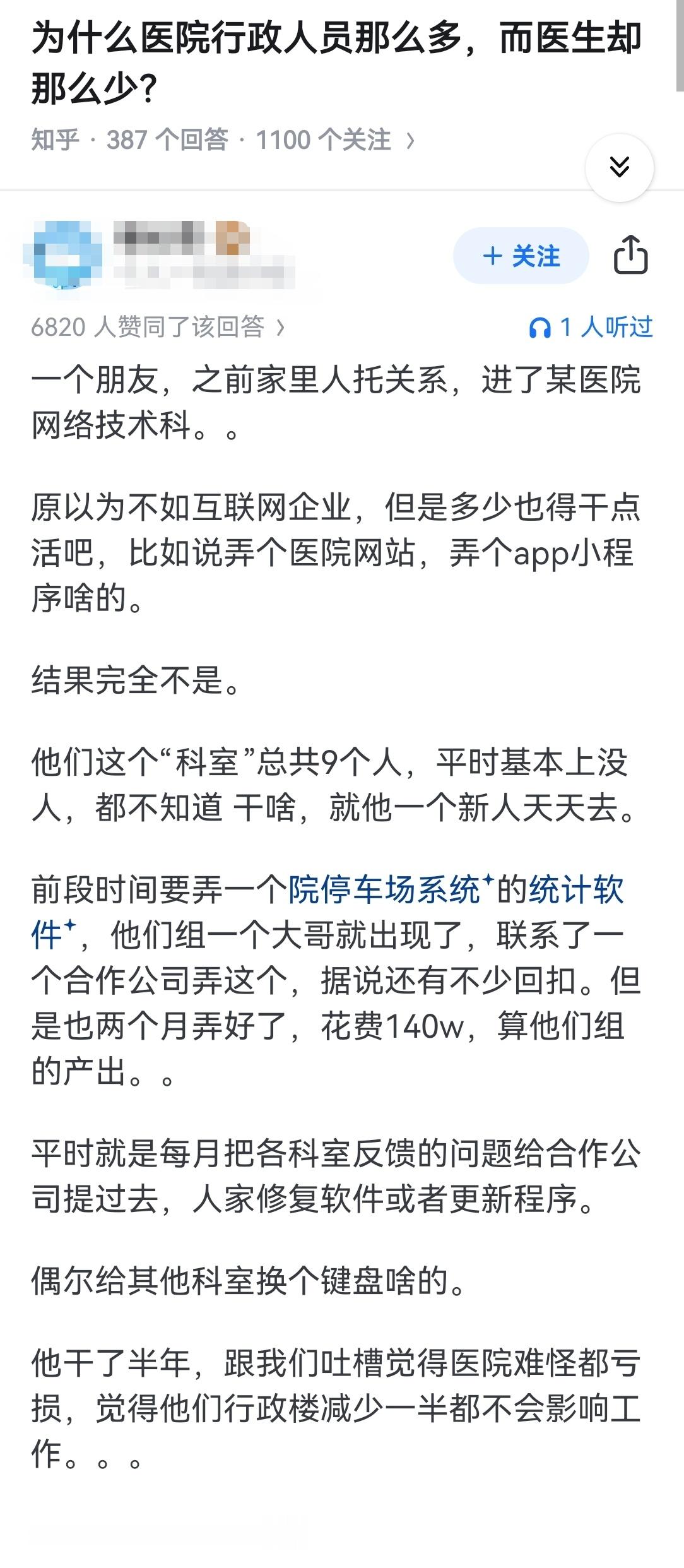1939年,白求恩医生牺牲后,交通队将他的遗体伪装成重伤员,连夜赶路,将他送到了后方的于家寨。 白求恩在孙家庄给伤员做手术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第二天伤口就肿了,他却没跟任何人说。 每天收工后,他偷偷把肿得发亮的手指泡进浓食盐水里消毒,转天照样攥着手术刀给伤员开刀。 后来转移到一分区医院,他更忙了,两天跑了两个战地医疗所,做了几十个手术,还抽空给医生们讲课,压根没把自己的伤当回事。 11月1号,前线送来了个脖子得重病的伤员,得了丹毒还合并蜂窝组织炎,情况特别危险。 医生们劝他,“白大夫,你手指还没好,万一感染了可咋整?这手术我们来做”。白求恩摇了摇头,说“这手术不好做,弄不好伤员就没了,还是我来”。 按理说这时候该好好养伤,可他哪闲得住?11月2号,头天刚走了七十里路,累得不行,身上还不舒服,天一亮照样爬起来,查了两百多个伤员; 11月3号,他用手套把伤口包紧,硬撑着给十三个伤员做了手术,最后一个手术做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回住处时一头栽倒在床上。 同志们怕他累垮,就瞒着他前线的消息,说没什么战斗,把他安置在村子中间,就怕他听见炮声。 可11月5号,他还是听见了隐约的炮声,一下子就醒了,穿上棉军服就推开窗户喊人。 他脸烧得通红,有点生气:“你们别骗我,北面在打仗,快准备出发!”大家想解释,他却急着要走,说“前线战士在流血,我不能在这歇着”。 那天雪下得特别大,风也猛,同志们轮流扶着他,他走得摇摇晃晃,每一步都费劲。 可一看见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他立马扔了拐杖,甩开扶他的人,跑过去扶着担架看,还一个劲怪自己“来迟了,来迟了”。 那时候他体温都到39度6了,自己才是最需要照顾的人。 到了11月7号,他们到了王家台的卫生队,离火线就十里地,白求恩左胳膊肘已经化脓,腋下疼得厉害,体温快40度了,吃了药昏昏沉沉睡过去。 可伤员一送过来,他立马要爬起来去手术,刚起身就晃了一下倒在床上,挣扎着起来又倒了。 他拉着同志们的手,断断续续说“只要是头、胸、肚子受伤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就算我睡着了,也得把我叫醒”。 见大家围着他不走,他又催“别管我,快去救伤员,他们比我更需要你们”。 11月10号,军区领导知道他不行了,派专人来让他去后方医院,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他送过去。 白求恩摸了摸肿得厉害的左臂,沉默了好久,才用发抖的声音说“我服从安排”。 躺在送他去后方的担架上,他看着越来越远的前线,眼睛里满是泪水,喃喃地说“我心里装着前线流血的战士,要是还有点劲,我肯定不走”。 下午3点到了黄石口村,离后方医院还有十八里,他却坚持要在这住下,好像知道自己撑不到了。 那几天,晋察冀的军民都惦记着他,军区派了最好的医生来,前线送来了缴获的药,老乡们也送来大枣和鸡蛋,都盼着他能好起来。 有人劝他截肢,他摇了摇头,说“能跟大家在一起,截了双腿我也愿意,可我血里有毒,截肢没用了”。 11月11号黄昏,后方医院院长林金亮赶来,白求恩看见他,勉强笑了笑,伸出右手使劲握了握他的手,说“谢谢你们,这么冷的天还跑过来”。 林金亮想把他转去条件好的医院,他却摇头,说“我是医生,知道自己得的是脓毒败血症,能用的办法都用了,还是让我赶紧写遗书和报告吧”。 他跟聂司令员说,自己可能要永别了,让转告加拿大和美国的共产党,他在这很愉快,就想多做贡献;让国际援华委员会给前妻寄点生活费,说自己对不起她,但也很快乐。 1939年11月12号清晨5点20分,白求恩还是走了,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为了反法西斯的仗,把命留在了这里。 当天上午10点,交通队怕日本人发现了来破坏,就把他的遗体化装成重伤员,抬着担架一口气走了五天,送到了于家寨。 11月16号,聂荣臻司令员含着泪给他入殓,帮他净身整容,用红绸裹着身体,穿上新的八路军军装,找了好柏木做棺材,把他埋在村南的狼山沟口。 为了防日本人扫荡,军民们把墓地犁平了,连坟头都没留,后来日本人真来扫荡了,没找到墓地,总算护住了他的安宁。 现在白求恩还埋在这片红土地上,是他把心都掏给了这里,他来的时候,带着手术刀和药品;走的时候,把生命和精神都留了下来。 这片土地见过他在手术台旁的身影,听过他讲课的声音,也记得他最后那句“我不能在这歇着”。 老百姓都记得他,记得有个外国大夫,不远万里来中国,为了救咱们的人,拼到了最后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