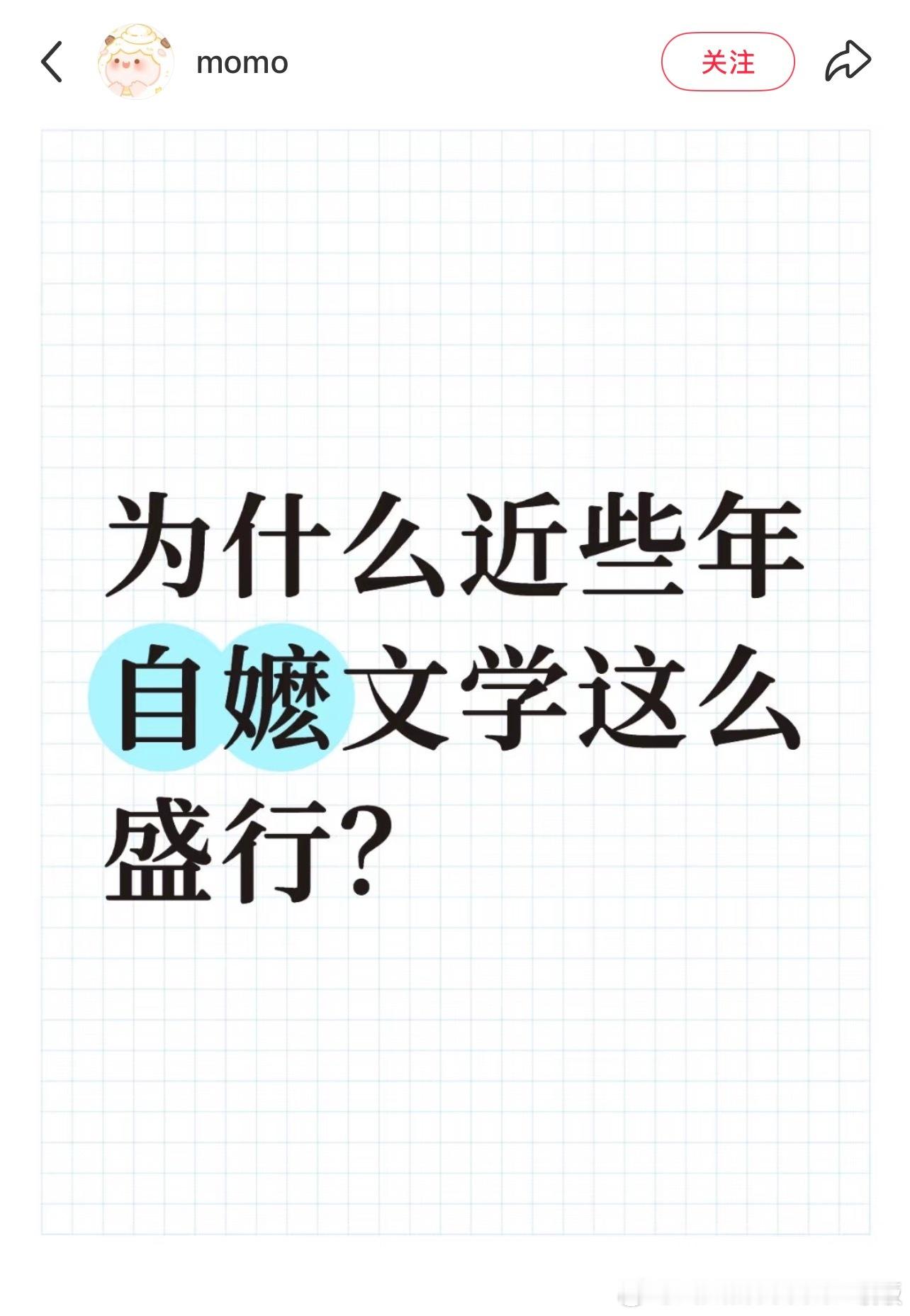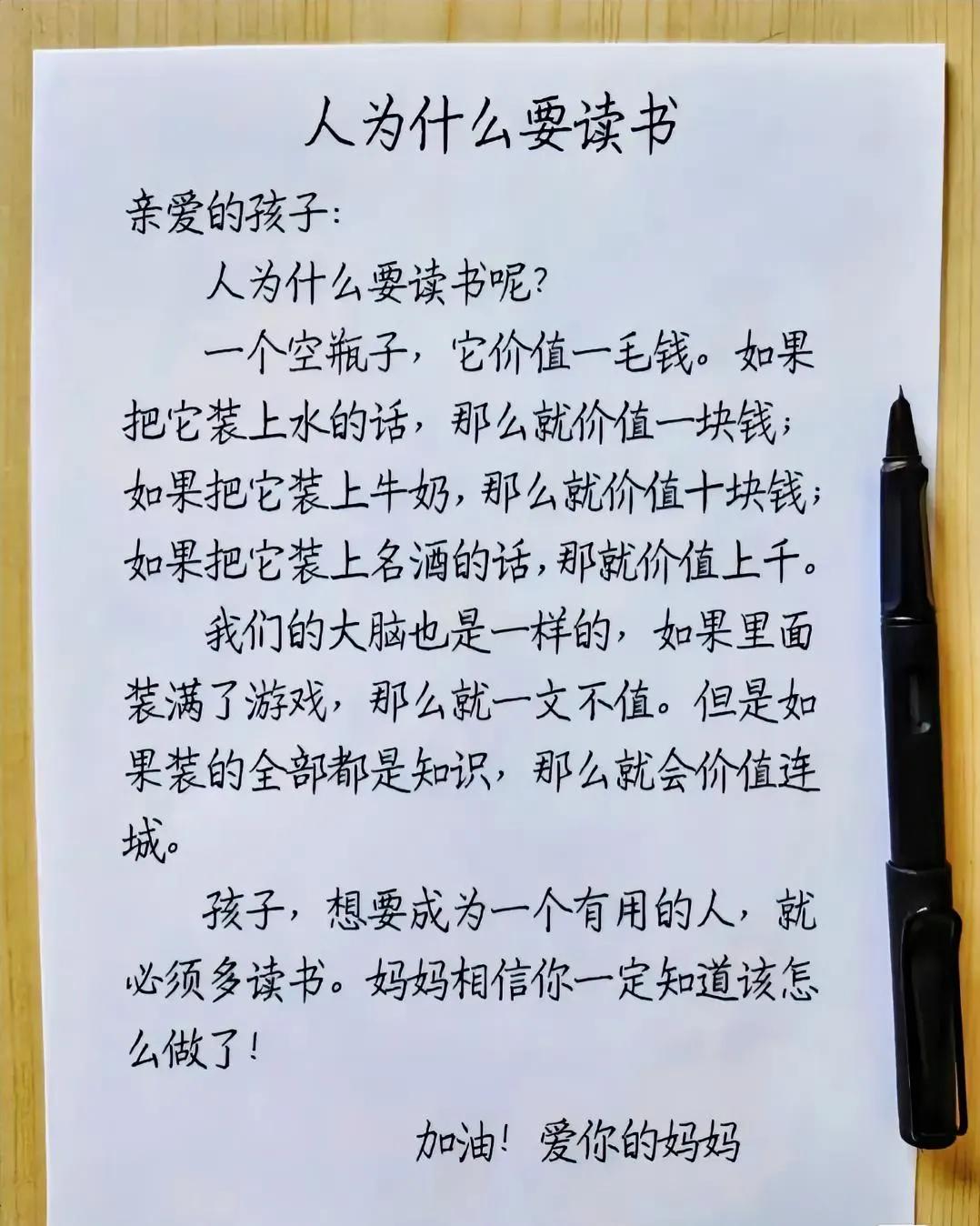诗人赵丽华对质疑者诘问:“我们对莫言作品读了多少?比瑞典人多吗?我们对作品中的时代和人物的理解有这么深刻吗?我们是否阅读贫乏而浮躁?是否懂得尊重和理解不懂得反思和自省? ”其实莫言的成就一直就被学界所认同,早在 2006 年,陈晓明就曾对莫言获奖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当时还把莫言和另 一位当代大家贾平凹进行了比较,分析了莫言更有资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 但也有国内的学者质疑,认为莫言不一定是中国当代作家中最出色的,应该是莫言的某种官方色彩的身份,或是其作品没有用激烈的措辞去揭露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表述相对委婉,他才能够获得被国内外意识形态的共同认同的机会。这些说法是否有真凭实据恐怕是见仁见智了,但是,诺贝尔文学奖严格的评选标准和规范的评选程序,莫言本人的作品和成就却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 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想象力无疑是最为璀璨的星辰之一,它不仅照亮了作品的内容,更引领着读者穿越现实与幻想的边界,体验那些未曾触及的情感与思想。想象力,这一看似抽象却又无处不在的能力,对于作家而言,既是感知世界的独特方式,也是创新表达的源泉。一个作家若缺乏丰富的想象力,其作品便难以保持新鲜感,更遑论拥有长久的生命力。莫言,这位中国当代文学的巨匠,正是凭借着他那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在文学的殿堂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莫言的作品中,想象力如同潺潺流水,时而平静温柔,时而汹涌澎湃,为读者展现了一个又一个既奇异又真实的世界。他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能够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这些因素一旦移植到我的文学中,那我的作品就跟别人不一样。”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感知能力的描述,更是对他作品中想象力运用的生动诠释。 然而,莫言的想象力并非总是受到赞誉。在《檀香刑》中,他大量引入了有关刑罚过程的细节描写,这些“冷酷”、“残忍”的描写,让一些读者感到不适,甚至有人认为这种超乎常人的想象太过于残忍,不合乎传统道德习惯。面对这样的批评,莫言或许会感到无奈,因为他只是一个作家,他的职责是记录和表达,而不是去迎合或遵循某种既定的道德标准。如果这也不能写,那也不能写,那么作家的想象力又该如何施展?创作又该如何继续? 除了道德层面的争议,莫言的想象力还曾被批评为过于泛滥,以至于减弱了小说的可读性,降低了作品的艺术价值。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戴维·洛奇曾说:“一部好的小说中的描写绝不仅仅是描写。大多数背景描写的危险在于一连串的漂亮的陈述句和叙述的中断将读者推向昏昏欲睡的境地。”莫言最初的小说实验,如《食草家族》,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作者毫无节制地使用想象空间,把大量毫无群体经验的个性语言抛给读者,还随心所欲地穿插、打断故事情节的发展,使小说显得散漫无序、支离破碎,让人难于卒读。 但值得庆幸的是,莫言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这样的创作风格中。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写作方向,在问题出现之后也能够很快改正,而不是一味的固执己见。在之后的作品中,如《天堂蒜墓之歌》、《酒国》等,他已经能够很好地控制想象力的运用,使作品既保持了独特的风格,又具备了较高的可读性。 在《天马行空》一文中,莫言曾说:“我主张创作者要多一点天马行空的狂气与雄风,少一点顾虑和犹疑。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艺术风格上,不妨有点随意性,有点邪劲。……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只要顺手顺心就好。”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创作态度的总结,也是对所有作家的鼓励。莫言依靠个性化的感觉和意识活动,构建起了一个想象的高密东北乡,并不断地扩展想象的空间,形成了一场想象的狂欢。关于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世界的想象,莫言曾坦言:“我写的不是我原来的家乡,仅仅是借助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名称。活动的人物,生长的植物,都不是那里的,这是我理想中的地方。” 他毫不掩饰自己对想象力的推崇,也在自己的小说中不断地实践。在《后起的强盗总比前辈更大胆》一文中,他更是直言不讳地说:“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在我的新作《丰乳肥臀》里,我让高密东北乡盖起了许多高楼大厦,还增添了许多现代化的娱乐设施。……我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我的真实的高密东北乡根本就没有山,但我硬给它挪来了一座山,那里也没有沙漠,我硬给它创造了一片沙漠,那里也没有沼泽,我给它弄来了一片沼泽,还有森林、湖泊、狮子、老虎……都是我给它编造出来的。”莫言曾说:“作家的想象力,是作家存在的唯一理由,或者说是看家的本事。”这句话,不仅是对自己创作生涯的深刻总结,也是对所有作家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