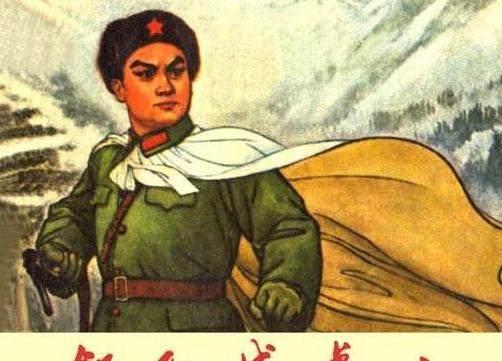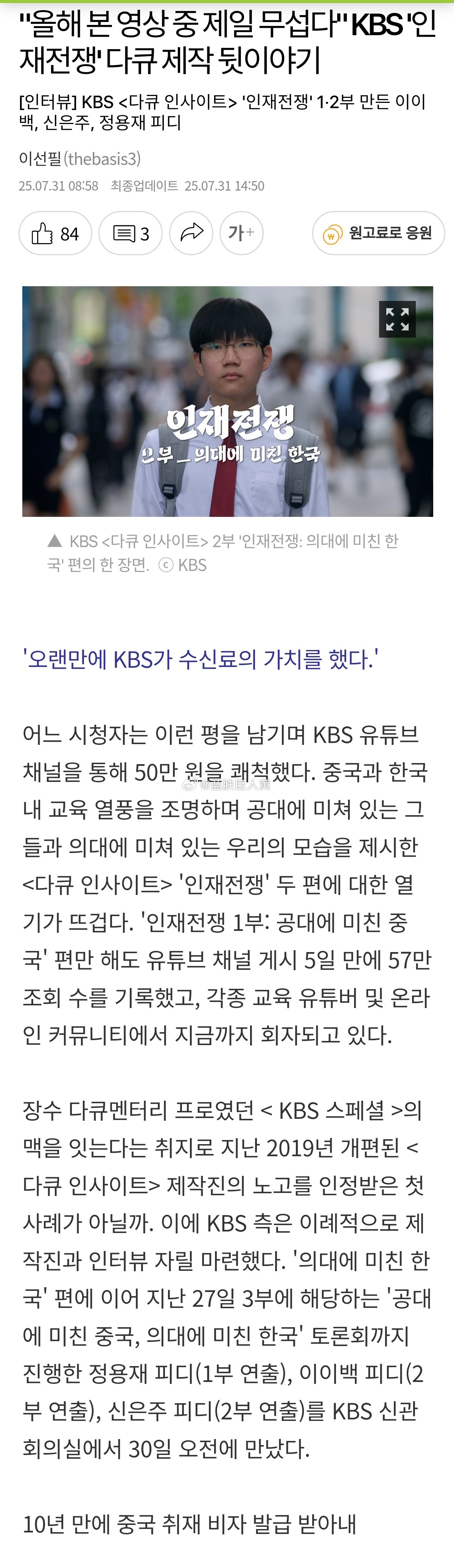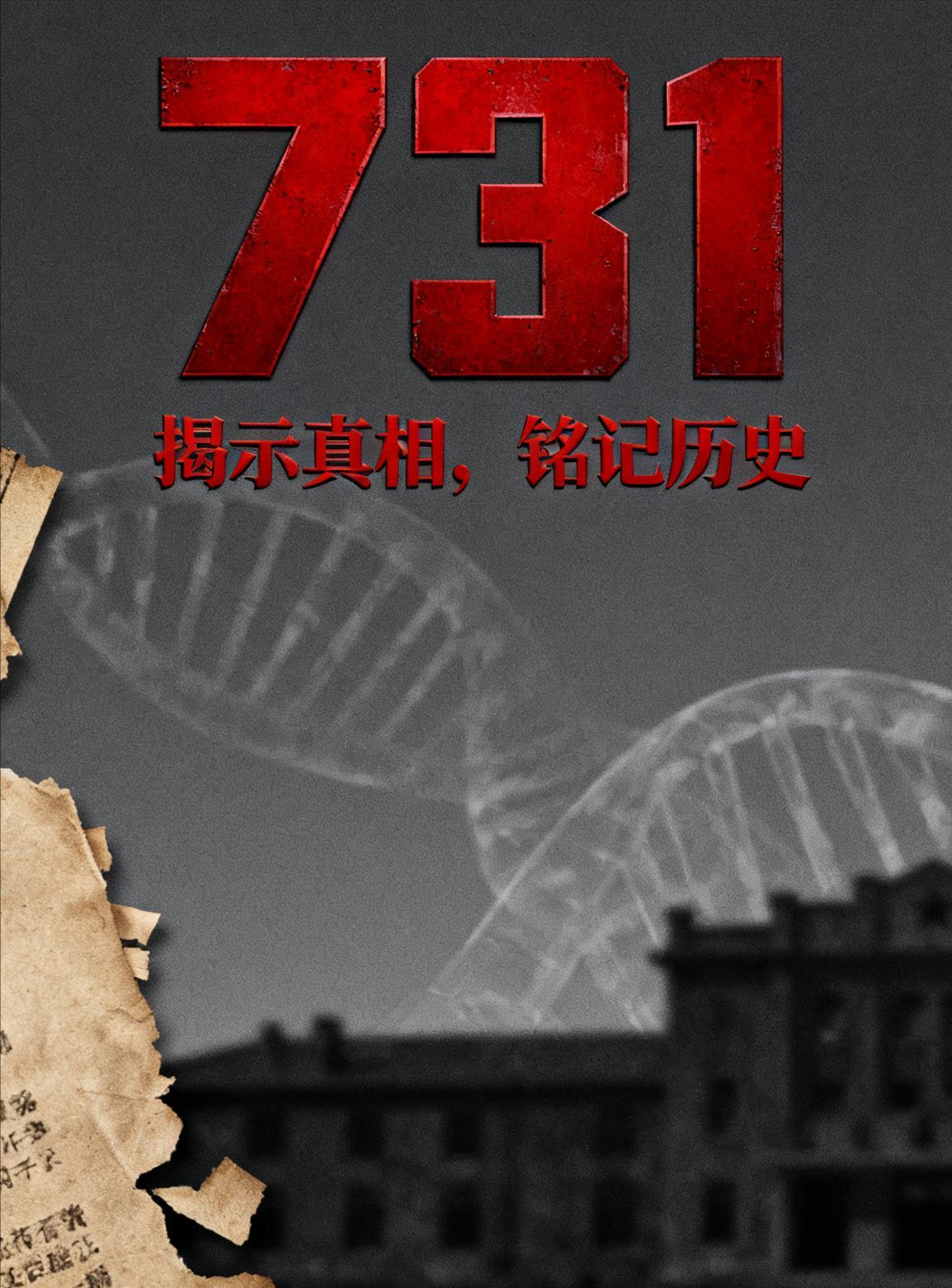“文革”期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了几十部外国影片,当时俗称“内参片”,当时谁能看“内参片”呢?只有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可以,以供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 当普通百姓只能看八个样板戏时,万航渡路的一座小楼里却在秘密译制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影片。这些被称为”内参片”的电影,观看权限严格到连译制厂领导都无法观摩。是什么让这些影片如此神秘?又是谁在那个封闭的年代里享有这种特殊的文化特权? 当年”内参片”搞得挺神秘,说白了就是不公映的内部参考片。上译厂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都译制过少量的参考片,这些影片是供中央少数首长和外事部门的人员观看的,以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动态。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普通观众的文化生活只剩下样板戏和几部阿尔巴尼亚、朝鲜影片,而”内参片”却为特定人群打开了另一扇窗。 陈叙一(1918~1992),中国电影译制片翻译、导演。浙江定海人,这位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奠基人,在那个年代里承担着一项特殊的使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后仅一个月,陈叙一带了三位同伴赶往东北长春,向长影的译制片组取经。回到上海后,他用一间20平方米的小房间、一个旧话筒、一架旧录音机,开启了中国译制片事业的先河。 “内参片”的译制工作充满了严格的保密要求。所有参加译制工作的人员一律不得外传片名、影片内容,配音用的对白剧本不得带回家,配音完成后一律上交、统一处理。这种保密级别之高,凡是不参加这部影片译制工作的,不管是厂内领导、工军宣队,甚至局一级的领导也一律不得看片,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的命令。 工作环境的艰苦与保密要求形成了鲜明对比。上译厂当时的工作条件很差,录音棚搭建在二楼的大阳台上,是个又小又闷的标准”漏音棚”。炎热的夏天里,为了避免电扇产生杂音,录音时必须关闭降温设备,工作人员汗流浃背却要保持声音的清晰稳定。更有趣的是,夜深人静时大喇叭一开,发出恐怖的声音:“着火啦!快来救火啊!”“救命啊!救命啊!”周围居民在睡梦中惊醒,吓得够呛,陈叙一不得不挨家挨户道歉解释。 审片环节更是体现了”内参片”的特殊地位。这些”内参片”译制完成后统一由徐景贤(当时称他为徐老三)审查,印制拷贝要用最好的伊斯曼胶片,直接送中央。有些影片甚至是文化部直接派人来上海取片,整个流程都透露着神秘色彩。 矛盾的是,每部”内参片”译制完成后,所有参与人员都要参加批判会。大家要口诛笔伐这些影片宣扬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判其美化资本家、鼓吹阶级调和的内容。配音演员们一边要全身心投入为影片中的人物配音,一边又要在批判会上抨击这些角色和故事。 “内参片”的真正价值在那个时代逐渐显现。首先这些”内参片”中很多影片让上级了解了世界动态。周总理曾指出:日本的《战争与人》是一部吹捧法西斯的影片,表面上反法西斯,实际上却在歌颂军国主义,影片内容很毒,要让我们的外国使节们了解。此外,我们译制了一大批欧美影片,为样板戏的创作人员提供了参考片。如影片《红菱艳》,芭蕾舞剧组的同志跟我聊过,这部影片很有借鉴作用。 当历史的车轮滚向改革开放,“内参片”终于走出了保密的围墙。这些内参片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曾公映或在电视台播出,最为观众熟知的有《巴黎圣母院》《简爱》《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等影片。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期,上译厂的”黄金年代”开启了,那些曾经在密室中诞生的艺术作品,如今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陈叙一形容说:“生旦净末丑,就像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谁上阵都能抵挡一阵。”这位译制事业的奠基人,直到1992年4月24日逝世,都在为这项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剧本翻译要有味,演员配音要有神”这14字厂训,至今还挂在上译厂最醒目的墙上。 60年间,上译厂共译制了来自40多个国家的1500多部影片。那个特殊年代的”内参片”经历,见证了中国译制事业从神秘走向公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进程。 从神秘的”内参片”到后来的译制片辉煌,这段历史既反映了特殊时代的文化生态,也展现了艺术工作者的坚持与创造。那些曾经只有少数人能看到的影片,如今已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你对那个时代的”内参片”现象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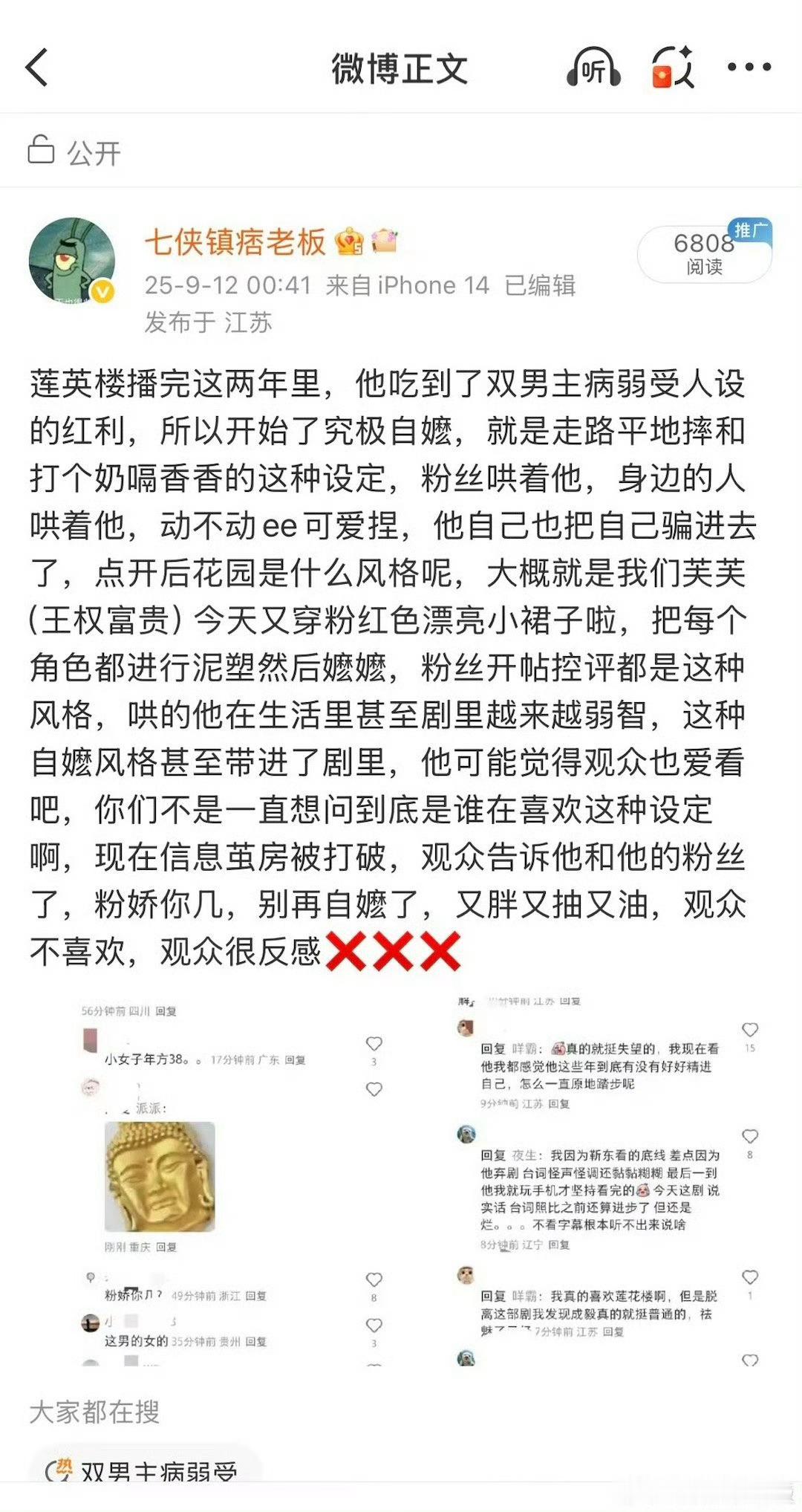
![[比心]玛格特罗比和科林法瑞尔性感亮相主演新片《绮梦之旅》纽约首映礼🤩[色](http://image.uczzd.cn/7547712053432169775.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