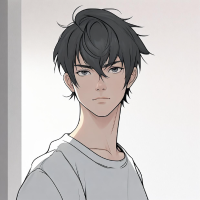1976年3月,广西边防某团王营长的妻子程玲玲,经部队批准,在驻地小镇开了一家小饭馆。说是饭馆,其实也就是给过往之人下碗面条、炒个小菜之类的,仅有几张桌子罢了。时间一长,镇上的人都称她为“玲玲嫂子”。 1976年春天,广西边境线上那风啊,刮得跟刀子似的。就在那么个小镇上,一个叫程玲玲的军嫂,开了家小饭馆。她男人是边防团的王营长,这饭馆,是部队特批的。 为啥特批?一来方便过路的战士和乡亲们有口热饭吃,二来,也能给家里添点收入。 程玲玲的饭馆,说白了就是个夫妻店,不,连夫妻店都算不上,就她一个人撑着。几张破旧的木桌子,一口大铁锅,一个泥巴糊的灶台。每天天不亮,整个小镇还在沉睡,程玲玲就得起来,院子里“邦邦邦”劈柴的声音,就是小镇最早的闹钟。 开张那天,第一个客人是个刚下哨的小战士,冻得跟个鹌鹑似的,一头扎进来就喊:“嫂子,有热乎的没?”程玲玲二话不说,麻利地给他下了一碗热汤面,还卧了个荷包蛋。那年头,鸡蛋可是稀罕物,是她用两尺布票跟老乡换的。小战士吃得满头大汗,掏出两毛五分钱和三两粮票,多的钱硬是不要找,说下次还来。 就这么着,“玲玲饭馆”火了。不是说生意多好,而是那份人情味儿。巡逻的兵路过,进来喝碗汤;赶集的乡亲,揣着几毛钱来炒个素菜,就着自带的窝头吃。程玲玲总会多给一勺菜汤,笑着说:“泡着吃,香!” 程玲玲的饭馆能开起来,靠的是什么? 不是资本,更不是商业模式。在那个人情和票证同样重要的年代,她靠的是一种最朴素的“社会信用”。她的信用,是丈夫王营长的军功章,是部队的批准文件,更是她自己那双能擀出筋道面条、能炒出锅气小菜的勤劳的手。 缺面粉了,炊事班长偷偷塞给她一小袋;缺盐了,供销社老李乐意用盐换她烙的饼。这种人与人之间基于信任的“等价交换”,比今天我们扫码支付要复杂,但也暖和得多。 这间小饭馆,成了那个艰苦年代里一个“暖和的窝”。一个老兵吃了她的面,感慨地说:“嫂子,这面下肚,比穿件棉袄都暖和。”这句话,就是对“玲玲嫂子”和她的小饭馆最高的评价。 现在谁还这样? 还真有。 前段时间,一篇重庆日报的报道,说的是綦江石壕镇有个叫“红军桥”的地方。有个叫陈文涛的汉子,接替他去世的哥哥,成了新一代的义务守桥人。他哥哥陈文全,一座桥,守了整整43年,风雨无阻,不拿一分钱工资。 这地方,是1935年红一军团长征路过的地方。当地人对红军有感情,守桥,就像守着自家的根。陈文涛说,他们祖祖辈辈都住这儿,是“天然的守桥人”。不光他,全村2580多口人,个个都是守桥人。下暴雨了,大家会一起去检查桥梁;节假日游客多了,村里的党员、年轻人,甚至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都会主动跑来当志愿者,当讲解员。 当地一位叫赵福乾的老同志,讲起他家的往事,说他爷爷奶奶当年就在红军驻扎地附近开了家小饭馆,跟红军打过交道。他说:“只有红军给钱,还讲礼貌。” 无论是70年代边防线上的“玲玲嫂子”,还是30年代红军路过的无名饭馆,亦或是今天仍在默默守护红军桥的陈文涛们。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一种不为钱、不为名,但求心安,但求为大伙儿做点事的朴素精神。这种精神,就像那座红军桥,历经风雨,依然坚固。它构建的,是一个有人情、有信任、有温度的社会。 从“玲玲嫂子”到“守桥人”,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传承。但另一面,我们也不得不面对一些当下的尴尬。 就在前几个月,我看到几个新闻,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姓李的哥们儿,因为盗窃坐了6年牢。出来后洗心革面,想送外卖自食其力。结果呢?在手机上申请,平台系统一查,有前科,直接拒绝。连一个靠力气吃饭的机会,都被一个冰冷的大数据系统给否了。 还有一个姓刘的朋友,抢劫罪判了12年。出狱后想开个小饭馆,就跟当年的“玲玲嫂子”一样。结果去工商注册,被告知他还有两年“剥夺政治权利”的附加刑没执行完,不能当法人。 这些事,让我一下子从“玲玲嫂子”的温暖故事里惊醒过来。今天的社会,规则越来越细,系统越来越智能,大数据能把每个人分析得明明白白。这当然是进步,它高效、安全、精准。但有时候,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呢?可能就是当年部队领导对程玲玲说“行,你干吧”的那份担当和变通;可能就是炊事班长偷偷塞给她一袋面的那份“违规”的温暖;可能就是乡亲们可以用一张奖状换土豆的那份灵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