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0年,大将军郭威发动兵变,闯入太后李三娘寝宫,李太后赶忙说道:“皇位尽可拿去,别伤我性命”,却见郭威扑通跪倒在地:“太后,臣郭威一片忠心,只为诛灭奸佞。”李太后幸亏没有当真。 宫门外的喊杀声还没歇,廊下的宫灯被风卷得直晃,照得郭威甲胄上的血渍忽明忽暗。李三娘攥着寝衣的手指发白,后颈贴着冰冷的墙壁——这堵墙还是当年刘知远称帝时新砌的,没想到如今成了她唯一的屏障。 她盯着郭威叩在地上的后脑勺,那顶铁盔上还沾着头发丝,不知是谁的。 “郭将军起身吧。”李三娘的声音有点抖,却没带多少怕,“奸佞是谁?是刚被你砍了头的小皇帝,还是这满宫的侍卫?” 郭威的肩膀僵了僵,抬起头时,眼里的“忠心”像淬了冰。 “太后明鉴,少主被小人蛊惑,滥杀功臣,臣不得已才……”他话说到一半,被远处传来的惨叫打断。那声音耳熟,像是负责守卫宫门的老将军,昨天还在给她递平安帖。 李三娘忽然笑了,笑声在空荡的寝殿里打旋。 她想起十六年前,刘知远还是个落魄校尉,在客栈里给她买了块热糕,说“等我出人头地,让你天天吃这个”。后来他真的当了皇帝,却在龙椅上告诫她:“乱世里,‘忠心’二字最不值钱,听着感动,转头就能剜你的心。” 郭威还在跪着,甲胄上的血腥味越来越浓。 他带来的亲兵守在门口,靴底碾过碎瓷片的声音,比宫灯摇晃还刺耳。李三娘瞥了眼梳妆台上的玉梳,那是刘知远送的定情物,梳齿断了两根——上个月小皇帝猜忌郭威,派人抄他府时,她偷偷藏起来的。 “既然是诛奸佞,”李三娘慢慢直起腰,后背离开墙壁,“那郭将军打算让谁当新君?” 郭威的眼神闪了闪,从怀里掏出份拟好的诏书,墨迹还新鲜:“臣已与众臣商议,拥立武宁节度使刘赟为帝,他是先帝的侄子,名正言顺。” 李三娘接过诏书,指尖划过“刘赟”二字,像摸着块冰。 她认得这个侄孙,去年来京时还怯生生给她磕头,手里攥着个粗布包,里面是乡下的枣干。让这样的孩子当皇帝,跟把羊扔进狼群有什么区别? “好。”她把诏书放在桌上,“那就依将军的意思。只是眼下兵荒马乱,哀家这宫苑怕是住不得,得挪个地方。” 郭威立刻道:“臣已备好偏殿,保太后安全。” 搬家那天,李三娘只带了个旧木箱。 箱子里没有金银,只有刘知远的几件旧衣,还有小皇帝小时候画的歪扭龙。亲兵想检查,被她冷冷盯着:“这里面是汉家的骨血,你也敢碰?”那人缩了手,眼里的忌惮比尊敬多。 偏殿的窗户纸破了个洞,李三娘总爱趴在那里看天。 她看见郭威的士兵在街上巡逻,看见百姓们紧闭门窗,看见有人偷偷给刘赟的府邸送东西,又被郭威的人拦回去。她知道,那纸“拥立”的诏书,不过是块遮羞布。 果然,没过一个月,消息传来说刘赟“病逝”了。 传消息的小太监不敢抬头,李三娘正用刘知远的旧衣改小被子,听见这话,针脚歪了一下,扎在指头上。血珠滴在布上,像朵小小的红梅。 当天下午,郭威穿着龙袍来看她。 新做的龙袍很合身,只是他站在门口时,李三娘总觉得那身衣服上,还沾着刘知远和小皇帝的血。“太后,”他的声音比上次软,“群臣拥戴,臣……不得已登基了。” 李三娘放下针线,指了指桌上的枣干——是刘赟去年送的,她一直没舍得吃。 “郭将军,哦不,陛下,”她慢慢说,“哀家不求别的,只求给汉家留个念想。” 郭威沉默半晌,下了道旨:尊李三娘为昭圣太后,供养于别宫。 没人知道,那天他走后,李三娘把枣干全倒在了窗外。风一吹,枣子滚得满地都是,像无数双眼睛,看着这乱世里的城头变幻大王旗。 后来有人说,李太后太懦弱,连自家江山都守不住。 可她在别宫活到了75岁,看着郭威的后周渐渐安稳,看着百姓们慢慢敢打开门窗。临终前,她让宫女把那个旧木箱烧了,火光照着她的脸,竟带着点笑意。 或许她早就明白,在这五代十国的兵戈里,保住性命,看着乱世慢慢透出点光,比抱着“忠心”的空壳子硬撑,更实在。 信息来源:据《旧五代史·汉书·李太后传》《新五代史·周本纪》记载,后汉乾祐三年(950年),郭威发动兵变,次年称帝建立后周,李太后(后汉高祖刘知远皇后)因审时度势得以善终。相关记载反映了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皇权脆弱的特点,以及乱世中女性的生存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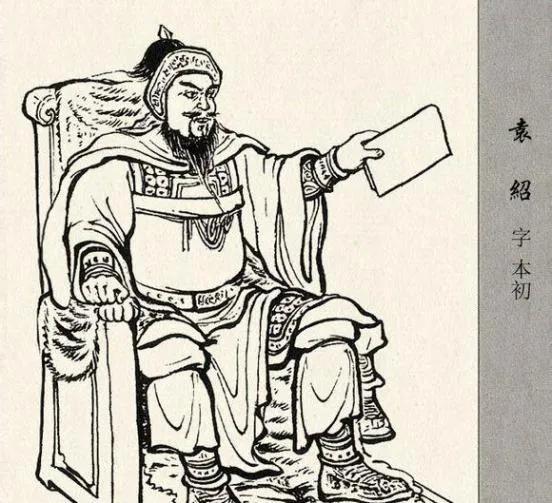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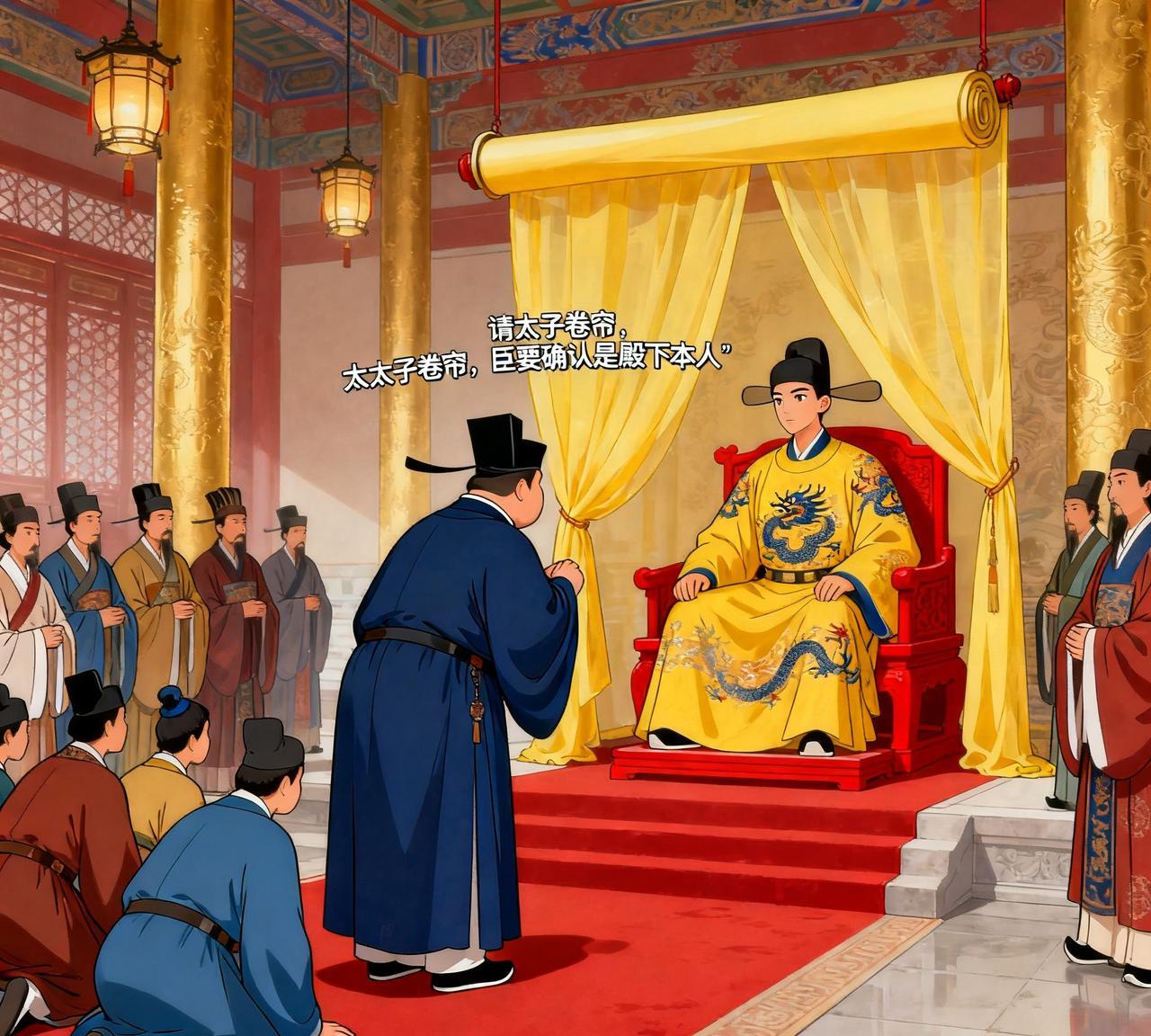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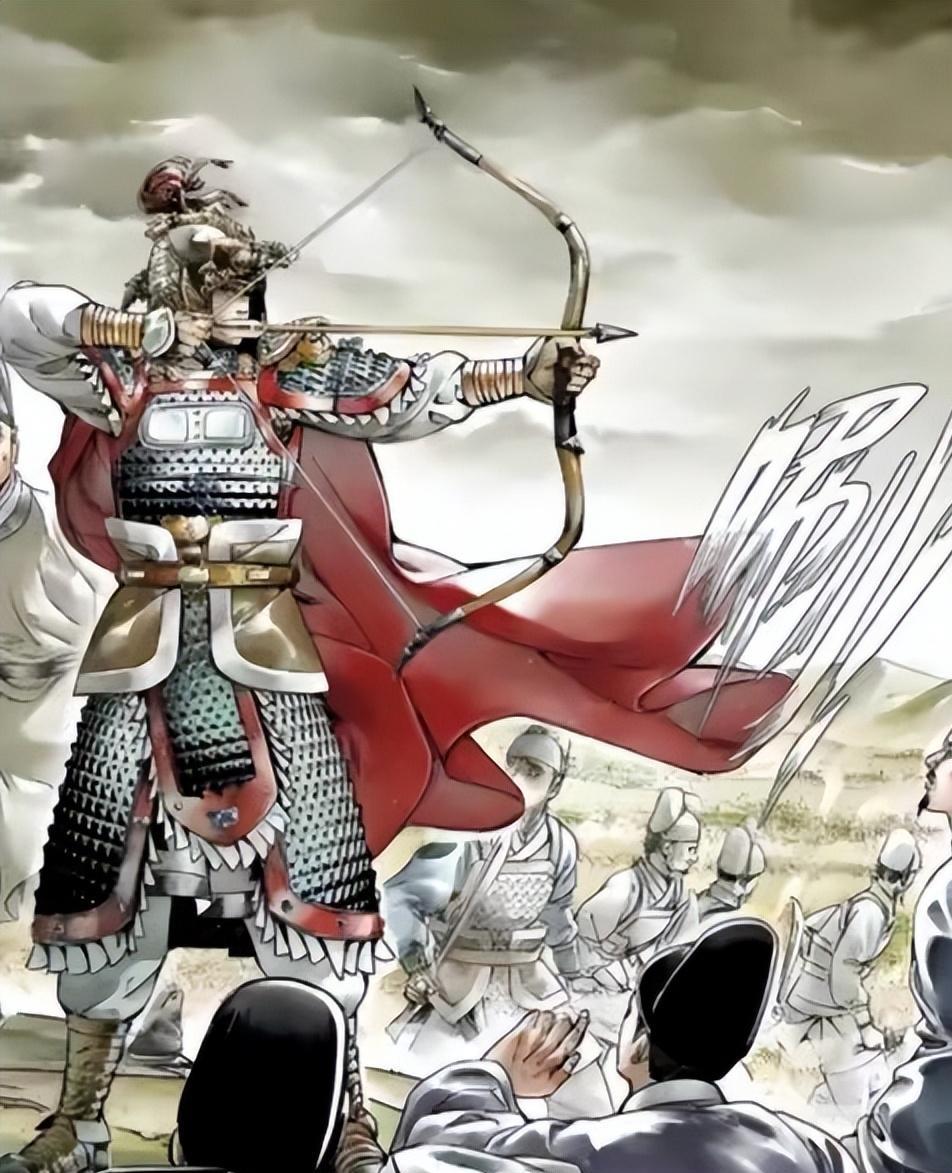




用户12xxx51
聪明人,通透,知进退,明得失,乱世中,于权力漩涡里保全,奇迹也
鲇川丸子的人001x
把郭威杀的断子绝孙!要是我有兵有权也会兵变!不兵变就会被杀死!
山花烂漫
刘氏杀郭威儿子时何曾心软?
用户76xxx23 回复 08-23 11:25
这样都能活很厉害。
用户12xxx71
杀郭威家人时,太后又在干什么呢
用户12xxx71
杀郭威人时,太后又在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