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大明朝的范进老先生,中了个举人,一时痰迷心窍,竟在街上拍手大笑:“噫!好了!我中了!”直吓得老丈人胡屠户一巴掌扇过去,方才还了魂。谁料想,数百年后的今天,范氏门中又出一桩喜事——范曾大师晚年得子,此事一出,文坛艺苑顿起波澜,比起老祖宗那“中举疯”的热闹劲儿,竟是不遑多让。

范进当年为的是功名,范公今日为的是血脉。一个是科举路上蹉跎半生的穷书生,一个是画坛驰骋数十载的大宗师。时代变了,范家人追求的东西也与时俱进,从“学而优则仕”进化到了“艺而优则嗣”,堪称范氏家风的现代化转型。
吴敬梓笔下的范进,把“喜极而疯”演成了千古名场面——胡屠户的巴掌还没落下,老秀才已拍着大腿在集市上转圈圈,嘴里喊着“中了!中了!”,活像刚抢着五折鸡蛋的广场舞领队。三百年后范家门第再出新闻,范曾先生古稀得子,全网比他还激动,热搜词条叠着词条,比当年报喜的锣声还热闹。这范门两门“大喜”,恰似一壶陈酒泡着冰可乐,酸的、烈的、甜的全搅在一块儿,咂摸起来别有一番荒诞滋味。

当年范进中举,难在“十年寒窗无人问”。五十多岁的老童生,头发比贡院的门槛还白,考到街坊邻居都懒得嘲笑——就像村口总说要发大财的王大爷,听多了连狗都不抬眼皮。胡屠户骂他“现世宝”时唾沫星子横飞,丈人鞋底的泥都比他金贵。可一旦捷报传来,胡屠户立刻换了嘴脸,提着猪大肠上门贺喜,那谄媚劲儿,比现在直播间喊“家人们”的主播还熟练。彼时的功名,是寒门唯一的梯子,爬上去就能把草鞋换成朝靴,难怪范进要喜疯,换谁在柴房里啃了半辈子红薯,突然端上满汉全席,都得先笑到缺氧。

如今范曾得子,妙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古稀之年添丁,比年轻人生双胞胎还轰动。当年范进中举靠的是笔杆子,如今范先生得子靠的是精气神,前者拼的是科举制度的通行证,后者拼的是现代医学的硬实力。消息一出,贺喜的人能从潘家园排到琉璃厂,送的礼物更是花样翻新:有送文房四宝盼子承父业的,有送育儿手册担心老爷子手忙脚乱的,还有人翻出《三字经》批注“范门后继有人”,比自己家添丁还上心。当年范进疯了是没人敢管,如今范先生得子是没人敢劝,毕竟人家身体倍儿棒,书画润格比黄金还贵,养个娃的底气比国子监的匾额还足。

这两场“范门狂欢”,看似风马牛不相及,骨子里却都是对“圆满”的执念。范进中举前,连老母亲都饿得起不来床,中举后米缸瞬间满了,连县令都亲自上门“认亲”,这冷暖反差比变脸还快。范曾先生本就声名在外,得子后更成了“人生赢家”模板,有人夸他“老当益壮”,有人羡他“福气深厚”,全然忘了当年范进疯时,众人只当他是“疯子”,没人说他“福气好”。可见这世间的评价标准,从来都是跟着结果走——中举是“喜”,疯了也是“喜极而疯”;得子是“福”,年纪大也是“老来得福”。

最妙的是两场喜事的“收尾”。范进被胡屠户一巴掌打醒,从此安安稳稳做他的举人老爷,再也不用看丈人脸色;范曾先生得子后,抱着襁褓笑逐颜开,书画里都多了几分柔意。当年的范进要是知道三百年后,自家后人靠“得子”而非“中举”上热搜,怕是要把八股文扔了,改练养生功。而那些围着范先生道贺的人,要是穿越回清朝,估计也会举着猪大肠去给范进道喜,嘴里喊着“恭喜老爷,贺喜老爷”,姿态和当年的胡屠户别无二致。

范氏二公,一古一今,一中举一得子,恰如中国文化的两面镜子:一面照见功名社会的荒诞与温情,一面映出当代艺坛的喧嚣与传承。戏谑之余,不禁令人深思:我们笑范进,笑的是那个已经远去的科举时代;我们贺范曾,贺的是这个多元开放的当下。而笑与贺之间,流淌的正是中国文化那股子既传统又现代,既庄重又幽默的独特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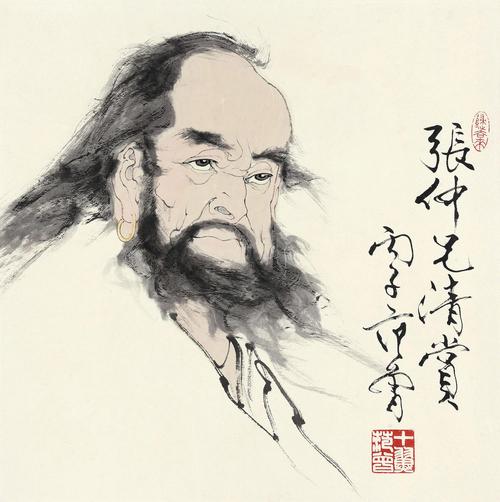
这正是:范进中举疯一时,范曾得子喜满门。古今戏谑皆成趣,留与后人细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