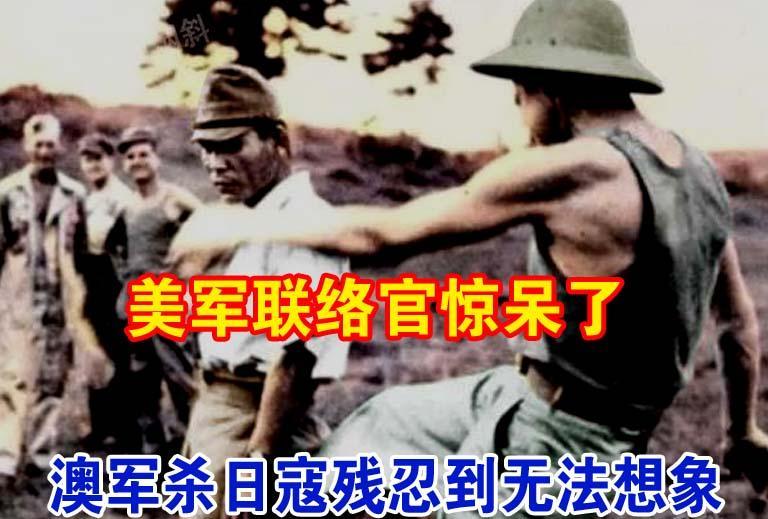1952年深秋,朝鲜中部铁原郡的山岭在燃烧。45师师长崔建功守在坑道里,右臂的旧伤随着炮弹爆炸的震动不断渗出血水。
而十七年前那个在黄土高原上举手投降、连枪都端不稳的国军小兵,此刻正决定着上甘岭的命运。他抓起铅笔在炸碎的弹药箱上写下一行命令,再守一天。
他就是崔建功,他以“誓死坚守”的决心鼓舞士气,在极端环境下保持冷静指挥,被评价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英雄”。
在1935年深秋,直罗镇的山坳里弥漫着硝烟与血腥气。
直到枪声停歇后,一群东北军溃兵被集中看管起来。
其中有个瘦高的年轻人,手脚不知该往哪儿摆,那个年代许多人都吃不饱饭,有些人参军可能就为了一口吃的。
而他正是如此为了混口饭吃,稀里糊涂跟着队伍,连红军长什么样都没看清就被缴了械。
老乡喊他崔小四,在河北魏县老家,他给地主种地,十六岁前连个大名都不配有。
那年黄河沿岸闹旱灾,饿殍遍野,他只好奔武汉讨活路,又赶上战乱断了生计,最终只能去当兵。
当红军战士端来的玉米糊糊还烫手,班长啃着硬窝头蹲在他面前。
这支衣服破烂的队伍,官兵睡同一个草堆。
那些关于“穷人打仗为娃吃饱饭”的话钻进了他心里,他爹活活累死在东家的田里,小妹饿死时小手里还攥着半块观音土。
原来世上当兵的,竟真有不一样的活法。
于是他选择留了下来,依旧叫崔小四。
送文件磨得脚底血泡连着血泡,老兵解下自己的绑腿裹上他的脚。
这支队伍不看你的过去,只看你今天干了什么。
没谁高高在上,也没人背地里剥削小兵。
没有吃的哪怕是军官,也一样跟着饿肚子。
不像在国军,大官高高在上趾高气扬吃香的喝辣的,而他们只能吃糠咽菜。
现在这支军队不一样了,大家好像都是兄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在1937年秋,崔小四随部队奔赴华北战场。
山西的寒风中,他亲眼看见日军刺刀挑起婴儿,整村整庄的老百姓被赶进沟里活埋。
消息传来,魏县老家也陷落了。
这个曾为糊口当兵的青年,第一次攥紧了步枪,护不住了,咱也得护!
十年烽火征尘,从通讯员到营长,黄河南北的山岭间布满他的足迹。
1945年打邯郸,他带突击队冲向碉堡。
子弹擦着耳际飞过,爆破筒塞进射击孔刹那,弹片深深切进右臂筋骨。
他在农家门板上草拟战报,抬头撞见满墙褪色的红字,“建功立业”。
他忽然对指导员说,往后叫我崔建功,命是弟兄们救的,总得建点功。
七年后,鸭绿江面浮动着薄冰。
时任45师师长的崔建功接到命令开赴朝鲜。
五次战役的硝烟未散,上甘岭的炮火已经染红了半边天。
1952年10月14日黎明,美军40余架战机与三百余门重炮开始对高地实施饱和轰击。
山头工事被削去两米,整排的战士在坑道口窒息而死。
师指挥所的岩石缝隙里震落着血滴,旧枪伤在持续猛烈的炮击下裂开。
血战至第十五天,前沿两个团几乎被打空。
通往军部的电话线接而复断,最后的消息是,没有预备队可调。
崔建功的笔尖戳穿了地图,“给军长发报!45师哪怕只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剩一个班,我当班长!
坑道里漂浮着硫磺与血肉蒸腾的雾气。
战士们干裂的嘴唇沾着湿毛巾,传说着一个苹果的故事,运输员突破封锁线送来的苹果,在十五个重伤员手中传了三圈才被啃掉小半边。
有人在断壁上刻下牺牲战友的名字,黄继光扑向机枪眼的土丘所在方位,欧阳代炎抱着炸药滚入敌阵的山坡标高。
炮火把山头犁了十七遍,阵地在敌我手中反复易手四十六次。
当美军第三步兵师撤下焦黑的山岭时,三万五千人的伤亡数字震动了西方世界。
范弗利特精心策划的摊牌行动,最终在崔建功和他的士兵面前,成了一场彻底的牌局崩盘。
庆功宴上,崔建功抚摸着军功章久久无言。
他说这勋章坠手得很,是坑道里那些冻僵的手、炸碎的腿堆出来的分量。
之后战场外的荣光接踵而来。
他走进人民大会堂,视察边防军营,当年的崔小四成了统领一方的昆明军区领导。
唯有电影《上甘岭》的放映通知送到时,他悄悄离席消失在夜色里。
影院内炮火轰鸣的声效远远传来,他蹲在杨树下的暗影里,右臂不自觉按着旧伤的位置,哪来那么多活蹦乱跳的英雄?一百个上去的,回来的凑不足一桌。
2004年秋,崔建功在武汉溘然长逝。追悼会上悬挂的巨幅照片中,老人右臂仍习惯性微微内扣,那是邯郸战役留下的永恒印记。
这个被饥饿逼上从军路的农家少年,在历史洪流的裹挟中,于太行山选择信仰,在朝鲜用生命写下注脚。
上甘岭的碎石里,至今还嵌着45师将士破碎的纽扣与姓名牌。
当将军的骨灰融进长江波涛时,那些沉默于异国山峦的灵魂也似得到安顿。
来选择直面深渊的身影,终将被历史以最庄重的笔画镌刻,纵使是无名者也有光,纵使是深渊亦能化为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