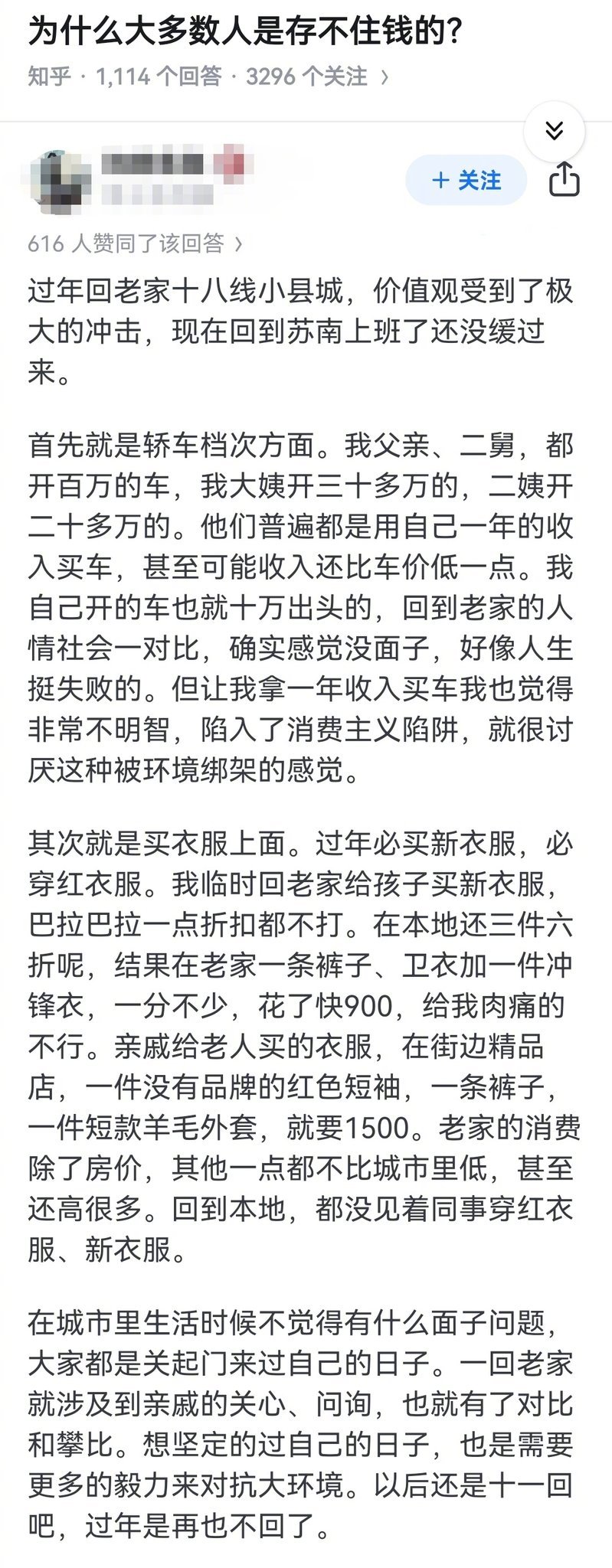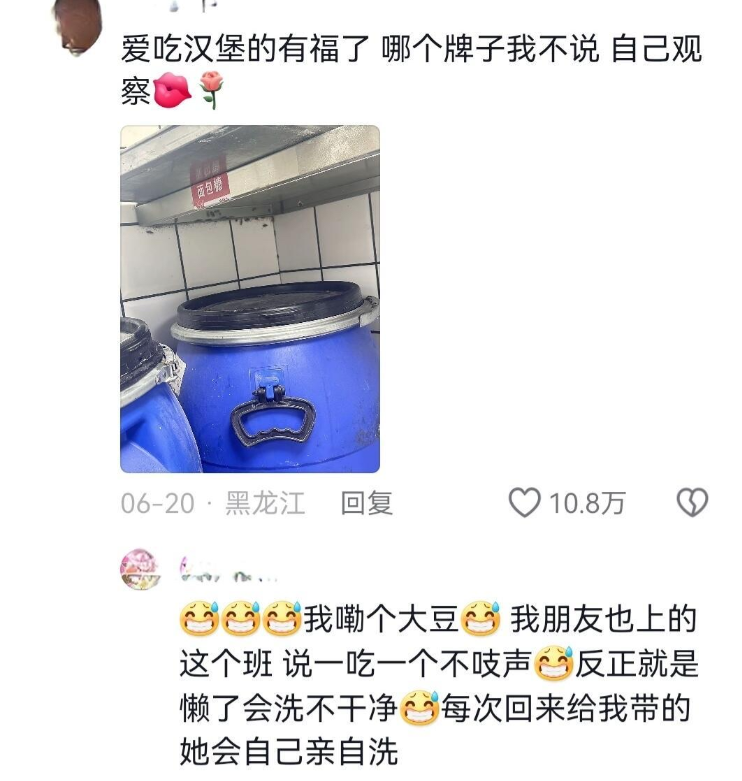村子里一个寡妇,巳年过六十,只有一个儿子,多年前去城里打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
孙立群说事阿吖
2025-07-16 18:20:34
村子里一个寡妇,巳年过六十,只有一个儿子,多年前去城里打工,一没有文凭,二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凭借一身力气,在一个老板厂里做杂工,老板看他诚实可靠,安排他去学开叉车。
那寡妇姓陈,村里人都叫她陈婶。丈夫走得早,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叫大勇,人如其名,长得五大三粗,却是个实心眼。离家那天,陈婶把攒了半辈子的两千块钱缝在他内衣口袋里,站在村口望着班车扬起尘土,直到影子都看不见了还站着。
大勇在城里头三年,住的是八人一间的工棚,吃的是最便宜的盒饭。每个月工资一到手,先往家寄一千五。陈婶总在电话里说用不着这么多,他就憨厚地笑:"妈,我在城里花不了几个钱。"其实他连件像样的冬衣都舍不得买,有年冬天手上冻疮裂得流血,还瞒着不让陈婶知道。
转折出现在第四年。厂里新来了批进口设备,需要会开叉车的工人搬运。老板看大勇做事稳妥,点名让他去培训。那半个月,大勇白天上班,晚上就蹲在仓库里对着说明书研究到半夜。结业考试那天,他操作得比老师傅还稳当,从此成了厂里技术工。
工资涨了,大勇却更省了。他报了个夜校学机械制图,每天下班骑共享单车穿过半个城去上课。有次陈婶打电话,听见背景音里老师讲课的声音,才知道儿子在偷偷学本事。那天夜里,陈婶把丈夫的遗像擦了又擦,小声念叨:"咱儿子有出息了..."
去年春节,大勇开着小轿车回村,后备箱塞满了年货。村里人围着车啧啧称奇,他却直奔村尾王奶奶家,送去新买的羽绒被——当年他离家时,王奶奶偷偷塞过二十个鸡蛋。陈婶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着儿子挨家挨户送东西,眼泪在皱纹里打转。
现在的陈婶可神气了。她家老屋翻新成了二层小楼,大勇特意给装了地暖。村里留守的老姐妹常来串门,她就泡着儿子带回来的龙井茶,讲城里的事。有回说到大勇被评为"优秀员工",照片挂在厂门口的光荣榜上,老太太们的赞叹声差点把房顶掀了。
最让陈婶欣慰的是,大勇去年把隔壁村三个小伙带进城,手把手教他们开叉车。其中一个现在已经是小组长,每月都给家里瘫痪的老爹寄钱。村里人都说陈婶养了个好儿子,她总是摆摆手:"孩子自己争气..."可眼角的笑纹藏都藏不住。
上个月我回老家,看见陈婶在村口文化广场教老太太们跳广场舞。她穿着儿子买的运动鞋,动作灵活得不像六十多岁的人。休息时她掏出智能手机,得意地给我看大勇发来的视频——他在职工技能大赛上拿了三等奖,台下掌声雷动。
夕阳西下,陈婶指着广场边的宣传栏让我看。那里贴着大勇的照片,下面写着"本村优秀青年代表"。照片里那个曾经只会出苦力的小伙子,如今穿着整洁的工装,胸前别着闪亮的厂牌,眼神里满是笃定。
回城前,陈婶硬塞给我一罐自制辣酱:"给大勇捎去,他就好这口。"罐子上贴着便签,歪歪扭扭写着:"儿啊,别太累。妈在家挺好。"我忽然明白,这对母子最动人的不是逆袭的故事,而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牵挂与成长,像种子在石头缝里发芽,终将顶出一片天。
0
阅读:39